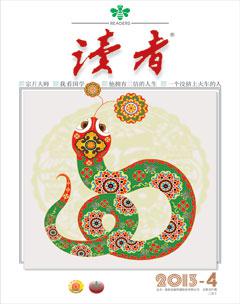圆满
吴念真

他父亲在乡下当了一辈子的医生,一直到七十五岁才慢慢退休。
退休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有医保之后,村里的人不管大小病都宁愿跑去邻近的大医院挤,加上人口外移以及老病人逐渐凋零。
母亲说,父亲现在的病人只剩下他自己,病症是自闭,不出门、不讲话,唯一的活动是自己跟自己下围棋。
从小他父亲就期待孩子中至少有一个人可以当医生,但三个小孩都让他失望:弟弟从小学钢琴,不过后来也没变成演奏家,现在是录音室老板,每天听别人演奏。
妹妹念传播,当过一阵子电视台记者,和企业家第二代结婚,然后离婚,用赡养费经营了一家双语幼儿园。
父亲曾经抱怨说,都是他这个长子的坏榜样。高中分科的时候,不管父亲怎么威逼利诱,他还是坚持念文科,之后进报社,职位起起落落,直到现在看着报业飘飘摇摇。
母亲曾经跟他们说,其实父亲最常抱怨的理由是:这三个小孩所做的事都“对咱们没帮助”。
不过几十年过去,那样的抱怨倒是慢慢地少了,更意外的是,当他的儿子竟然选择医科并且高分考上时,父亲不但没有惊喜,反而淡淡地说:“傻孩子,这个时代才选这条艰苦的路。”
除夕那天,母亲口中“三个台北分公司”的三家人陆续在黄昏之前回到老家。妹妹、两个儿媳妇加上几个孙女,几乎把厨房挤爆,她们一边在那儿帮忙,一边听母亲讲之前和父亲搭邮轮去阿拉斯加旅行的见闻。弟弟则在客厅给那台老钢琴调音,“叮叮咚咚”的,那是他每年过年回家固定的仪式。其他几个半大不小的男孩则歪在老沙发和祖父的看诊椅上看漫画、玩电动。
父亲仿佛跟家人完全搭不上边似的,在二楼阳台侍弄他的兰花。他隔着纱门看着父亲已然苍老的身影,父亲的背都驼了,连步子也迈不开。
当他把威士忌递给父亲要他休息一下时,父亲只是笑眯眯地接过杯子。他跟父亲说大儿子得值班,初一晚上才会回来给他拜年,父亲也只是说:“住院医师……若苦役哩,大大小小的事情做不完……”隔了好久才又问:“回来时……高速公路有没有塞车?”
“没呢。”他说。
然后两个人就都沉默地望向过去是一望无际的稻田,而今却四处耸立起别墅型农舍的田野。
暮色逐渐笼罩,他不经意地转头看向父亲时,没想到父亲也正好转过头来,静静地啜了一口酒之后,仿佛很努力地在找话题,最后终于问道:“回来时……高速公路有没有塞车?”
“没呢。”他依然这么回答他。
团圆饭后发红包,孙子们发现阿公留给医生哥哥的红包是他们的两倍厚,大家起哄说阿公偏心。已经五六杯威士忌下肚,整个脸红彤彤的父亲笑着说:“哥哥当医生最辛苦啊,他是在顾别人呢,你们都只需要顾好自己就好。”
父亲习惯睡前泡澡,那时候所有人都挤在二楼的和室陪阿嬷聊天、打牌,泡完澡的父亲忽然笑眯眯地拉开纸门说:“你们累了就先去睡,等贺岁的时间到了,我叫你们。”
所有人忽然安静下来,因为父亲的表情好像还有话要讲,等了好久之后他才有点腼腆地说:“看大家这么快乐,阿公也好快乐。”
他说:“那是父亲这辈子最感性,却也是最后的一句话。”
当他们听到贺岁的鞭炮声已经远远近近响成一片,而父亲竟然还没有上楼叫他们时,才发现父亲舒服地斜躺在沙发上永远地睡着了。
他的表情好像带着微笑,电视没关,交响乐演奏的正是父亲往昔结束看诊之后,习惯配着一小杯威士忌眯着眼睛听的乐曲,维瓦尔第的《四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