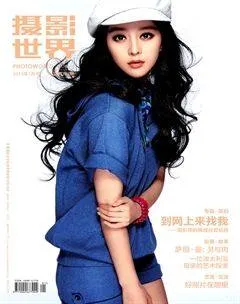曹德胜:航海人的视界
随着摄影器材的进步和普及,随着人们职业生涯的多元化,越来越多的人把摄影当作自己的爱好和乐趣。他们不以此为生,但以此为乐。正因如此,他们可以在摄影中进行更为大胆无羁的尝试,可以将各自基于不同经历和学科背景的视野、思考融会进作品中,为摄影领域注入新的活力和可能。为此,本刊今年特开设“跨界”栏目,请这些跨界人士与我们分享他们的佳作和故事,期待读者从中可以获取灵感和启示——从摄影,到职场,甚至到人生。
船,行驶在太平洋正中。乌云盖顶,暴雨滂沱,瓢泼的雨水浇打下来,驾驶台的雨刮器刮也刮不及……突然,一阵风刮过来,雨竟然随风停住,太阳啪地闪现在上空,迎着船头、朝着大洋放出万丈金光,船上所有人都被卷裹进这金灿灿的光线里。一个恍惚,太阳和它的光芒埋进乌云,消失不见。一切不过几秒间,有如神迹、“佛光普照”般的几秒钟!
这不是少年派的奇遇,不是电影里的特效,这是曹德胜拿着一张片子在回忆,他今年9月带着船队出访美国归途中遭遇的又一场海上奇景。那张照片捕捉住了陆地上无法形成的云明明暗暗翻滚的姿态,耀眼的光以及墨蓝的海。
“看得到的视角,看不到的视野。感受得到的日子,感受不到的生活。”他带着开玩笑的语气总结一个爱摄影的航海人的体悟。
海上十余载,从水手干到船长,即使后来上了岸,做了中国海事局的副局长,每年也差不多有3个月的时间要在船上度过。作为一个资深航海人,曹德胜的确有着常人无法触及的生活体验,而作为一个手拿相机的航海人,他眼中也确实有我们看不到的风景。
1977年,曹德胜成为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中的一员。家人希望他去当兵做飞行员,他却跑去学了航海。这个少年时代率性而为的选择决定了他一生的职业方向,也让他跟摄影结了缘。
1981年,还没满18岁的曹德胜大学一毕业就登上了远洋船。7000吨的船,从上海跑洛杉矶,一趟得跑一个月。
那真是让人记忆深刻的一个月。告别风和日丽的海港,船漂泊在海上,当强风袭来,海浪排山倒海、前赴后继,这个学校里的运动健将、万米长跑冠军开始晕船,吐得苦不堪言——先吐胃里的东西,接着吐胃液,最后吐血。一个月下来,曹德胜从一百二十来斤瘦到了九十多斤。
晕船归晕船,活儿还是要干。每天轮两次班,一次4小时。冲甲板,刷防锈漆,拿锤子一点点从船头到船尾敲海水蚀出的锈,等敲到船尾,船头又起了新锈,于是从头再来,周而复始。新人的工作内容里还包括给高级船员递茶送水,包括适应晕船和孤独,磨炼身体与意志……和每个水手一样,曹德胜日复一日地干着这些活儿,慢慢看惯了海上的日出日落;和那年代的一般水手不太一样的是,他所在的船上有个爱摄影的二副。
“什么哈苏啊宾得啊,他有很多很多摄影器材,十来平米的房间堆了一房间!我出于好玩,就跟在他后面。”
年长的二副来自一个有摄影传统的家族,每天都要认认真真拍上几张照片。跟着他,曹德胜在船上完成了自己的摄影启蒙,他第一次摸到相机,按下快门——用的是二副的哈苏。
那时拍照拍的都是胶片,要自己冲洗。看着胶卷从什么都没有到慢慢显影,摸索不同的显影定影配比带来的不同效果……这一切都给曹德胜带来了无穷的乐趣,“拍拍拍,就喜欢上了。”
那几年,他在休假时跟着二副一起背着相机去西藏去缅甸,也开始有意识地找相关书籍,看片子,向摄影大家们学习。
到1991年,28岁却已是经验丰富的船长的曹德胜从船上下来,他逐渐养成了随身带相机的习惯,断断续续地持续拍照,直到今天。
“这么多年,我拍照片都是随兴所至,没有什么专门的主题。当然,跟水相关的可能比较多,能拍出感觉的也就是水。”
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海洋和船上的生活给曹德胜提供了不尽的题材。
他也拍西藏的湖泊,云南的梯田,沙漠的胡杨,小东江上的渔船,但曹德胜拍得更多是与海洋、与海事有关的一切。
他跟海最亲近。在船上,他是船长,担负着船员的信任和保证船舶安全的职责,率领船队环着地球乘风破浪,最长时间一年半没下过船;在海事局,他主要负责海上事故的应急处理。客船起火、渔民遇难、航道结冰……哪里出了事、哪里有重要活动,他就第一时间飞到哪,现场指挥。
船长也好,应急指挥员也好,曹德胜的工作一直伴随着巨大的压力和紧迫感,摄影于他,也因而有着不同的意义。“我拍片子的一个功能就是让自己放松放松,分散注意力,缓解紧张情绪。同时,也是一种记录。等我退休了,一张张地整理照片,会回想起很多当时的事情。”
曹德胜的片子大都是在东奔西走的工作之余拍下的:大洋深处自由跃起的海豚,伫立碧波中的大沽灯塔和拖着白浪的船只,老铁山灯塔夕照下沉默温暖的灯光,劈波斩浪的船头飘扬着蓝色海事旗,漫长的海岸线,碎裂的巨大冰块漂浮在渤海湾,海巡船破冰引航,奥帆赛时浮山湾的蓝海白帆,给船只刷漆的船员,获救的渔民,忙于灭火的救援队员……
他选择的拍摄位置常常是驾驶台、直升机、雷达站,居高临下地占据了陆地上鲜少能看到的视角和场景。曹德胜的作品画面往往色彩浓郁瑰丽,视野宽阔,气势浑然。偶有花鸟小品,明净而温柔,与其他作品呼应,好似展露出作者内心深处的另一角。
“这次我们出去,船也不小,100多米高,可浪有30多米,我们一会儿在浪底下,一会儿翻上去。什么叫一叶扁舟啊?你去看树叶在河里漂,跟那感觉一样——你没有任何可以做的,只能随波逐流。”
“人定胜天是理念,事实是人定胜不了天。当你到大海洋上,无论多大的船,一定都非常非常渺小。什么叫沧海一粟?那时候你就知道。”
“船员最讲义气。什么叫同舟共济?你在船上,大家必须抱成一团,才能活下来。”
没有人比航海人更懂什么叫“一叶扁舟”、什么叫“沧海一栗”、什么叫“同舟共济”。每个航海人都势必对大自然充满敬畏,性格里也必然留下海洋的刻记。
跟海打交道,几遭死里逃生,曹德胜说自己“曾经差点死过三次”。
第一次,他们船上运了8000吨航空煤油,机舱失火,控制不及,船员们在封住机舱后撤离。不到万一,不能弃船,时为二副的曹德胜和另一个兄弟留守在船上,俩人在餐厅里一人拖着一箱啤酒对着喝,不抱希望地静静等待与船一起爆上西天。最后火烧光了密闭机舱中的氧气,熄灭了。
第二次,在南海遇到台风,船进了台风眼。风眼区无风无浪,但船只稍有偏离中心区,就随时可能被高速旋转的气流掀翻。盯着雷达,看着气象云图,曹德胜指挥着船跟着台风眼走,耗了七天七夜,终于安然等到台风过去。“也没啥感觉,真的,就想着怎么让船跟着风眼走,没想到活啊死啊危险什么的。”
第三回是撞船,他们的船差点沉了,所有人全部下了救生艇。
“这么说吧,我们班毕业的时候32个人,等到20年同学聚会时剩下26个,30年聚会剩下24个。除了1个是正常死亡之外,其他的都是遇到海难走了,风险就这么大。所以我呢,现在很幸福,能活着就很幸福。有我们这种工作经历的人,对生活都很坦然。”曹德胜说,“大自然第一你捉摸不透;第二,永远别想着跟它去抗争。”
曹德胜把所拍到的最好的片子全归功于自然造化,而非自身的技术和能力。
他用近期自己最喜欢的一幅作品作为例证,“可遇而不可求,这种片子要是特地去拍根本拍不出来,也造不出这样的效果,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
那是一张打眼看去犹如一幅超现实主义画作的照片。凝固的有着金属质感、液化形态的气泡,大概只有航海人才可能在细查下看出若隐若现中,艳绿色的是甲板、白色的是护栏与主桅杆,深蓝色的是海,蔚蓝色的是天——这是梦幻解于现实所造就的新景观。
片子同样拍摄于9月的赴美之行。船队前往夏威夷的途中,在太平洋上遇到超强台风,风掀起10层楼高的巨浪,一浪过来盖过曹德胜身处的30多米高的驾驶台,船左右摇摆得厉害,他被摔倒在地,抬起脸正看到面向自己的窗玻璃上不可思议的场景,他抓起相机想都没想按下快门,“就一秒钟的事,海水还没下去,雨刮器还没刮过来。”
——除了航海人的眼睛,谁还能看到这样的画面?除了在海上经过风浪、尝过生死一线的幸运儿,谁还能捕捉这样的瞬间?“这么多年在船上,拍到这张片子可以说是大海对我的眷顾。” 曹德胜说。
把陆地和近海所没有的风景带上岸,航海人的片子是自然的眷顾,也是他们向自然的致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