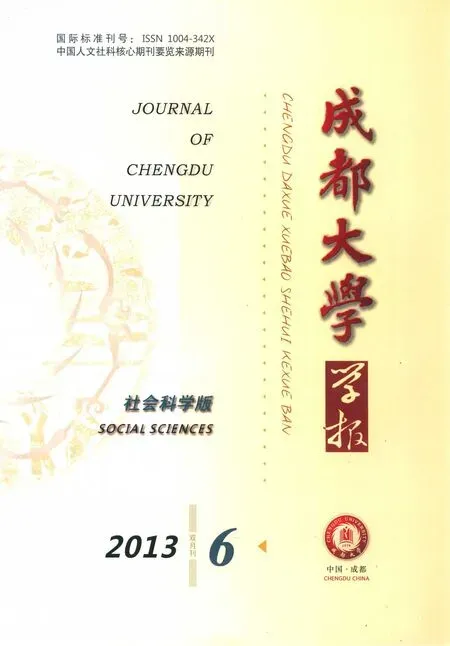从泰语和中文教学看中泰两国关系之发展
段立生 赵 雪
(云南大学 泰国研究中心,云南 昆明 650031)
语言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是人与人之间进行相互交流和沟通的工具。对于两个使用不同语言的国家和民族来说,要想建立正常的联系和交往,首先就必须学习、了解和掌握对方所使用的民族语言。只有具备了语言翻译这个最基本的条件,才谈得上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交流,才能维系良好的外交关系。同时,两国之间友好关系的深度和广度,亦是跟两国之间学习、了解和掌握对方语言文化的深度和广度成正比的。就是说,我们可以从中国的泰语教学与泰国的中文教学的演变历程来看中泰两国关系之发展。
一 1世纪公元至15世纪中泰交往靠“重译”
早在公元1世纪中泰两国之间就开始了联系和交往。根据中文古籍的记载,在汉朝的时候,即公元1-5年,中国使节从广东乘船,经越南、柬埔寨,渡暹罗湾,步行越过克拉地峡,然后乘船至印度。《汉书》卷83说:“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罗国;自夫甘都罗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与珠涯相类。”从地望上分析,谌离国和夫甘都罗国皆在马来半岛的克拉地峡附近,属今泰国领土范围内,应是泰国境内的早期城邦国家。
公元230年吴国官员朱应、康泰奉命出使东南亚,归来后朱应著《扶南异物志》,康泰著《吴时外国传》,其中提到现今泰国佛统一带的金邻国。暹罗湾古称金邻湾,就是因金邻国得名。
公元5世纪,马来半岛南部存在一个盘盘国。《新唐书》卷222说:“盘盘,在南海中,北距环王,限少海,与狼牙修接,自交州海行四十日乃至。”盘盘国与当时中国的唐朝建立了外交往来,“贞观中,遣使朝。”
与盘盘国存在的同时,在宋卡、北大年一带有一个赤土国。《隋书》卷82载:隋大业3年(607年)炀帝派常骏、王君政出使赤土。常骏一行从南海郡乘船,昼夜兼程,一月余达赤土界。“其王遣婆罗门鸠摩罗以舶30艘来迎,吹蠡击鼓,以乐隋使,进金鏁以缆骏船。”后来,赤土国王还命王子那邪迦随同常骏等回访中国,受到隋炀帝的接见和封赏。
公元6世纪,泰国中部佛统一带出现了堕罗钵底国,又称墮和罗国。《旧唐书》卷197说:“堕和罗国,南与盘盘,北与迦舍佛,东与真腊接,西临大海。去广州五日行。贞观12年(638年)其王遣使贡方物。”
公元10世纪,中国宋代的文献里出现了三佛齐国。赵汝适《诸蕃志》三佛齐条说:“三佛齐间于真腊、阇婆之间,管州十有五。”虽然这个国家的中心在苏门答腊岛上,但有一部分领地深入马来半岛现今泰国的版图之内。泰国素叻它尼和斜仔,至今仍保留三佛齐时代建的佛塔和其他文化遗址。
公元13世纪,泰国北部南奔地区存在一个孟族建立的哈利奔猜国,中国史称女王国。这个国家见于樊绰的《蛮书》。南诏曾派二万军队去征服它,但被它打得大败。据说这个国家建于公元7-8世纪,是一位名叫占末苔维的孟族公主建立的,传至公元1292年被兰那泰所灭。
以清迈为中心的兰那泰是泰族建立的城邦国家,中国古籍称之为八百媳妇国。《明史》卷315说:“八百媳妇者,其长有妻八百,各领一寨,故名。”中国古籍还记载了兰那泰于明嘉靖年间为缅甸所并的情况。
公元13世纪的素可泰王朝,是泰族战胜高棉族统治后建立的泰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全国的中央王朝。中国称之为暹。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汪大渊的《岛夷志略》、元《大德南海志》等著作都提到过这个国家,《元史》记载了素可泰与元朝的密切的交往。
大约与暹国存在的同时,在湄南河下游的华富里存在一个罗斛国。后来罗斛国日益强大,并有暹地,中国史称罗斛灭暹,这就是公元1349年建立的被称为暹罗国的阿瑜托耶王朝。
明宣德至永乐年间(1405-1433年)太监郑和奉命七下西洋,曾多次到达暹罗。同行的马欢、费信、巩珍分别写了《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三本书,详细介绍了阿瑜托耶王朝的情况。截至到这个时期,中国都没有官方培养的泰语翻译,包括泰语在内的东南亚各国语言以及中国南部少数民族的语言,都被称为“南蛮鴂舌”之语,像鸟语一样难懂,完全靠“鴃舌重译”来沟通,即通过第三种语言进行翻译。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就是一位通晓阿拉伯语的翻译,他在《瀛涯胜览》序中说:“以通译番书,亦被使末。”15世纪时,伊斯兰教徒控制了海上贸易,阿拉伯语成了世界的通用语言,很多东南亚国家使用的小语种都是先译成阿拉伯语,再转译为中文的。迟至明万历年间,暹罗送来的国书,都由回回馆(阿拉伯语)“带译”。弘治10年(1497年)10月,“暹罗国进金叶表文,而四夷馆未有专设暹罗国译字官,表文无能译办。”大学士徐溥将这个情况报告皇帝,明孝宗才下令:“既无晓译通事,礼部其行文广东布政司,访谙通本国语言文字者一、二人,起送听用。”[1]但由于种种原因,此事一直没有落实。直到万历6年(1578年)大学士张居正提议,才在四夷馆内增设暹罗馆,将前一年来京的暹罗使者握闷辣、握文铁、握文贴,通事握文源“并留教习番字”,“考选世业子弟马应坤等十名送馆教习”[2],正式开启了中国官方主办的泰语教学事业。
二 四夷馆的泰语教学
四夷馆是中国第一所官办的教习国内少数民族及周边国家语言文字的学校,创办于明永乐5年(1407年),地址原在南京石门外,后随明成祖朱棣迁到北京。最初只设鞑靼、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等八馆,正德6年(1511年)增设八百馆,万历6年(1578年)增设暹罗馆。其中百夷馆是教习西双版纳傣族的文字,八百馆教习以清迈为中心的兰那泰文,暹罗馆教习现代泰国使用的泰文。
四夷馆的学员皆从世家子弟中选拔,学习期间享有官爵和俸禄,学成之后充当译字生。四夷馆的教员则是由来华朝贡的贡使中挑选,其中不少是移居外国的华人。负责四夷馆的官员称为提督,一位名叫王宗载的提督写了一本书《四夷馆考》,记录了许多有关四夷馆的重要史料。
暹罗馆的设置无疑是为着适应日益密切的中泰关系发展的需要。正如《重修翰林院四夷馆碑记》所言:“译习之学,可以数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也。”[3]根据《明实录》的统计,在明朝存在的270年内,明朝使节到暹罗19次,暹罗使节到中国110次,两国使节的来往,较以往的任何时代都频繁。明洪武10年(1377年)朱元璋将一枚镌有“暹罗国王之印”字样的金印颁赠给阿瑜托耶国王,这是中国官方第一次对这个国家使用“暹罗”这个称呼,直到公元1932年后才改称泰国。
另一方面,暹罗馆的设置又进一步增进了两国的相互了解。四夷馆提督王宗载“课余之睱,因令通事握文源且述彼国之风土物产”,并将了解到的情况记录在他的《四夷馆考》一书里。从这本书里,我们可以了解到暹罗到中国的海路航程。暹罗的物产有:食货、布、花木、禽、兽、鱼、蔬菜等。暹罗的官制分为九等:一曰握哑往、二曰握步喇、三曰握莽、四月握坤、五曰握闷、六曰握文、七月握板、八曰握郎、九曰握救。暹罗的行政区划分为:全国有大司库九、府十四、县七十二。老百姓“无姓有名,为官者称为握某,为民者称为奈某,最下称隘某”。“小民多载舟至各国商贩,市物少则用海叭多则用银”。“其所用磁器、缎绢皆贸自中国者”。
中国和暹罗有了语言方面的直接交流,无需再通过第三种语言转译,大大促进了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
明朝灭亡后,清朝从顺治元年(1644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统治中国,正值暹罗阿瑜托耶王朝后期至曼谷王朝初期。中暹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更加密切。暹罗方面主动向清政府提出恢复暹罗与明朝固有的朝贡关系。所谓朝贡,就是暹罗承认属国的地位,定期带着礼物来中国进贡。中国方面照例要给“赏赐”,按照天朝“怀柔远人”、“厚往薄来”的原则,“赏赐”物品的价值远远高于进贡的物品。因此,所谓朝贡,实际上是朝贡国单方面获利的官方贸易。而且,随贡船带领的商品,还可以减免关税,在广州就地销售。暹罗方面对于朝贡很感兴趣,按规定三年一贡,实际执行起来却是每年都有贡船来。第一年称为“探贡”,即先派几只船来试试看;第二年“正贡”,由贡使正式带着船队来;第三年再派船来接贡使。每次带来货物的批量都非常大,“虽云修贡,实则慕利”。
除了朝贡式的官方贸易外,私人贸易也有长足发展。特别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政府开放海禁,准许沿海居民到暹罗贩米,解决国内出现的粮荒,正式开启了中暹大米贸易。由此,形成了近代一次大规模的移民高潮。《嘉靖一统志》卷552暹罗条说:“澄海县商民领照赴暹罗国买米,接济内地民食,虽行之已逾四十余年,但此项米船,据称回棹者,不过十之五六。”
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依靠清朝官办的四夷馆来培养泰语翻译人才是远远不敷使用的。据《四夷馆则》载,四夷馆6年一考,每次招收40-50人,最多一次招收学员94人,其中泰语译字生不过10来名。由于多是世家子弟,免不了有部分不肯用功读书的膏粱纨绔,所以四夷馆则规定:“诸生学业荒废,怠累考俱下,列为下等,遇会考之日通算量行裁,抑或罚月日,或不准授冠带,以儆下驷。”[4]四夷馆基本上是采取科举制的办法来培养译字生。“初入馆者,照坐监例,食粮习学,俟三年后考中者,与粮一石,家小粮俱仍旧。又过三年,再考中者,与冠带。俟至九年考中优等者,授以从八品职事,习译备用。其初试不中及再试中否,俱照子弟例施行。三试不中者,送回本监别用。”[5]由此看来,经过九年培养,三次考试通过后,才能享受八品官衔,成为宫廷使用的译字生。
四夷馆的泰语教学方法,最初采取全日制的“逐日进馆”,崇祯元年(1628年)改为“三、六、九日近馆”。这样每月只需进馆学习11次,即点11卯,“二卯不到,记旷业簿。四卯不到者,记旷仍扣食粮。十一卯全不到者,即时参呈内阁停食作旷满日,不准收考。”[6]至于教材,则由教习自己编选。笔者曾见到一本当时使用的字典,仅收数百单词,用中文注音。比如说,泰语的“天”,中文注音“法”;“地”注音“佩丁”。教材十分简陋。
至于民间贸易往来需用的翻译人员,则靠华侨移民充当。第一代移民无疑是通晓中文的。当他们移民暹罗一段时间后,慢慢地学会了一些泰语,也就可以充当翻译。但是,在暹罗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华人,他们首先是在当地社会环境中学会泰语的,在家里受一点儿中文熏陶,然后到华校系统学习中文。所以,伴随大批华侨移民暹罗,泰国的中文教学便自然提上了历史的日程。
三 泰国早期的中文学校
暹罗华人社会的形成,是泰国早期中文教学得以实现的社会基础。美国学者威廉·斯金纳(G·William Skinner)估计说,公元17世纪,暹罗京城有4000华人,全暹罗有 10000华人。[7]泰国学者沙拉信·威腊蓬在他提交给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清代中泰贸易演变》中说:“1690年代初期,在大城(阿瑜托耶)的中国人已经达3000人,在暹罗其他地区的中国人数目可能更多。似此可观数字使人可以了解当时的对外贸易几乎全在中国人经营之内,因为事实上是,全暹人口不会超过200万人。”[8]
众多的华人移民聚居在一起,形成华人社区。明朝黄衷的《海语》说:“有奶街,为华人流寓者之居。”笔者亲临实地考察,奶街并不是一条街,而是大城外的一条名叫奶街(读若gai)的一条小河,河两岸住满华人。曼谷的大皇宫、三聘街一带,也是著名的华人社区。一直沿袭至今成为曼谷的中国城。居住在华人社区里的人很容易保持原先的语言、服饰和生活习惯。特别是明清时期,中国实行的是以血统决定国籍的《国籍法》,只要你有华人血统,包括其子孙,都是永久的中国人。因此,二战以前旅居泰国的华人都自认是中国人,他们办华校对子女施行中文教育,是把中文当作国语或母语来看待的。二战以前,泰国的华校多达294所,皆是由华人投资、华人管理、华人任教,并用中文教学的学校。这些华校无异于把中国的学校照搬到泰国。华校培养的大批泰国出生并精通中文的华人,支撑起两国间进行友好交往的桥梁。
二战时期日本占领泰国后,亲日的栾披汶政府下令封闭华校,使华校剩下为数不多的几所,并通过限制中文教学的时间,用泰文作为教学语言等手段,把华校变得跟泰国的一般学校没有什么区别。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强迫同化政策,使得战后出生的泰国人中几乎找不到通晓中文的人。泰中关系陷于停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泰国华校才得以复办,到1948年猛增至374家。但是到了第二年,泰国教育部饬令所有华校停办初中部,华校教育转入低潮。上世纪60年代,全泰国仅剩华校120家。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泰国追随美国反共排华的政策,中文一度被视为共产党的语言而遭受歧视。
四 从南京东方语专到北大东语系
近现代中国的泰语教学始于民国时期创建的南京东方语言专科学校,由研究泰国历史文化的著名学者姚枬先生担任校长。抗日战争时期一度由南京迁往昆明。解放以后并入北京大学东语系,由季羡林教授担任系主任,直到文革结束后。
1962年笔者考入北大东语系泰语专业学习,全班只有13名学生。在此之前,泰语专业也只招收过2-3届学生,毕业人数不超过20人。那时候中泰没有外交关系,再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影响,62级的泰语专业学生,一半以上被迫改行。可以说,那是中国泰语教学的低潮时期。
与四夷馆时代的泰语教学相比,北大东语系的教学质量显然是高了许多。泰国专家西提猜先生负责高年级的教学,低年级的课则由回国华侨范和芳、侯志勇、郑先明担任。还有前几届毕业留校的潘德鼎等老师。学生皆是从全国挑选来的尖子,学习刻苦用功。有的学生甚至连晚上说梦话都用泰语。笔者所在班级1962年入学,1966年便遇上文化革命,实际只学了3年。隔了17年没用,1983年笔者应邀到泰国清迈大学讲学,连我自己都没想到,开口还能讲泰语。完全是拜我的老师之赐。北大东语系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包括中国驻泰王国特命全权大使,经济参赞,武官,以及从事泰国语言、文化、宗教、历史、文学、经济等方面教学、科研的骨干和专家。
1975年中泰建交后对泰语翻译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和更高的要求,这是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首先,中泰两国经贸关系的迅猛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趋势。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建成,泰国对从中国进口的90%的产品实行零关税,中国对从东盟进口的93%的产品免征关税。中国成为泰国的第一大出口国,是泰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泰双边贸易具有极大的互补性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在经济互利的平等原则下,中泰两国建立起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高层的政治交往日益频繁,文化交流日益密切,民间往来日益增多,旅游观光日益兴旺。在这种情况下,决定了两国必须加速推进双语教学,即中国必须培养更多的通晓泰语的专业人才,泰国也必须加快培养更多的通晓中文的专业人才,才能适应目前形势发展的需要。
五 中泰双语教学现状
1.目前中国的泰语教学情况
从1975年中泰建交至2013年的38年间,中国泰语教学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远远超过了过去的二千多年。它彰显了中泰友好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日新月异的发展。中泰建交之前,整个中国开设泰语教学的学校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所,它们是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专科学校、广州外国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等。培养出来的学生人数不多,还有一部分毕业生因没有专业对口的单位而被迫改行。现在除了北京、广州、西安等城市外,广西、四川、云南等省也办起了许多教授泰语的学校,包括大学的泰语系,一直到高、初中和职业专科学校,都办起了泰语班。如果要统计整个中国目前的泰语教学情况,是一件需要花费很大精力的复杂工程,我们仅以跟泰国毗邻的云南省为例,进行调查统计,列表如下,便可以管窥豹。

云南省开设泰语以及泰语相关专业的学校统计表[9]

25 云南开放大学 泰国语(专科)166 26 昆明理工大学城市学院 英泰双语(本科)30 27 昆明市第二十七中学 泰语班(高中)60 28 昆明市第二十九中学 泰语班(高中)66 29 昆明市外国语学校 泰国语(职高)71 30 昆明市五华实验中学 泰语班(高中)60
根据上表,截至2013年7月,云南省共有30所学校开设泰语以及泰语相关专业,在校学生共计4165人。其中,云南省进行泰语专业硕士培养的有1所学校,学生90人;开设泰语相关专业本科专业的共13所学校,学生共2369人;开设泰语相关专业专科学历的共14所学校,学生共1449人;高中阶段开设泰语相关专业的共4所学校,学生共257人。
为了检验和认定泰语学习的成果,云南大学泰国研究中心与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合作,于2012年5月在昆明举办了第一次泰语水平考试(CUTFL),这是跟英语托福考试(TOFEL)和汉语水平考试(HSK)一样,由泰国官方正式认可的泰语水平考试,并由泰国朱拉隆功大学诗琳通泰语中心颁发证书。第一次泰语水平考试计有38名学生参加,第二次(2013年5月)发展到60人,参考人数和成绩均有大幅度提高。这不仅使云南的泰语教学逐步纳入正规化、规范化的轨道,也有利于学生的升学和就业,受到考生与用人单位的一致好评。
2.目前泰国的中文教学情况
1975年中泰建交后,泰国开始出现学习中文的热潮,泰国政府也一改过去的做法,允许各大、中、小学开设中文课程。20世纪90年代,泰国的华人企业家在郑午楼先生的领导下,筹资创建了泰国华侨崇圣大学。这是当今泰国乃至全世界唯一一所由华人出资创建的私立大学,“其中为商场上急切需求之华文华语人才,尤为圣大重点教育之一。”[10]当然,华侨崇圣大学已经不是二战以前的华校,它跟泰国的一般大学一样,隶属于泰国教育部大学部领导,除中文系可以用中文讲课外,其他系一律用泰语教学。另外,还创办泰国华文师范学校,免费培训来自泰国各地的中、小学华文教师。经考试合格后,颁发华文教师合格证书。
在中国“汉办”与泰国教育部的密切合作下,孔子学院如雨后春笋般在泰国出现,极大地促进了泰国的中文教学。根据汉办驻泰国代表处网站资料,目前泰国孔子学院的分布情况如下列统计表:

泰国孔子学院统计表(截至2013年7月)[11]
六 简短的结论
综上所述,中国的泰语教学和泰国的中文教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它的兴衰和发展史,实际是两国关系的晴雨表。中泰两国友好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决定了两国必须培养语言互通的翻译人才。从公元1世纪至15世纪,两国的交往主要靠“重译”,即通过第3种语言转译。直至公元1578年明朝政府在四夷馆中开始暹罗馆,中国才有了官办的泰语教学。这种用科举制度来培养译字生的方法一直沿袭至清朝末年。20世纪成立的南京东方语专是近现代中国泰语教学之滥觞,新中国成立后并入北京大学东语系。北大东语系培养了一批泰语方面的专业人才。但在1975年中泰建交之前泰语教学的规模不大,培养出来的人才有限。泰国的中文教学始于阿瑜托耶王朝时期,大批华人移民暹罗并在当地形成华人社会是泰国华文学校得以创办的基础。二战以前的泰国华人自认是中国人,泰国华校亦是照搬中国的学校。二战期间日本占领泰国后一度关闭华校。二战以后泰国政府限制中文教学,致使泰国通晓中文的人才出现断层。
1975年中泰建交后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发展,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催生了中国的泰语教学和泰国的中文教学的迅猛发展。目前形势喜人。本文通过对中国、特别是云南省开设泰语教学的学校、专业、师生人数的调查统计,以及泰国12所孔子学院的调查统计,用具体的数字和生动的事例说明中泰双语教学的蓬勃兴旺,由此反映并进一步促进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
[1] 《孝宗弘治实录》卷129。
[2] 王宗载:《四夷馆考》,东方学会1924年排印本,卷下,第21页。
[3] 吕维祺编:《四夷馆则》,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四辑》。
[4] 文祺编:《四夷馆则》,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四辑。
[5] 同上。
[6] 同上。
[7] G.William Skinner:Chines Society in Thailand.Cornel University Press,1957.
[8] 沙拉信·威腊蓬:《清代中泰贸易演变》,张仲木译,载曼谷《中华日报》,1984年10月18日。
[9] 统计数据均为笔者向云南省各学校调查统计所得,收集数据截至2013年7月,不包括2013年9月起开始招收泰语相关专业的学校。
[10] 郑午楼:《圣大建校计划三阶段》,载段立生主编《郑午楼研究文丛》,中山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43页。
[11] 根据汉办驻泰国代表处资料统计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