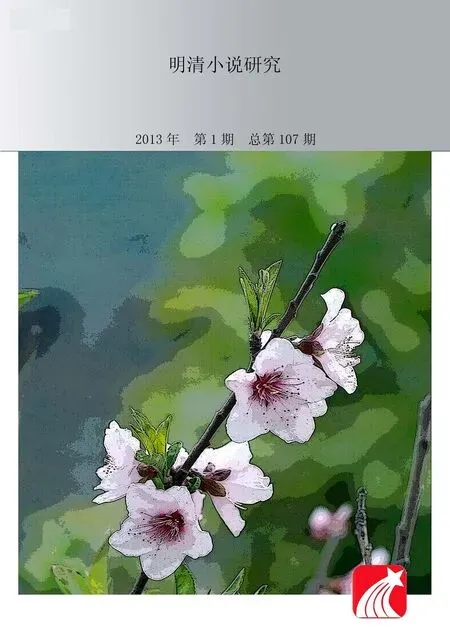论清末民初小说中“英雌”形象嬗变的双重维度
· ·
摘要“英雌”形象是晚清“新小说”所提供的一类独特人物面相,并呈现出强烈的民族国家叙事话语特征。从晚清到民元,在对“英雌”形象的“知识考古”中,不仅可以找寻出从性别“缺席”的“英雌”到性征鲜明的“女人”形象的嬗变谱系,亦可以梳理出从晚清的“英雌”到民元前后《妇女时报》中“女侠”形象的嬗变图谱,这一形象的嬗变必然牵动着其所隶属的民族国家叙述话语的改变。
关键词清末民初 英雌 嬗变 女性 女侠
在晚清救亡图存的时代语境中,女英雄,即“英雌”,不仅高频率、大规模地出现在报章新闻中,成为当时的流行语,而且也成为晚清“新小说”所提供的一类独特人物面相。在晚清译著模糊、混乱且富足的创作格局下,这类人物形象呈现出极大的活力,如半编半译的历史小说《东欧女豪杰》(岭南羽衣女士著)塑造了“若不用破坏手段,把从来旧制一切打破,断难造出世界真正的文明”①的女英雄苏菲亚形象,她以救世自任,组织革命团体,倡导工人革命,声张废除专制。小说的重心似乎不在于讲述女英雄的传奇经历,而在于政治观念的宣扬,诚如“谈虎客”所批:“此书特色在随处将学术政法原理横插叙入,令人读过一通,得了许多常识,非学有根柢者不能道其只字,即如此处说刑法原理,虽属至浅之义,亦中国人未曾见及者”②,尽管是要突出小说的独创性,但这种形式却早已在“新小说”的典型范本《新中国未来记》中预设好了;再如标注为“闺秀救国小说”并带有科幻色彩的《女娲石》(海天独啸子著),小说以金瑶瑟为中心,通过她的奇遇及与各色政党的接触来宣扬救国之理,金瑶瑟同样属于这类女英雄形象;再如历史小说《洗耻记》(汉国厌世者著,冷情女史述)中致力于民族独立的女性郑协花、迟柔花等,她们同男性形象一样不甘于异族的统治,“于是儿女念断,而起义之心决矣”③;再如托名译本的政治小说《瓜分惨祸预言记》(男儿轩辕正裔译述)塑造的夏震欧形象亦是如此,这些“英雌”形象共同表现出爱国救亡的民族国家叙事话语特征,以及冲锋陷阵、巾帼不让须眉的气魄和才智。
到了1911年,“新小说”的创作高峰早已过去,这类“英雌”形象却并没有完全退潮,我们依然可以在清末民初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妇女时报》所刊载的小说中找寻到与其相似的面孔。实际上,不惟此,在稍后的《礼拜六》杂志及其他鸳鸯蝴蝶派刊物,尤其是其刊载的翻译小说中,都能现出这种爱国女英雄的踪迹。尽管如此,“英雌”形象在延续晚清某些基本特征的同时,也表现出了显著的嬗变痕迹,这一进程是通过两种维度实现的。
一、从“英雌”到“女人”
晚清“新小说”中的“英雌”形象一心忙于救国,她们在表现出相似的国族叙事话语特征,以及巾帼不让须眉的气魄和才智的同时,作为女性的主要性征(形象、性、性格)也在强势的国族叙事主题下被遮蔽了,如政治小说《瓜分惨祸预言记》中塑造的女英雄形象夏震欧,面对沉重的国家、民族灾难,她宣称:“这中国就是我夫,如今中国亡了,便是我夫死了。这兴华邦是中国的分子,岂不是我夫的儿子么?我若嫁了人,不免分心”④,以此来弱化、消减自己的女性特征,这或许也为当代十七年文学中的无性写作提供了某些样板。
应当注意,晚清小说中的“英雌”形象呈现出的无性化写作特征,是因为“新小说”的时代语境决定了她们更多的是作为一个符码,以达到“群治”、“开智识”的社会功用,所以性别的指涉或刻意塑造的大批“英雌”形象,并非主要区分她们的非男性化特征和立意要突破男权的“逻各斯(logos)”中心,即“存在、本质、本源、真理、绝对”等宇宙事物的理性与规则,它们重在表达和期望的是全民族上下的每一个人,尤其是下至市井野民、村夫田老,都能在“开智识”的基础上最终实现民族危难的化解和富强,在这种意图下,女性完全会由一个无知、蒙昧的村妇,如黄绣球(《黄绣球》)在梦中聆听了法国罗兰夫人的宣讲后,便会开智识,晓得这世上的开化之势,到处演说,甚至会如夏震欧、郑协花、迟柔花那样成为革命运动的领袖。然而,与这种意图如影随形的必然是女性形象的提升和现代性特征的具备,这又不可避免地会冲击到男权的“逻格斯”中心,呈现出女权主义的特色,显然这是晚清小说写作中与创作意图呈现正向增长的附加值,而不是本质意图,于是可以看到,在国家、民族话语的叙述中女性的性征就会变得模糊,所以在呈现出突破男权“逻各斯”中心的倾向后,她们又悖论式地表现出对男权“逻各斯”中心的皈依,这种皈依的方式是通过对自己形象、身体性征的置换来实现的,即这类“英雌”形象更多的是作为男性形象及其话语特征进行表述的,所以作为符码本身并不区分性征,只是表明作为传统观念中亟待启蒙开化的一个弱势群体,在大的时代主题下需要被塑形、想象成一种国族视域下的正面形象,于是“英雌”形象更多的包含着一种政治、社会内涵,而作为文学、人性的内涵,在国族话语的叙述中,她们甚至将爱情、生育这些标志女性最本质的底线都抛弃了,最终完成了“英雌”与“英雄”的置换。
在国家、民族的救亡图存成为第一时代主题的语境中,晚清小说中的“英雌”形象影响、并延续到了处于相同语境中的《妇女时报》所刊载的鸳蝴派小说创作,特别是翻译小说,如周瘦鹃翻译的英国作家哈斯汀的小说《无名之女侠》(《妇女时报》第7号),塑造了与晚清小说中的夏震欧毫无二致的、反抗俄罗斯政府专制的女英雄形象;再如周瘦鹃的小说《爱国花》(《妇女时报》第3号)中的女主人公,面对异族的入侵,本邦国族身份的强烈认同感让她发出了“可恨女儿不是男子,若是男子,定必和那傲然自大的拿破仑,一决雌雄,杀他个双轮不近,保全我梯洛尔如火如荼的河山”⑤的呼声,于是她们在继承、延续晚清小说中“英雌”形象的同时,亦表现出了对男性身体想象与强力的向往。但是另一方面,《妇女时报》所刊载的鸳蝴派小说,特别是原创小说,在继承晚清“新小说”强烈的国族叙事话语及由这种话语直接衍生出的“英雌”形象的同时,又在悄然嬗变。
第一,还原并添加与男性互补、对立的女性自身的品格。首先,包括女性阴柔的形象之美,如“一个风姿绰约、娉娉婷婷的女郎,出落的杏腮舒霞,柳腰抱月,秋波盈盈,露出几分英气,真合着‘神如秋水,气若严霜’八个字”⑥,这就与威武雄强的晚清“英雌”形象的阳刚之美产生了较大的距离;其次,还包括她们在面对异族歧视、污蔑性话语:“亡国奴,速去休,勿污吾一片干净土。其速行,毋溷乃公为。脱不然,莫谓吾棒下无情也”⑦时,产生的源于民族自卑心理的无限感伤。于是,晚清“英雌”形象在临危之时的魄力与勇气:“父母俱逝,于是儿女念断,而起义之心决矣”⑧,开始消解、转换成“且行且泣,彷徨途次,血泪染成红杜鹃”或“一忆及国家多故,则觉鸟啼花落,无非取憎于己。泪珠盈盈,已湿透罗袖”⑨的忧郁与娇弱之气,这种浓郁的忧伤情绪弥漫字里行间,几近于十余年之后才出现的郁达夫的小说《沉沦》。
第二,“英雌”形象的大众时尚偶像制造。《妇女时报》通过其“编辑室”栏目征求以女子从军为题材的小说创作:“吾国女界不乏文豪,或能编述女子从军美谈,如小说体裁,或能迻译他国革命战争事件而关系女界者,尤为本志所盼望”⑩,来加强晚清“英雌”形象的塑形,并且充分利用近现代传播媒介中“形”的因素,即征求女军人照片:“吾女军人中,如能以玉照惠登本杂志,俾令英杰之姿,为世界所崇拜,尤为本志所祝”,进一步强化“英雌”形象的传播。这是否说明处于晚清“新小说”语境或者由晚清向民国过渡的语境中,以“英雌”形象为标识的晚清“新小说”时代的国族叙述话语与此时《妇女时报》语境中的国族叙述话语呈现出同构、同质性呢?单就其“编辑室”栏目中的征图、文启事来讲,这些举动反映了这一时期鸳蝴派多元价值取向的文化品格,首先,其国族叙述话语依然受到晚清“新小说”语境的影响,成为表征他们的一个重要面相。其次,存在着启蒙与时尚的边缘或者交叉点的问题,类似这种征文、征照片的行为预示着后来鸳蝴派发展的一个典型运作或生存方式,这也意味着他们在宣扬严肃国族话语的同时,却又暗含了某种消解的倾向,即向着迎合大众文化口味发展的可能,“英雌”或“女军人”形象亦可作为大众时尚的偶像被隆重制造,尽管它不同于后来《礼拜六》、《小说大观》等征集的妓女图片,但从征文内容的“玉照”、“崇拜”等软性词语来看,却分明见到了日后鸳蝴派发展的魅影,这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鸳蝴派的发展并不是从诞生起就轮廓分明,在历史语境的更替、发展中它经历了一个逐渐嬗变的过程。
第三,爱情由“缺席”到“在场”的叙事模式添加。在《妇女时报》刊载的小说创作中,“英雌”的形象及其国族叙述话语得到了继承与延续,如笔名为“泰兴梦炎”的小说《鹃花血》中的孟蕙莲,她以“新世界之女国民”自居,以“完成我国民之本分”自警,在感慨于“二亿女同胞奄奄无生气”与“今日何日,大势去矣,看江山如画,中原一发,日已西斜,雨横风狂,未知所极,甘心异族欺凌惯”中,展开了对男性身体与强力的置换与想象:“可有男儿愤不平,若辈茸,可笑人也,妾所以重君者,正为君青年志士,来日方长,本期携手同归,登帕米尔高原,长歌当哭,唤起国民魂性,不意为郎憔悴,辜负雄心,今将长别矣,愿郎整顿起爱国精神,男女本分,为支那演出风云阵,使妾亦得为文明大国鬼”,这些与晚清“英雌”形象的国族叙述毫无二致,但是孟蕙莲在言说国族叙事中的启蒙话语时,如“吾惜女界革命军固未剧耳,今缠足之害,知者十八九,而自由结婚之说,则群以为诟病,彼诚不知自由之权,男女得而有之,不专诸父母之谓也”,又自然过渡到了男女婚恋不自主的问题,这同样存在着一个边界与交叉的问题,它会使鸳蝴派依照自身的本性惯性式地生长出时代主旋律之外的、鸳蝴派之所以为鸳蝴派的另一种面相。在这里,婚姻自主的启蒙主旨却并非与时尚交叉,而是衍生出了婚恋不自主的言情叙事模式,这一模式在民初鸳蝴派的繁荣期反复续写,并为“五四”新文学家(如周作人)所论及。于是,晚清“新小说”中“英雌”形象的爱情“缺席”被理所当然地演化成此时及日后的“在场”,它不仅不能成为救国、革命的障碍、牵绊,以及精神盈余品,反而可以借言情表达爱国之思、弱国之伤,并且相得益彰,诚如小说《鹃花血》中所言:“弥宇宙不可遏,故不畏死,不畏苦,不畏人訾议,一意孤行,然后可以爱国,可以合群,可以犯天下之大难……胥由情乎鼓吹之,如蕙莲者,处家庭专制之时代,而爱情集注一点,愈深愈炽,歌哭无端,生死若忘,推斯情也,使为罗兰夫人可也,临没之言,慨当以慷,须眉宁不自愧耶?”再如周瘦鹃的另一部小说《落花怨》,同样是借言情表达爱国,固然黄女士的异域爱情及其颠簸遭际成为小说叙事的主线,但是黄女士的不幸又始终与“娟娟明月,印河山破碎之恨;飒飒悲风,起故国凄其之慨”的孱弱国民的处境、感伤纠结在一起,与“妾之魂化为明月,君之魂化为地球,辗转相随,万古不变,即至天荒地老,海枯石烂,而妾之魂犹绕君而行,不宁舍君他去也”的浓情密语相伴随的,是不能忘却的民族国家:
嗟乎吾夫,死矣死矣。滔滔流水,容知吾心。妾生不逢辰,生于中国,乃蒙吾夫遇吾厚,而自濒于难,虽粉身碎骨,不足以报万一。妾久怀死志,所以含耻偷生者,因未见故乡云树,死为异域鬼耳。今所吸者乃中国之空气,所居者乃中国之土地,生为中国之人,死为中国之鬼,如此江山,妾亦无所眷恋。与其生而受辱,不如拼此残生,以报吾夫,亦所以报祖国也。
此外,黄女士在濒死之际发出的呼声:“吾中国之同胞其谛听,脱长此在大梦中者,将为奴隶而不可得,彼犹太、波兰之亡国惨状,即我国写照图也”,以及作者以全知叙述人的身份进行叙述干预时,所标识的黄女士形象仍旧是“中国国民之前车也”这样的“英雌”话语,这就使得民族国家叙述话语与通俗的言情叙事元素在小说中平分秋色,并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从而与晚清“新小说”中的“英雌”形象及国族叙事产生了较大的距离,同时也为下一阶段鸳蝴派小说的嬗变与成型作好了准备。
二、从“英雌”到“女侠”
从晚清到民元,在对鸳蝴派及其小说的“知识考古”中,不仅可以找寻出从性别“缺席”的“英雌”到性征鲜明的“女人”形象的嬗变谱系,以显现出国族叙述话语及其面相在鸳蝴派身上的继承、延续以及变更,同样也可以梳理出从晚清的“英雌”到民元前后《妇女时报》中“女侠”形象嬗变的图谱,这为考察晚清到民初语境更迭中鸳蝴派国族话语及面相的嬗变提供了另一条殊途同归的路径。
晚清小说中“英雌”形象的诞生及其复制,与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女英雄形象相比,呈现出极大的不同。首先,时代语境的差异使晚清“英雌”形象的政治意义大于文学意义。一方面,这使晚清小说与传统叙事文学,如《木兰辞》,呈现为两种截然相反的叙事模式,前者是强烈的国家、民族认同意识支配个人的行动,同时又消解着与本邦认同意识无关的、甚至阻碍这种国族意识延展的私人化情感与行为,而后者则是个人化的情感支配国家、民族认同下“英雌”行为的产生(如花木兰的从军缘自基于血缘关系的传统儒家伦理的“孝”);另一方面,这也使得晚清“英雌”形象的创作数量尽管要远远超过中国传统文学史上的女英雄,却很难成为花木兰那样的文学经典。其次,晚清小说中的“英雌”形象带有明显的异域移植色彩。实际上,传统文学中的女英雄形象并未为晚清“英雌”形象的创造提供多少借鉴,因为这一形象的塑造更多地要符合一种国族意识,以实现“群治”的宗旨,于是晚清乃至民初小说家从“泰西”小说中找到了相似语境下,以俄国女虚无党人或法国罗兰夫人为原型、反抗政府专制与异族侵略压迫的这一类人物形象,并推崇有加,在翻译之余,他们开始了半编半译或托名译著的仿写,进而是带有西化色彩的本土化原创,从这些实验品来看,都明显地带有异国风情的味道。所以,晚清“新小说”中的“英雌”形象与传统文学中的女英雄呈现出的是一种断裂性。
在这一异域形象的横向移植中,既然要服从于“群治”的启蒙宗旨,“英雌”的形象必然要经过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只有通过具体可感的人物形象与紧张起伏的故事情节,并为大众所接受、认可,“新小说”的启蒙意旨才能最大限度的实现。显然“英雌”对于中国大众或被启蒙的受众来讲是一种陌生化的形象,于是晚清小说家将这一人物置换为“女豪杰”、“女侠”的称谓,并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宣称:“《水浒》以武侠胜,于我国民气大有关系,今社会中尚有余赐焉,然于妇女界,尚有余憾……欲求妇女之改革,则不得不输其武侠之思想,增其最新之智识”,像这种添加进传统文学中“豪杰”、“侠士”的精神元素与故事情节的做法,在晚清得到了刻意地倡导:
神州大地,向产英灵,不特燕赵之间,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已也。然中国旧史,向无义侠名。太史公编列《游侠传》,独取荆轲、聂政、朱家、郭解之徒,其大旨,以仗义报仇者近是。成败虽不足论人,然个人上之感恩知己,求其舍生敢死,关系于国家主义者,又不数睹,遂使数千年文明大陆,如东洋之武士道,能动人国家思想者,不啻流风阗(阒)寂焉。悲夫!圣经贤传,颓人气魄;即所谓稗官野史,又无以表彰之,又何怪哉!则虽欲不让小说为功臣不得也。毛宗冈编《三国演义》,金人瑞编《水浒传》,虽其中莽夫怪状,不无可议;而披览蜀魏之争,人知讨贼,逼上梁山之席,侠血填胸,社会之感情,有触动于不自觉者。况今日者,大地交通,殉国烈士,中西辉映。而其人其事,为小说家者又能运以离奇之笔、传以恳挚之思,稍有价值者,社会争欢迎焉。故比年以来,风气蓬勃,轻掷头颅,以博国事者,指不胜屈。即所谓下流社会者,亦群焉知人间有羞耻事。以是为义侠小说输贯之力,盖无多让焉。
实际上,这种置换的实现并不单单是基于一种启蒙民众的需求,这类中、西人物形象谱系的相似点也构成了置换发生的基础。“英雌”的元人物形象强调的是反抗政府专制与异族压迫,通过个人发动群体的力量,救国家、民族于危难,如异域人物苏菲亚(《东欧女豪杰》)以醒世救民为己任,组织革命团体,聚众演说,即使被捕入狱,也依然在乐观的精神下立志宣扬这个时代的共识:“用破坏手段,把从来旧制一切打破……造出世界真正的文明”。而作为传统文学中的“侠”,尽管强调的是一种个人精神与自由意志,与“英雄”被国家意志所肯定的传统儒家理想价值取向相区别,它代表的是一种民间理想价值取向,不服从于任何国家体制与社会力量的管制。但“侠”所呈现出的“义”,不顾个人安危、为民请命的精神,以及惩强扶弱、劫富济贫的正义感与民间道德责任感,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与“英雌”的国族形象找到了连接点,使二者有了对话与融合的可能,如《女娲石》中的女侠士金瑶瑟因痛于国难而刺杀慈禧太后,遂被通缉,走上了流亡之路,《东欧女豪杰》中的苏菲亚,因反对政府专制、宣扬工人革命被捕入狱等,就很难分清这种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救国救民的义举是一种基于个人的“侠士”之举,还是基于国家、民族认同意识的“英雄”行为。由此,在二者的连接点上,“侠士”所崇尚的个人精神会被毫无冲突地统摄进严肃悲壮的、隶属于“英雌”形象的国族话语的叙述中,如《瓜分惨祸预言记》中的女侠士夏震欧愤慨于清官的昏庸、洋人的屠戮,强烈的爱国意识使她认识到“若是没了国,任你有天大的才艺,他人也虐待迫逐,使你无处容身”,于是崇尚个人主义与以传统“忠君”思想为标识的国家意志相游离的“侠士”精神,在时代语境下,与忠君爱国的思想汇流并消解。所以我们看到,在晚清小说中,“英雌”与“女豪杰”或“侠女”的形象是等同的,这些概念在晚清小说家看来可以混同使用,如历史小说《洗耻记》第六回“话故事英雄挥泪,读碑文侠女灰心”,用“英雄”和“侠女”共同指涉小说中的“英雌”迟柔花与郑协花,闺秀救国小说《女娲石》第五回“捉女妖君主下诏,挥义拳侠女就擒”及第七回“刺民贼全国褫魂,谈宗旨二侠入党”,以“侠女”来指称小说中的女英雄金瑶瑟与凤葵。此外,我们也可以看到,“英雌”形象的横向移植是一个双向改造的过程,一方面,是异域“英雌”形象的本土化,即晚清小说家为其寻找本土化的、为大众熟知的形象“寄主”;另一方面,是传统“侠士”形象的异域化或者时代化,即统摄进以西方启蒙、救亡话语为主导的时代国族话语中,以此来完成晚清“英雌”形象的本土化制造。
随后到了《妇女时报》这个时期,“英雌”与“侠女”形象合二为一的局面被鸳蝴派作家改写了,这一形象的嬗变必然牵动着其所隶属的国家民族叙述话语的改变,也因此使《妇女时报》时期的鸳蝴派呈现出与晚清“新小说”相异的民族国家话语及其面相。
如前文所论,在《妇女时报》所刊载的小说中,我们能够很容易地找寻到通过添加或删减、嬗变了的“英雌”形象及其国族叙述话语,同时,我们也能很容易地找到“侠女”这一类形象,但是与晚清小说不同的是,“侠女”仅仅就是“侠女”,与“英雌”形象无关,即鸳蝴派作家将晚清小说中“侠女”与“英雌”合二为一的形象实现了一种剥离。《妇女时报》中“侠女”形象的产生并不以民族国家话语的表述为自己的形象特质,甚至可以说国族话语的叙述在“侠女”身上是“缺席”的,她们的形象特征被基于个人恩怨的复仇所标记,如小说《玉蟾蜍》(思蓼,《妇女时报》第3号)塑造了“柔情侠骨”的碧秋形象,其身上没有丝毫地呈现在这一时期延续下来的晚清“新小说”的国族叙述话语特征,侠女碧秋仅仅是基于“孝”而为父复仇,构成其复仇障碍的也只是言情元素的掺入,在爱与恨的冲突与焦虑中,完成了游离在时代国族话语之外的“女侠”形象的塑造。这一形象也为同期或稍后的鸳蝴派小说所继承,如《桃花劫》(梦,《小说时报》第1年第1号)中的越女,因同情被游学所成的丈夫抛弃的刘碧桃,侠义惩治轻佻伪善的碧桃丈夫魏琴声;《绛衣女》(梦,《小说时报》第1年第3号)中的郑秋菊,嫉恶如仇,只身潜入虎穴,力搏盗墓贼,最终也赢得了黄生的倾慕;《女儿红》(吴双热,《民权素》第3集)中的女儿红,武艺卓绝,因不满其兄杀人越货,怜悯回乡探母病的书生而大义灭亲、救人于危难;再如侠烈小说《贞姑》(胡仪,《小说丛报》第13期)中的贞姑,尽管没有骄人的武功,这使其作为“侠女”的形象受到了动摇,但是她勇敢地站出来当堂对质揭发淫僧污三十人清白而后自尽的义举,依然实现了“侠”的精神风貌,因此作者也承认:“设非此侠烈之女,彼被污之三十余人,皆抱不洁之名以死”。
总之,在“英雌”形象与“侠女”形象发生剥离之后,“英雌”的形象仅仅存在于翻译小说或以嬗变的形态存在于鸳蝴派原创小说中,并且在新的时代语境的更迭中,这类形象也逐渐地走向尽头。而“侠女”形象的还原与改造却呈现出鸳蝴派发展的一个重要图景,在剥离掉国家、民族的重负后,它沉潜到了私人化的情感层面,随着这一形象不断发展、完善与武侠小说在20世纪20、30年代的日臻成熟,以“玉娇龙”(王度庐《卧虎藏龙》)为表征的新一代女侠继承发展了这一套路,并在爱恨情仇中深刻地诠释“女侠”形象与性格的丰富性,这也成为鸳蝴派文学贡献给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类独特人物面相。当然,“英雌”与“侠女”两类形象的剥离或者说“侠女”形象的“祛魅”,尽管表明了鸳蝴派国族话语及其面相在《妇女时报》时期的消解,但这并不等于其在鸳蝴派身上消失,“英雌”形象的其他嬗变形态同样表征着这类形象及其统摄话语的存在与不能轻易被遗忘,而且进入民初后,鸳蝴派国族叙述话语及其面相还将会以其他方式呈现出嬗变,这一进程还远未结束。
注:
⑤⑥ 周瘦鹃《爱国花》,《妇女时报》第3号,宣统三年八月朔日(1911年9月22日)。
*本文系济南大学博士基金资助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