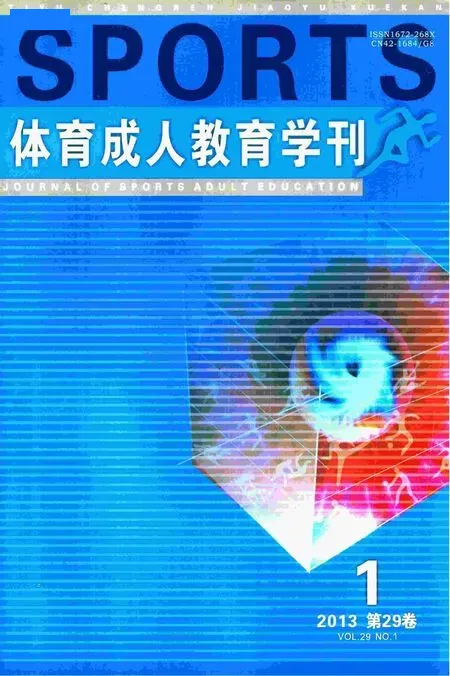新闻媒体建构国家认同的价值发现*——伦敦奥运会国际媒体报道案例
黄 璐
(河北理工大学 体育部,河北 唐山 063009)
全球化使人的身体存在与物质生活紧密联结在一起,国家边界的判断依据更多的是自我身份的界定与认同,强大的国家需要忠诚的人民,自我对家园的感情、对国家的认知构筑了后现代国家的文化根基。新闻媒体在国家概念认知与自我身份认同之间架起了心灵沟通的桥梁,不断反复地进行内容生产和主题报道,建构国家认同的当代神话。这就好比说,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付出了巨大努力,这种积极努力并不等同于民众的认可,真实发生的事件与民众认知之间存在信息转换区域,新闻工作做得好则如虎添翼,“好事”放大形成广泛共鸣,做不好则适得其反,“好事”反而受到民众普遍质疑。奥运竞技最显著的特点是身体竞争,区分“我”和“你”,更要分出高下,这为建构国家认同提供了天然素材。每逢全球重大体育赛事,必是诸国媒体挖空心思、大做文章的时候,2012年伦敦奥运会国际媒体报道提供了鲜活的分析案例。
1 奖牌榜传播中的国家认同价值发现
奥运会奖牌榜(Medal Count)反映各国代表团的总体实力,表征国家政治经济与科技的国际地位,历来受到国际媒体与政治的追捧与关注,奥运竞技是一场竞争白炽化的奖牌榜媒体战争。现代奥运会继承创新了古奥运会的比赛形式和仪式特点,坚持独树一帜的奥林匹克精神价值观,造就了目前奥运会的世界首要赛事地位。为突出奥林匹克价值体系,保持奥运会赖以生存发展(精神纯粹性)的赛事核心竞争力,淡化民族主义和锦标主义色彩,体现重在参与和享受比赛的奥林匹克精神,国际奥委会在名义上不主张任何形式的国家团体总分排名。但是升国旗奏国歌的民族主义仪式已经明确说明奥运会是国家间的竞争,国际奥委会只是在形式上进行“去官方化”的努力,把奖牌榜的评价权力和争论交给“民间”。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态度,让世界诸国媒体找到了奥运会国家排名的“兴奋点”,极力倡导奥运会国家团体总分排名,展现基于自身特点的“国家强大”内容。媒体在事件与民众间扮演的桥梁中介角色,兼具官方诉求和民间属性的双重色彩,既能实现官方对“国家强大”议程设置和主题叙事的要求,又能体现民间的大众狂欢和娱乐至死精神。奥运会奖牌榜媒体宣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例如伦敦奥运会英国代表团开局战绩不佳,BBC干脆在首页撤掉了奖牌榜,来减少比赛成绩对国家形象和国民心理的负面影响。美国媒体为了“战胜”中国,CNN—体育画报合作网站修改了奖牌榜排名规则,排序方式反复在金牌和奖牌总数间变换,并且发生篡改奖牌榜的行为,以表现美国代表团的实力和“国家强大”的内容[1-2]。
从理论上来说,奥运会存在金牌制、奖牌制、计分制、人均奖牌制等国家团体排名方式。金牌制依次以国家金、银、铜数(金牌并列则看银牌数)的多少排列名次,奖牌制以国家金、银、铜牌数的总和排列名次,计分制按照一定的计分规则进行团体总分排名,人均奖牌制以国家奖牌总数与国家人口基数的数值关系进行排名。金牌排名制体现了国家团体的绝对竞技实力,奖牌排名制和计分排名制体现了国家团体的整体竞技实力,人均奖牌制体现了国家人均奖牌效率。从媒体实践上来说,由于计分制的计分规则种类繁多,并未形成共识,而人均奖牌制又不尽合理,国际上形成了以金牌制为主,奖牌制为辅的排名格局。金牌制体现绝对竞技实力,排名规则简单明晰,获得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可。而奖牌制存在一定争议,因为排名的基本原则是要明辨实力差距,在统计学上淡化金牌的竞技优势,不符合排名的基本原则,并且取前三和取前八均能反映国家整体竞技实力,这就让奖牌制成为一种间接的计分制。事实上,目前实行奖牌制的国家媒体较少,主要动机取决于本国在奖牌数上是否具有排名优势这一因素。例如北京奥运会中国金牌数超越美国,美国主要媒体放弃了一以贯之的金牌排名制,《纽约时报》迅速更新了奖牌数据库。再如德国受到中国、美国、俄罗斯的竞争强势影响,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德国“金牌拿不到、奖牌一箩筐”的局面,为体现奖牌数对“国家强大”形象的建构作用,德国《明镜周刊》近两届奥运会启用奖牌排名制。诸国媒体普遍选择扬长避短式的奖牌榜报道策略,力求建构一个民族国家想象的话语共谋和文化认同,拥有强势话语权的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得以实现跨文化的国际传播[3]。
2 体育明星报道中的国家认同价值发现
报业翘楚《纽约时报》对体育明星报道中的种族身份叙事给予了较大关注,表征与发挥美国种族政策风向标的作用,为美国种族融合神话和社会团结提供话语支持。从迈克尔·乔丹、泰格·伍兹、齐达内到林书豪,种族问题一直是媒体政治极力营造的神话主题,亦是无身份边界的后现代国家必须攻克的文化难题。如高尔夫球星泰格·伍兹,一个“精心包装”和“细心打造”的媒介化典型形象,从他已故父亲厄尔·伍兹的严格教导(美国传统家庭的形象),到泰格·伍兹不关心政治,并且明显带有白人化倾向的媒体形象,这种“迈克尔·乔丹化”的陈旧叙事模式背后隐藏的媒体政治动机,有必要进行批判性反思[4]。种族多元化政策惟有在符合白人中心论的精神前提下,在契合美国生活方式的表现框架下,才能进入媒体报道视野,是典型的“香蕉人”报道模式。道格拉斯摘得伦敦奥运会体操女子个人全能项目桂冠,成为奥运史上首位夺得该项冠军的黑人运动员,小威廉姆斯摘得网球女单桂冠,实现职业生涯金满贯的骄人成绩,《纽约时报》在网站主页的奥运专题栏目上进行浓墨重彩。这是黑人运动员的胜利,也是美国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胜利,即“非洲人美国造”,具有黑人的种族外表,美国白人化的行为和价值观。黑人运动员报道的国家认同价值发现,一是报道策略上避重就轻,重点报道运动员的个人成就,淡化金牌榜暂时落后于中国的事实。二是报道突出美国优越论,成就黑人体育明星的是美国政治经济、教育与多元文化制度,是崇尚改变与创新的美国价值观。
即便单一的政治经济专业媒体并未将奥运报道放在重要位置,却积极配合国家一盘棋的舆论战略,这种甘做螺丝钉的媒体精神,不仅在金牌社会效应的舆论宣传上竭尽心力,并结合专业媒体定位的价值视角建构奇观叙事。《大西洋月刊》定位于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精英读者,追求客观中立和深度评论的美国观点,该刊网站在伦敦奥运会第8个比赛日头条刊登了菲尔普斯的图文报道,显示了明星运动员带给美国社会团结和政治发展的积极影响。菲尔普斯的竞技传奇形象生动的表达了个人主义式的资本主义精神,通过个人勤奋努力实现个人成就梦想,应得与个人成就对等的财富和地位。《大西洋月刊》藉此焦点事件,发出美国政治为保障公民发展权利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的强烈信号,建立美国政治在国内的认同和在国际的影响。
《时代》杂志具有分类化的广泛主题和国际化的发展定位两大特点,在道格拉斯以绝对实力夺得伦敦奥运会体操女子个人全能冠军之后,《时代》杂志并未把镁光灯聚焦在新科冠军道格拉斯身上,而是在网站主页显赫位置宣传报道华裔教练乔良。这种对幕后英雄和少数族裔的重点关注,表达了人人生而平等的普适价值理念,为美国在国内塑造民主自由、文化多元、种族平等的核心价值观,在国际上建立尊重文化种族差异的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具有积极的舆论宣传效果。《时代》杂志践行差异化报道的幕后动机昭然若揭,不与《纽约时报》竞争主流报道,不与地方小报竞争娱乐解读,选择价值立场,抓准报道重心,发现与放大突发公共事件的国家认同价值,甘做报业评论中的“螺丝钉”。面对如此有价值发现的新闻报道,要求我们对某些“做文章”的体育新闻持质疑态度,调查问责体育领域里的强权和随之产生的政治和商业文化将愈加迫切[5]。
3 “他者”形象建构中的国家认同价值发现
奥运媒体传播是一种透过奥运文化认知国家社会发展和理解人自身的过程[6],奥运文化的不同类型——古希腊原版、美国文化版、中华文化版等,代表了不同的话语权力、国际影响和文化软实力,蕴涵不同的文化叙事与国家身份。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当今世界竞技体育头号强国,这种事实必须与民众的认知划等号,国家实力与国家认同(硬实力和软实力)共同实现且合二为一。媒体惟有不断地界定与建构“他者”形象,才能有效地建立个人认知与国家概念之间的身份关系,建立名副其实的强国形象与认同。
刘翔摘得雅典奥运会110m栏桂冠,中国媒体在民族主义情绪调动下群起围观,刘翔摇身变为家喻户晓的商业巨星和民族英雄,西方媒体难以理解黄种人统治高速赛道的事实,给予了平常心报道。由于伤病原因退赛,这在残酷的精英竞技中司空见惯,北京奥运会和伦敦奥运会刘翔退赛事件,西方媒体反而投入了极大热情,表现出遗憾和嘲讽的腔调。《泰晤士报》网络版的新闻报道具有代表性(题名为Liu Xiang withdrawal was a crying shame for China,文章现已删除),评论称“谁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再看见他?中国的奥运明星昨天闪烁了一会儿就迅速地回到了黑暗中。”东方世界在田径项目上历来表现萎靡,刘翔的出现对西方意识形态话语中的制度、文化和种族优越论形成了观念冲击,刘翔退赛事件是重建西方国家认同和重振西方优越论威风的千载难逢机会。北京奥运会刘翔退赛事件的负面报道力度堪比美国民族英雄菲尔普斯,我们表现怎样,他们表现怎样,只有在二者的鲜明对比中,才能理解国家的优势力量,建立国家的强大形象,塑造国家的身份认同。西方媒体顺势反戈一击,新闻隐喻的巧妙运用将刘翔形象回溯至雅典奥运,“雅典赛场的欢呼声是那么遥远”、“一闪光又回到了黑暗中”、“那些荣誉好像没有发生”等比较性话语,刘翔雅典奥运夺冠被西方媒体政治描述为随机事件,一个诸多偶然因素的集合反映。蔚为壮观的尚有“后院起火”,中国媒体从“悲情论”到“阴谋论”[7],一派鲁迅笔下的“看客”嘴脸,具有中国特色的自嘲、自惭、自贱的民族与媒体心态值得反思。
在一个长期由西方世界主导的奥运基础大项中,孙杨、叶诗文、焦刘洋的泳池竞技表现令人印象深刻,而美国昔日泳坛巨星菲尔普斯则出师不利,西方媒体试图塑造“他者”的负面形象,来比较与衬托“自我”的强大。西方世界在未取得任何事实依据的前提下,散布有关叶诗文服用兴奋剂,并且带有明显话语攻击倾向的猜测和质疑。西方媒体人首先发难,训练专家遂即做出经验描述,《自然》杂志进行补充论证,组成“媒体—训练—科研”三重质疑链条,由叶诗文个人的评价上升到中国身份或国家角色的合法性存在层面[8],藉此消解优异成绩的事实预期产生的国家认同效果。叶诗文夺金事件有力佐证了中国竞技体育优势项目的结构性转型带来的积极变化,这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结构优化调整的国际形象联系紧密;运动员年轻化趋势透视出中国强大的后备力量储备和未来发展潜力,这与中国经济与社会强劲的发展势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联系紧密,这些中国叙事都是西方媒体感到不安并极力掩盖的事实隐喻。
需要注意的是,西方媒体政治中的“他者”话语,是一个广阔的话语叙事范畴,不仅与之强劲的竞争对手中国针锋相对,一切既成思维定势的西方统治项目,由此衍生出的可能危及西方国家认同的潜在因素,均在新闻价值发现的评估范畴。博尔特打破尘封多年的美国高速赛道神话,迎接爆棚式的兴奋剂质疑声洗礼,从博尔特那无奈的抱怨和那无助的神情得以启迪,我们的新闻媒体在体育赛事报道建构国家认同问题上,需要下更大的功夫,付出更多的努力。
[1]田秋霞,胡娅娟.金牌榜传播:话语权博弈和文化认同[J].青年记者,2008(3):9-10.
[2]Pamela C.Laucella.Review on“Handbook of Sports and Media”[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 Communication,2008(1):404-408.
[3]刘红霞.数字化时代体育新闻传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5(5):67-70.
[4]冯霞.北京奥运文化传播的特点、性质及其对国家形象的塑造[J].新闻界,2008(2):79-80.
[5]常江.2012伦敦奥运会热点事件中的媒体景观[J].新闻界,2012(3):35-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