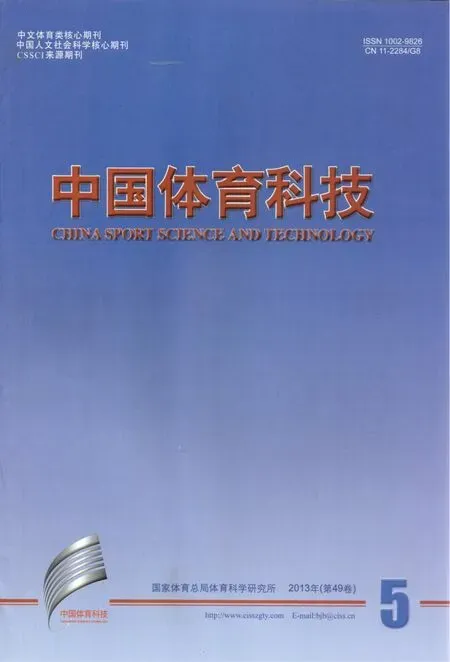竞技武术是一项现代体育运动项目吗?——在古特曼现代体育特征体系下对竞技武术的再审视
赵 岷,李金龙
1.Shanxi University,Taiyuan 030006,China;2.Shanxi Datong University,Datong 037009,China.
1 由古特曼相关著作引发的思考
1979年,阿伦·古特曼出版了《从仪式到记录:现代体育的本质》一书,书中阿伦·古特曼归纳总结出“现代体育具有7种特征,从而定义了现代体育。作为‘理想形式’,现代体育是世俗的、平等主义的、理性的、科层化的、专门化的、量化的并且对纪录的追求特别痴迷。[1]”奥林匹克运动会可以说是现代体育的最高代表,作为中国传统体育中现代化程度较高的竞技武术,2008年却与奥运会擦肩而过。武术工作者虽不断分析国内、外各种影响因素,但终究无法改变竞技武术未能进入奥林匹克运动体系的事实。如果抛开所有外在因素,单就现代化程度进行分析,竞技武术是否符合古特曼所提出的现代体育7大特征呢?如果竞技武术的现代化程度不足,不具备现代体育运动所必须的因素,那么,它又如何能够进入世界现代体育行列,并为奥林匹克运动体系所接纳呢?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现代化程度的高低直接决定着竞技武术未来的发展走向。
当然,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非要用古特曼的现代体育理论来审视竞技武术,而不是用其他人的理论?难道只有古特曼的理论才是正确的?”理由正如袁旦所述,古特曼并不是简单地堆砌概念,也不是从一个定义到另一个定义,而是“就像现象学所说的‘回到事实本身’,通过叙述古今一些个体和族群生活中的本能游戏和祭祀仪式、艺术表演和体育竞赛的史实故事,从叙述过程中显现出人性深处那种创造古今体育的原始思维,正是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抽象和概括出了现代体育的本质和本质特征。他这本书的标题就是‘现代体育的本质’,他仅从体育属于人的游戏这一不证自明的常识出发,在叙事中展示出人类体育从本能的游戏(play)到人类有组织的游戏(game)这个体育起源的必然性,展示出古代或前工业社会的体育(如果说是体育的话)到现代体育这种文化演进的历史必然性,从而给出了现代体育的本质的定义。……这种有影响的成果,至少我是未曾见到的。[21]”当然,也不是说古特曼的现代体育理论就是完美无缺的,本研究只是借助古特曼的理论来审视竞技武术是否符合现代体育运动所必须具备的几个极其重要的特征条件。随着社会的发展,今天之世界已经不再是一个封闭的、平面的、独立的世界,而是开放的、立体的、相互联系的世界。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任何体育项目根本无法在封闭的空间中独善其身,只有勇敢地走出去,相互交流才能发展壮大自己,成为一项全世界人民喜爱的体育项目。正因如此,才要借助于古特曼提出的现代体育七大特征来考察竞技武术距离现代体育项目有多远,还存在哪些不足,需要做哪些改进,确立怎样的现代理念。惟有如此,竞技武术才能真正成为现代体育大家庭中的一员,从而才能真正输出自己纯正的具有东方特色的技击、养生理念,获得真正广阔的发展空间。
2 对竞技武术七大特征的剖析
2.1 竞技武术的世俗性
古特曼明确指出“现代体育的第一显著特征是现代体育比原始体育和古代体育更加世俗化[1]”。“现代体育变成一种世俗信仰的倾向,是原始仪式到世界系列赛,再到世界杯漫长而迂回的道路上最奇特转变之一[1]。”古特曼对世俗的强调是同“神圣”相联系的,其书中标题便是“The sacred and the secular”(神圣与世俗)。古代体育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宗教背景,无论是古希腊以祭祀大神宙斯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还是美国西南部的吉卡里拉阿伯切人用“体育”和太阳-月亮的符号体系来作为每年丰收仪式的一部分[1]。神圣的宗教信仰更多是维护体育活动的精神纽带,所以,在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看不到女性观众,同时,也没有女性运动员参加,惟一例外的德尔菲神庙(Demeter)女性神职人员则是作为神的仆役出现,拒绝女性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在这里显然是一个全民必须共同遵守的神圣信仰。当然,古希腊的妇女并不是不运动,她们有自己的运动会——赫拉运动会,参加者全部为女性。因此,从这一点看,古代体育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其对神圣世界的信仰与尊重。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增长,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已经走出了先验世界,特别是,随着近代科技体系的发展,过去那种单纯依靠宗教信仰维持的世界已经坍塌。轰轰作响的工业列车带领着人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冲向理性的彼岸,过去的神圣世界成为车窗外的风景,人们已经完全进入了一个由“人”组成的世界,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完全世俗的世界。世俗性变成这个时代最大的标识,体育自然也如同古特曼所言:“无论人们是否将现代体育的热情、仪式以及神话看成是一种世俗宗教,其与原始体育和古代体育的根本性差别仍然存在。世俗与神圣的联系已经割断,对于超验世界的依恋也已经断绝。现代体育一方面是为自身目的而进行的活动;另一方面也是为其他世俗的目的而举行的。现代化不会因为祈求大地丰收而赛跑。我们的工作与休闲彼此分离,时空断裂。[1]”这就是现代体育与古代体育最大的不同。
就竞技武术的发展来看,由于近代列强的入侵使得中华武学赖以生存的农耕文化空间突然断裂,在少部分人的主动和绝大多数人的被动之间,在彷徨不安、踌躇不定、左右摇摆之间,中国武术被猛然抛上了现代化的列车。之前的种种不适应与之后时局的无形催逼直接将中国武术一条粗绳拉扯成竞技武术和传统武术两根单线。这种生硬的二分法不但直接降低了武术的文化合力,也使得竞技武术现代发展之路变得极为艰辛坎坷。可以说,竞技武术与传统武术都没有完全做好“世俗化”的准备工作。虽然,中国武术没有奥林匹克祭祀运动会那样的宗教源头,但并不是说中国武术从一开始就没有先验色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五行、八卦、经络等这些极具东方色彩的,且大多以感性体验为主的理论学说构成了传统武术的文化基石,成为中国传统武术的“神圣理论”。目前,虽然不能完全摒弃这些东方特色理论,但如果同西方现代体育理论进行比较,就会明显感觉到这些理论的神秘性,难以通过现代科学技术加以验证。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石是西方的现代科学理论,正是由于这种理论体系的世俗化发展,才使得今天全世界人类可以共享这一体系带来的全新生活方式。现代体育的发展完全是建立在这些科学理论基础之上的,因此,导源于西方宗教体系下的奥林匹克祭祀性质的竞技赛会,最后演变为今天全球性的、极具世俗意义的体育竞技盛会。
现代科学理论体系是现代体育世俗化的一个前提条件。就竞技武术而言,由于其生成发展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当中,又生硬地按照西方现代体育模式强行在传统武术的基础上构建起自己的竞技体系,这样的结果是,虽然其技术体系按照西方竞技体育模式框架搭建起来,但其最基本的基础性理论却依然停留在传统文化理论体系之中。特别是,中国传统学说几乎完全是依照东方化的思维体系构建的,与西方科学理论重量化实证、技术检验、逻辑推导似乎格格不入。以中国武术传统理论中最基本的“经络学说”而言,在人体科学如此发达的当代,至今没有哪个实验可以清晰地将其呈现出来。中国传统武学理论中的阴阳、五行等基本概念术语,也很难用西方化的理念进行完全对等的表述与解读。旧有理论无法用现代理论解释,现有技术体系又不能完全按照西方理论体系构建,这样就使得扎根于传统理论的竞技武术总要借助于西方化的理论模式去表达,最终的结果是竞技武术处于传统与现代的双重困境中不能解脱。
当然,不是说所有中国传统武术学说理论都没有一点科学根基,只是在科技教育如此发达的今天,如果依然延用传统的阴阳五行、太极八卦学说来解释武术,不但西方人接受不了,就是现代中国人恐怕也很难理解,这对竞技武术的普及与推广,自然也就成为一种阻碍和屏障。因此,从这一点来看,竞技武术的世俗化还没有彻底完成,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2.2 竞技武术的平等性
现代体育的第2项重要特征就是平等性。古特曼认为:“现代体育的第2个特征则是两层含义上的平等:1)每个人在理论上都有比赛的机会;2)对于竞赛者来说,比赛条件是同等的。在实际经验中,有诸多的不平等,当我们抛开理想形式直面现实的时候,我们总是被琐碎事物牵绊着。然而,根本性的原则是明晰的,现代体育存在于平等的假设条件之下。”[1]古特曼从阶级不平等、业余与专业的不平等到阶级隔离、种族隔离以及性别隔离等诸多现象中提炼出现代体育是一种理想上的平等。粗略看来,竞技武术完全符合这种平等性,但如果深入剖析却会发现,即便在这一点上竞技武术依然有许多值得思考和改进的地方。
竞技武术从宏观体系上分为散打和套路两个大项,散打是近似西方拳击搏斗项目,从赛制、体重,甚至是拳套护具都极显其平等性。套路项目上这种平等性就出现了较大的倾斜,特别是竞技武术套路中拳种的选择上就存在偏倾。中国武术历来以“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著称,由于历史发展的繁杂性和多变性,中国武术每个拳种几乎都有着不同的门派和风格。这种门户流派由于受到中国传统“正名”思维的影响,又大多以最本真、最传统的姿态自居,再加上空间的地域分割、时间的自我演化和人为的动作改变等种种因素共同构成了武术拳种的繁杂化。这种繁杂的拳种关系本应需要较长时间的梳理、论证、研究,才可能编排出一个大家大致都能认可的技术套路。但是,竞技武术套路由于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这些基本工作做的较少,在较为匆忙的情况下编辑而成的套路技术体系自然难以完全做到平等地对待每一个拳种流派及其技术动作,随之就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技术问题。现在竞技武术套路动作体系依然在应用,但在这一点上仍需要进一步改进。
竞技武术发端于传统武术,其传承体系上自然也会带有一定的传统特性。典型如师徒关系,传统武术谚语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特别是,在祖先崇拜如此盛行的中国,师傅与徒弟从来少有真正的平等,这固然有传统文化的影响,但也不能排除武术这一特殊运动的技术本质因素的影响。中国武术被称为功夫,也就是说没有一定时间的磨练很难达到一定水平与高度,由于技术掌握程度和技术体验的不平等性,无形中就增强了师傅与徒弟在技术体系上的不对等。这种不对等反映在人际关系上就是一种不平等。这种师徒传承体系与西方体育中的教练员、运动员体系有着极大的不同,再加上传统理念中的师门之情、同宗之意,都在无形中影响着竞技武术的评判体系。正如古特曼说:“平等与成绩原则之间的关系是极为重要的[1]。”很显然,竞技武术在这一点上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2.3 竞技武术的专业化
现代体育第3个大的特征就是专业化。用古特曼的话来说:“谈到现代体育的内部逻辑,专业化和职业化是不可避免的课题。在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两者是相同的。正如我们在谈到平等原则和业余原则时所说的那样,职业化的核心要素不是金钱而是时间——一个人将一生中多少时间投入到体育训练中去?换句话说,一个人的技能到底专业化到何种程度?正因为各个体育项目中的竞技成绩与任何一项中的最高水平都无法相比,这就使得专业化的领域越来越细化。尽管我这里所用到的‘职业化’这一专业术语还是遵循其普通含义,用来描述那些公开接受金钱补偿的运动员,事实上,这种职业的本质在于,运动员专业化程度达到将单个运动技能的不断提高当作自己相当长时期内的主要目标。[1]”相对而言,竞技武术体系在专业化这一领域做的较好,因为,它所处的体制是以全国之力来培养竞技武术运动员,这些运动员每天所要做的就是训练,然后是参加比赛。虽然,现行的体制近年来略有变动,但其根本目标和基本职责并未改变,这在时间和经济层面都促使竞技武术运动员成为全职性的专业运动员。
当然,正如古特曼指出的那样,“伴随现代体育领域专业化的是精密的人事支持系统[1]。”西方现代体育的专业人事划分系统是一种社会发展的本能性自发需要,一切按照社会的需要而设置,虽然有部分人为因素,但总体而言,更多是社会自然形成的。而我国竞技武术设置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将竞技武术推入奥运会,一旦竞技武术难以进入奥运会体系,这些专业运动员的出路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然,这种现象不独在竞技武术界存在,如何解决这些专业运动员退役之后的出路问题,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社会性的问题,影响着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
2.4 竞技武术的理性化
比赛必须要有规则,即使是在原始体育中也是如此,从体育的本质来讲,它属于有组织、有规则的游戏。除了原始社会的规则以外,比赛规则的性质比规则的数量更能奠定现代体育规则的基础。规则的起源和地位各不相同。现代体育在马克斯·韦伯的目的理性观念中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即手段和目的之间存在着一种逻辑关系。为了做这件事,我们必须做那件事。游戏的规则对于我们来说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更重要的是,只要当参与者感觉到游戏的方便比原始规则的保守更为重要的时候,新规则就会被发明,而旧规则就会被舍弃[1]。理性化可以说是现代体育项目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特征。从西方的发展历史来看,理性精神的确立对推动西方文明的发展,甚至整个人类的发展起着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时至今日,这种理性精神依然隐匿于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体系当中。当然,作为人类文明成果之一的现代体育也必然包含着深刻的理性特征。比如,篮球是美国马萨诸塞州春田市基督教青年会体育教师奈·史密斯先生在1891年发明的,之后迅速传播至全球流行。篮球是一项有意识的发明,是一件经设计——使用——再设计的文化艺术品,象征着游戏理性化的胜利[1]。可以说,理性化是所有体育项目发展的关键,现代体育中诸多项目的发展历程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纵观竞技武术发展历程,实质上体现出的是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近代理性思潮的影响下,不断向世界主体发展潮流接近的一个过程。竞技武术这一发展方向与中国社会巨大变革轨迹相一致。传统武术诞生于封建体制下的农耕文明体系当中,其内在思维模式以感性思维为主,外显的评判方式则以“擂台比武式”以命相搏和“点到即止”的主观体验式比试为主。评价标准中还夹杂着大量类似为人处世式的道德品性判断,这种将个人品质和主观体验杂揉在一起的评判方式显然与西方所极力倡导的理性体系有着巨大的差异性。因此,从近代以来,改造传统武术使其更符合世界体育发展潮流的呼声一直没有停息过。新中国成立以后,各种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作为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性质、地位、目的和作用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在此背景下,竞技武术从传统武术中抽离出来,特别是,1958年9月,中国武术协会成立后,邀请一些经验丰富的武术工作者制定了中国第一部《武术竞赛规则》,并在1959年的全国青少年运动会和第1届全国运动会上正式执行[3]。这一规则的出台标志着竞技武术理性化改革的全面启动。
“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就是要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有效配置全国的竞技体育资源,上下形成合力,提高竞技体育水平,创造优异运动成绩,为国争光[15]。”由此可见,竞技武术改革方向更多体现出的是一种行政体系下的主观人为性,对项目本身的理性特征挖掘不够。因此,在随后的发展中竞技武术一直处于左右为难的状态。从现代角度而言,由于竞技武术理性化程度不足,难以在世界范围内大面积推广普及,在进入奥运会体系过程中屡屡受挫;而从传统角度而言,竞技武术背离了传统武术的习练方式和传承体系,走的是完全西方化的道路,为广大传统武术爱好者所不理解。这种以官方形式创立的竞技武术更多体现出的是行政意志而非武术本身理性发展要求,使得竞技武术在后期的发展过程中,无论从比赛规则还是技术动作都似乎距离现代体育项目的理性化要求越来越远。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以“长拳”为主的竞技武术套路愈走愈远,最后形成一个宏大而奇异的技术体系。竞技武术最终在“高、难、美、新、稳”的指导思想下,日益缺失武术本身所具有理性特征,成为一种体操化、舞蹈化、艺术化、表演化的武术。究其根本原因,在于竞技武术从诞生起就不是以理性的精神来构建自己的技术体系,更多体现出行政行为和国家意志。
2.5 竞技武术的科层化
古特曼认为,“在实际操作中,谁来决定现代体育的规则以及是谁来管理复杂的研究机构呢?答案是很明显的——一个科层组织。同样,我们应该关注到马克斯·韦伯关于规则行为的原始等级制度与角色分工的现代科层组织之间的区别的分析。[1]”科层系统最重要的功能,首先,就是保证规章制度的普遍适用性;其次,则是必须使比赛的网络结构易于操作,这些比赛通常是自下而上从地方比赛开始发展,然后通过国家级比赛直至世界级比赛。体育联盟还有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功能,即对纪录的批准与认可[1]。由于现代体育运动绝大多数导源于西方,因此,这种发展模式是以西方的体育管理体制推导出来的,西方由于其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宏观的市场调控能力、各式各样的俱乐部管理模式和职业联盟体系,从不同层面构筑起立体、高效的自下而上的科层化管理体系。
中国竞技武术科层化管理体系是一种自上而下垂直管理,这种管理体制实质是中国竞技体育宏观管理体制。1955年,国家体委在运动司下设武术科,专门负责武术工作。之后,又将武术科升格为武术处,负责国家对武术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和武术的普及推广、组织竞赛等工作;并指导各地群众组织的武术活动[3]。1956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运动竞赛制度暂行规定(草案)》把武术列为表演项目,定期举行,这是竞技武术由传统武术走向正式比赛项目的第1步。有研究认为,“竞技武术的发韧,正是从建立运动制度开始的[23]。”1958年,成立中国武术协会全面负责中国武术管理工作。1990年,国家体委下发了《关于中国武术协会实体化的通知》,中国武术协会正式成为国家体委(现国家体育总局)直属事业单位,其行政职能进一步明确。1994年,国家体委又下发了《关于国家体委武术协会更名为国家体委武术运动管理中心的通知》,明确规定了武术管理中心为国家体委直属事业单位;同时,又是中国武术协会的常设办事机构,并赋予其对武术运动项目的全面管理职能[3]。其资金来源主要依靠政府拨款,其管理部门也是各级行政机构,财力、物力和人力等资源的分配调节也大多由政府管理部门依靠行政手段完成,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管理操作系统。
竞技武术这种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与西方现代体育自下而上的科层管理体制有着巨大的差别。首先,自上而下的管理体系,越往下其行政控制力度越小,而操作难度越大,这样自然就会形成一种上下的离散与脱节。因此,在现实中面对民间普及发展问题往往力不从心,竞技武术如此,足球、篮球等项目也大多如此。其次,由于各级行政机构相互之间的协调配合完全是依靠行政指令进行的,特别是平级之间沟通执行渠道不畅通,很难形成一种平面化的行政指令自由流通体系,既不能保证规章制度的普遍适用,又不易做到整个网络沟通与操作。再次,竞技武术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普及发展性问题,全球推广性问题,从而将竞技武术推入奥林匹克竞赛中,这一点恰恰是现行管理体制最难以做到的。
纵观现代体育项目的发展历程,绝大多数项目都是先由一些体育协会进行传播推广,随着参与人数的不断增多,逐步向世界各国发展普及,最后成为一个拥有众多会员国的世界性大型体育项目。这种自下而上的科层化发展模式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民间自发的休闲娱乐精神,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极大的感染力。例如,足球的第1个规则《剑桥规则》就是1848年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进行校间足球比赛所制定的规则,而后不断发展完善,1863年,英国足球协会才正式制定并统一了足球规则,随后足球风靡世界;篮球诞生于1891年,第2年才由奈·史密斯制定了13条比赛规则,1932年,国际业余篮球联合会正式成立,并统一了竞赛规则,1936年奥运会将男子篮球比赛列入也式比赛。我国目前发展较好的太极拳运动正是这种自下而上的科层化发展模式的极好例证。竞技武术体现出的是自上而下的行政主导发展模式,因此,民间普及和全球推广进展较慢。
2.6 竞技武术的量化
古特曼认为,“现代体育的特点是几近疯狂地想将每一项竞技行为转换成可以量化、可以测量的事物。体育项目无孔不入的数据积累,是足球、棒球、篮球、曲棍球,以及田径项目的特征所在,这些项目当中,随着科学技术的向前推进,量化的精确度不断提高,而秒表这样的东西,已经变得像原始社会的产物一样古老、落后。而现在,电子计时器可以精确到百分之一秒,甚至是千分之一秒,不管是观众还是运动员,都十分重视这些奥妙的时间之差。[1]”近代体育是建立在工业革命的基础之上的,而工业生产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计量化。特别是随着工业生产模式的全球性推广更是将这种计量化带到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现代体育自然也不例外,即便是最难以量化的体操比赛,今天依然将其设计为由“一个动作难度的系统和一组裁判,然后采用裁判主观性判断的数学方式(包括最高分和最低分)来打分[1]。”因此,古特曼认为体育数据是现代社会数据的一部分,量化是现代体育运动项目中极其重要的一个特征。
竞技武术的发展也遵循着这一量化原则。比如,散打里以体重级别进行的分组比赛,套路里有明确规定的难度系数。特别是从1985年制订的第1部武术套路竞赛规则开始到2012年最新的规则出台,前、后进行了多次的反复修改,套路整体动作也日益朝着“高、难、美、新、稳”的方向发展,量化标准越来越明确细致。2012年,修订出台的《武术套路竞技规则与裁判法》中明确规定了长拳、剑术、刀术、枪术、棍术等各项动作难度内容及等级与分值。比如,在太极拳、太极剑动作难度内容上就明确规定“腾空飞脚向内转体180°”为322B级难度(0.30分),“腾空摆莲540°”为324C级难度 (0.40分)[4]。这 些 规 则 一 方 面,使得竞技武术朝着标准化、体操化、表演化、西方化的道路发展,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地削弱竞技武术的技击性,可以想象,当一个运动员在腾空旋转540°或者720°时自己能否站稳尚存在疑问,更遑论击打他人。反观现代体育项目诸多量化规则实际上都是在突显该项目的技术特色,使其技术动作更加规范化、标准化、统一化、美观化。量化的结果使其技术动作和比赛形式更加鲜明突出,同时,也有利于大众观赏与评判。竞技武术却在不断的量化过程中削弱自己的技击特色,演变为体操化、表演化的武术,中国武术的本质特征被日益稀释、弱化,技术特征越来越不明显。竞技武术产生于传统武术,缺少的恰恰是这种量化精神,再加上其特殊的演练形式和习练方式,使得竞技武术无法完全演变为纯西方化的竞技体育项目。
中国传统武术中的套路大多是一种练习手段,是为达到技击目的而采用的一些身体练习方式,其根本目的是在最恰当的时机,用最恰当的技法,以最有力的方式击倒对手,从而保全自身。因此,传统武术套路练习更注重实战模拟性,以快速准确击倒对手为目的,对所采用的身体姿态不做量化要求。在某种程度上甚至鼓励习练者自己体悟技术动作,创造更为简洁明了的技术动作。比如,太极五大家拳法中有许多动作大体相似,但在细微处却有着诸多不同,几乎每一家都有自己独特鲜明的技击特色。当然,如果生硬将这些动作细节划归入量化考核体系,那么自然其鲜明的技击特色也将消失,但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又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评判标准,不利于全球性推广。
2.7 竞技武术中的纪录
现代体育“结合量化的冲动以及获胜、超越、成为最好的欲望——其结果就是纪录的概念[1]。”纪录“是一个极为抽象的概念,它不仅使得在同场竞技的运动员之间的竞争成为可能,还可以使那些不同时间和空间里的运动员们的竞争也成为可能。[1]”当然,有明确数量关系的田径、游泳等项目较好标注其纪录,而对于体操、花样游泳等项目纪录设置就显得较为困难,但人们很快就找到一种全新的纪录标注体系,即评分等级、夺冠次数、比赛分值等量化标准。例如,“纳迪娅·科马内奇(高低杠运动员)7次达到了‘完美’(满分),而这神奇的7次成为了一项纪录,这就打破了涅利金一次获得满分的纪录。”[1]现代体育项目对纪录的追求是一种人为的顶层设计,它促使一代又一代人不断超越自己,但这种超越究竟有没有终点,或者终点在哪里呢?反观拥有毕达哥拉斯、阿基米德、欧几里德等大批数学家的古希腊人却从没有试图在他们的奥林匹克竞技会中设置纪录,因为,他们认为“人类始终是测量一切事物的标准,而不是被不断测量的对象[1]。”这是古希腊人的思维模式,但“现代人的体育与另一种哲学联系在一起,这种哲学有时候分散,有时候条理清晰,它就是进步论。进步观或者进步理论是一种线性观念,它认为在每一个进步的基础上都可以再进步。[1]”正是在这种进步理论的影响下,现代体育一直朝着人类身体的极限前行。
做一个简单的逻辑推论,以100m为例,假设人类速度可以无限提高,但其最终的端点无非就是0s跑完全程,0s之后呢?人类的另一个纪录终点又将设置在哪里?如果人类一直是进化着的,那么0s之后就不再进行化了吗?当进化理论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之后,现代体育发展的终极走向或许也会成为困惑现代人类最大的问题。
中国传统武术由于诞生于农耕文明背景下,用现代体育中的纪录思维来看,应该属于一种内隐式的纪录追求。传统武术讲究“拳练千遍,其意自现”,练拳的过程实际上是身体对技术动作的体悟过程,而这一过程中身体能充分感受到技艺的增强给身体带来的种种变化,而这种体悟到的身体变化实质上就是传统武术中内隐的“纪录”。纪录的本质是超越,只不过西方体育将其量化、数理化,而传统武术则将其内隐化,自我体悟与身体感受是对武术技法的最好“纪录”。每天练拳都有一种全新的感悟,而这种感悟正是激励许多习拳者最大的动力源。竞技武术由于是在特定时代对传统武术技术加以改造,其规则的不断修订过程充分体现出西方化的纪录要求,如腾空飞脚向内转体180°、腾空摆莲540°等。这种外显的数量化的纪录追求直接破坏了传统武术中的体悟感,虽然部分技术动作外形相似,但其目标追求、精神内涵已经完全不同,这也是当前广大健身者不喜爱练习竞技武术套路的原因所在。
3 小结
从世俗化的角度看,竞技武术虽然从传统武术中分离出来,但其技术体系仍然延用旧有套路中的部分技术动作,因此,在传承体系、习练方式、训练比赛等诸方面依然与传统武术相通,特别是在竞技武术理论方面,由于无法完全采用现代公认的生理学、解剖学、人体力学等多种西方现代科学理论进行解释,使得其技术体系较难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竞技武术要向现代化世俗化发展,首先,必须解决理论问题,而后是技术问题,只有这两方面都普世化了,竞技武术才能真正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
从平等化的角度看,竞技武术要注意技术习练中的平等性、套路选择中的平等性和人际关系中的平等性。虽然,在表面看来竞技武术在平等性上做的较好,实质上由于竞技武术诞生于传统武术之中,其技术体系从选择、编排、评判都存在着一种隐性的不平等。当然,任何体育项目都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平等性,但是,作为一种技术评分类项目,最基本客观的平等性必须要做到,否则不利于传播和发展。
从专业化角度看,目前,绝大多数竞技武术运动员都是以专业化身份在生活、比赛。社会中这种专业性市场化比赛较少,因此,大多数运动员在退役后生存问题显现出来。必须要思考如何将专业和职业联系起来以解决此问题。
从理性化角度看,竞技武术理性化严重不足。首先,竞技武术诞生于具有东方形象思维背景的传统武术体系中,理性精神存在先天不足;其次,竞技武术诸多改革行为是国家行政意志的反映,而不是从项目本身的理性角度出发进行自我变革。
从科层化角度看,竞技武术是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体系,因此,在发展普及中遇到诸多障碍不利于在世界范围内更好普及发展。
从量化的角度看,由于竞技武术从一开始就主观追随西方体育量化标准来进行自我改造,削弱了自身鲜明的技击特色,同时,由于始终在刻意模仿西方评分类项目,使得竞技武术越来越体操化、表演化、西方化。由于竞技武术体系现在自成体系、赛制完备,只有将传统武术与竞技武术分开发展,相互促进,才有望走出当前“双重困境”。
从纪录角度看,竞技武术仿照西方体育模式将对纪录超越的追求逐渐外显化和数量化,破坏了传统武术流传数千年的内部身体感悟激励机制。使得当代武术爱好者在练习竞技武术中缺乏由练拳直接给身体带来的超越快感和激励性,从而使竞技武术习较难广泛开展普及,从根本上影响到竞技武术的长远发展。
什么是现代体育项目?现代体育项目具备的基本特征、基本因素有哪些?现代体育项目具体的发展模式是什么样的?只有这些基本问题梳理清楚,竞技武术才可能真正走向现代化。用西方现代体育所具备的七大特征来重新审视竞技武术,发现当前竞技武术距离成为一项标准的现代体育项目依然有着较大的差距。
[1][美]阿伦·古特曼.从仪式到纪录:现代体育的本质[M].花勇民,钟小鑫,蔡芳乐,编.袁旦,审译.北京:北京体育大学,2012:2,21,29,30,42-45,48,50,52,54-56.
[2]曹湘英.竞技武术套路形成的主要技术特征分析[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7,30(11):601-604.
[3]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中国武术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6:367,388,391.
[4]关于印发《武术套路竞赛规则与裁判法》2012年版修订内容的通知[EB/OL].http://www.wushu.com.cn.
[5]贡建伟,唐文兵.对比奥运竞技体育谈中国武术的文化生存力[J].体育与科学,2008,29(5):51-54.
[6]洪浩,范会玲.竞技武术发展研究综述[J].体育文化导刊,2007,(2):50-53.
[7]吉灿忠.竞技武术“文化空间”之研究[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2,29(2):197-218.
[8]李翠霞,赵岷.加与减:对中国武术发展的另类思考[J].中国体育科技,2012,48(1):96-101.
[9]李龙.当代传统武术与竞技武术关系之解析[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1,34(10):137-140.
[10]路云亭.迁徙的精神家园:论奥运主义激荡下的中国民族意志[J].体育与科学,2012,33(4):5-11.
[11]刘同为,张平安.从格式塔心理美学视角论武术动作的表现力[J].体育科学,2010,30(8):92-96.
[12]刘桂海.体育政治化深层机理研究[J].体育科学,2012,32(8):66-72.
[13]彭鹏.竞技武术套路特点研究[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8,25(5):56-58.
[14]冉学东,王岗.对中国武术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新思考[J].体育科学,2012,32(1):71-87.
[15]体育事业“十一五”规划[EB/OL].国家体育总局网站,2007-03-02.
[16]王国凡.“标准化”视角下的竞技武术(套路)国际化发展的几点探讨[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9,32(2):35-38.
[17]王岗,吴松.现代竞技武术套路技术体系及其价值取向[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6,30(3):62-87.
[18]王岗.论竞技武术的强化、异化与软化[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7,41(7):35-41.
[19]王巾轩.论武术的竞技性、传统性与大众性[J].体育文化导刊,2010,(2):85-90.
[20]文善恬.竞技武术,歧路之羊?——武术发展要警惕一种“去竞技化”倾向的回潮[J].体育科学,2008,28(11):87-92.
[21]袁旦.时代呼唤人文体育价值观和工具理性价值观批判——从一本西方体育学者著作说起[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2,(1):1-6.
[22]张江华,刘定一.起点即终点:武术发展的知识向度[J].体育科学,2012,32(5):42-48.
[23]周伟良.中国武术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25.
[24]赵岷,李翠霞.现代语境下对传统武术中“传统”的解读与思考[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9,25(2):20-23.
[25]赵岷,李翠霞.影响武术国际化的五大历史原因[J].体育文化导刊,2006,(1):2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