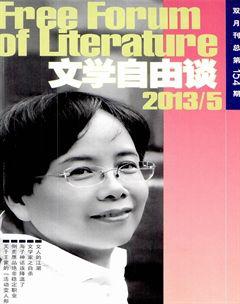“忘”也是一种新生
毛志成
写此文的灵感,源于几件琐事。其一是数年前的迁居,必须退掉几十年来住过的原宅。此屋中曾经堆满了像小山一样的东西。这些东西包括:一,我写过的(而且大都发表过)的作品的原稿(包括当初手写的和后来打印的);二,发表在各种报刊杂志上的样报样刊;三,各种奖状(我未获过大奖,但中奖、小奖加在一起不下百余种);四,教育部门(也包括文学部门)发给我的头衔委任书以及当嘉宾、评委时的聘书;五,各种人(也包括有地位、有名气之人)给我的来信,其中有的是夸我的信,有的是骂我的信。上述的东西,尽管我在舍弃时有无奈之意,但还是雇了一辆平板三轮车往返运了三四次将其卖到了废品站。事后,真有《红楼梦》中所云“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快感。第二件事是几次老同学聚会,其中包括小学、中学、大学同学的聚会,此外还有并非同学而只是一般相识者的聚会。以我这样的高龄之人,所阅的人和事可谓多矣。即使以他们与我的关系而论,不仅亲疏各异,连恩仇也不尽相同。这一点,只要想想当年政治运动的频繁就不难明白。在上述的聚会中,只要有人用太多的话去谈过去的事,包括对我当了多年的“运动对象”表示同情,我也都不作回答,只是简单地回应:“俱往矣,忘了吧!忘才是一种很有价值的事。”
基于此,我索性要深入地说一说“忘”的多种涵义:
一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大智人物之一庄子,他的学说如果用三个字来概括,就是“无”,“忘”,“化”。关于“无”与“化”,我已经写了多篇文章,不再赘叙,这里只重点地说一说“忘”。
什么是忘?因庄子而引发的两个有名成语是:得鱼忘筌,得意忘形。值得说明的是:“得意忘形”曾是一个具有很大褒义的词语,不同于后人(包括今天)所指的“小人得志,忘乎所以”。
得鱼忘筌的原意是:捕到了鱼就应当忘掉鱼具本身,不要捕到了鱼(甚而未捕到鱼)却天天向人卖弄他的鱼具,炫耀他的鱼具,或是标以高价。用今天的例子来佐证就是;衣服是为了穿的,食品是为了吃的,车子是为了用的。总之都不是为了显示的,不是为了表明自己的“高品位”。
得意忘形的原意是:掌握了某些知识条文、社会道理、语言词句,弄通了并已经付诸实践,就应当忘记那些条文、道理、语句本身。不能将牢记、背诵、卖弄那些有形的东西当成兴趣,当成本领,当成不凡。
这样的“忘”,没有一定的德智品位是办不到的!
二
有时,善于牢记是优点;有时,善于遗忘也是优点,甚而是更大的优点。
中国是一个偏爱牢记的民族,证据之一就是:中国的史料、史籍和以讲史为业为趣的人是世界上最多的国家。这当然是优点,一个民族无史便会“断其根”。但是记而不忘,将太多的心思和行为都固守在历史中,徘徊在过去中,不肯忘,也有悲哀色彩。
三
中国的牢记、念念不忘,和淡忘、遗忘的比重,前者太多而后者太少。
而且牢记的内容中,带有仇恨色彩的人和事又居多。而带有宽恕、谅解意味的人和事往往偏少。
典型的例子之一是:上世纪从五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中期,当阶级已经近于不复存在的时候,铺天盖地的口号仍是:“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对某些人和事,包括有仇恨色彩的人和事,一时的记一下是正常的,也是应当的。但永远的牢记不忘也无异于给自己的心灵带上永不脱掉的枷锁。
四
汉武帝下旨独尊儒术之后,中国的国民(尤其是儒生)对孔子怀着敬意念念不忘了两千多年。到了“文革”,举国又对孔子念念不忘地骂了多年。前时,又掀起了《论语》热,弄得很多人对孔子又是念念不忘。
我们能否像庄子那样得鱼忘筌、得意忘形?能否简明地知道孔子的一点梗概而淡忘他的许多细枝末节?如果那样做,大有益也!
五
中国病态式牢记的习惯,一般有三种:一,法定式牢记。科举制时代所规定的必读教材,都是法定的,弄得儒生们整日陷在死记硬背的痛苦中,而实际上并无多少真正的有用价值。二,功利式牢记。这仍然可以用科举制为例,儒生们“十载寒窗”,苦苦读书,无非为的是谋取功名,想的是一朝发迹。真的发迹了,也就把那样的敲门砖丢掉了。三,崇拜式牢记。只要是“人上人”的书、文、话就奉若神明,“放之四海而皆准”或“一句顶一万句”,于是就牢记之、诵读之,念念不忘。殊不知任何名著、名文、名言都是该时该事的产物,真正的智者都应该立足于“得其意而忘其形”。任何人一经只是记而不肯忘,只能是蠢人而不知其蠢。不忘,断不能前行!
六
中国以记得牢、记得多而享誉一时的人太多了,基此而获得了各式各样的头衔,如学者、专家、教授、通家之类。如果登上了什么“论坛”、“讲堂”之类,就更像“高品位之人”。其实我反倒认为:谁能把知识、学识、见识、才能、本领精简化,忘记了太多的书籍、文章、语句、演技,把上述的东西凝炼为切实有益于社会的几句话、几种见识、一两项本领,更像明白人、有用之人。只是“记”而不肯“忘”者,所生产出的文化品,十之八九至多是社会的装饰品、点缀品、陈设品、贩卖品,实用价值是很小的。
七
高品位的记和高品位的忘都是宝贵的,缺一不可。
高品位的记所指的内容很多,而高品位的忘从根本上说只指一条。高品位的记,从下而上依次是:一,对事物之形的记,其一便是对字形、句形的记。连基本的识字量、识词量、识句量都不达标,或记了便忘,只能称之为蠢。二,对事物之理(包括原理、法则、公式)的记,连那样的基本之理都糊涂或一窍不通,便很难形成对世界的基本认识。三,对极具个性化的人和事的记。世上模式化的人和事太多了,比比皆是。对那样的人和事越是记得多,就会越平庸。只有极具个性的人和事,我们哪怕记下来少量的几个、几件,都有益于提高我们的独立思考能力。
而高品位的忘,根本的特征只有一个:对已知领域或既成事实只是回眸一笑,予以告别,转而向未知领域、未成事物推进。
八
中国的不良传统之一,恰恰在于对已知(包括自认为已知)领域的陶醉,不厌其烦地重复、图解、复制。对既成事实(尤其是被誉为“英明”、“卓越”、“正确”而又未必真实的事),则群体式地大唱颂歌。否则便不允许,甚而成了犯禁之事。此时,如果有谁能喊出“忘记那些事吧,搞点新的事去干吧!”他很可能是真正的智者。
九
若干年的中国文学,立足于“记”而拒绝去“忘”的现象往往很醒目。
从“土改文学”、“合作化文学”始一直到“阶级斗争文学”,大都把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右派视为永远说不完的反面角色,牢记不忘。好像离开那样的“黑n类”就不能构成文学作品。然而在实际上,又常常只是牢记了上述人一些黑色的政治符号,并没有真正将其当成“人”来入细入深解读。以地主为例,实际上是有三类的:官僚地主,恶霸地主,正宗地主(有的也称儒家地主)。正宗地主只是纯粹的土地经营者,有的还讲求一点儒家理念,在道德上并无恶行,他们既怕官又怕匪。我绝对拥护土改,也希望出现高品位的土改文学,但是中国的土改文学不仅只会写官僚地主、恶霸地主,而且认为地主就是官僚、恶霸的同义词,根本否定正宗地主的存在。更何况土改、合作化、公社化实现以后,等于地主已经消亡,何苦还要强化对地主的牢记(甚而将其黑色加重之后再去牢记)?我看远不如将其忘记更理性些,更明智些。
十
文学该忘的作品太多了,作家该忘的事也太多了。
今天以写古代事、前代事为主趣的作家中,有的具有对历史进行反刍、从中提炼新理念、汲取新营养的价值,值得尊重。而有的则只是为了用往昔的花花事件来赢得哗众效应和名利效应。如古代或前代的匪魁寇首(包括女性的或尤其是女性的),往往最容易被搬上银幕。其实,将那样的人尽量忘掉,多写些或多演些具有文明品位的现代勇士,价值要大多了。
十一
顺便说说中国的武术神话,我认为必须与之告别,尽量忘记。中国武术,也称中国功夫,绝对是好东西,说其是中国瑰宝也不过分。但是通过文学手段或影视作品将其神话化,如同仙术妖术,具有上天入地、喷云吐火、静坐闭目而能致敌死命的法力,这就有欺人欺世之嫌了。必须懂得,武术本身首先是体育活动。用它去搞社会斗争,无论是斗争工具、斗争手段还是斗争理念都是落后的,也是反现代、反文明的。对武术神话,我们必须遗忘!
十二
无论是文学界、艺术界还是社会的其他各界,最难忘记的东西莫过于名利。只要是现实的人,有一定的名利需求都是正常的,也是合理的。但是名和利,不仅应当是合乎道义的,而且它一经坐享或困守那样的名利,都意味着走进了既成名利的坟墓。
忘,不仅是一种道德也是一种智慧。高品位的忘,也是一种宝贵的正能量。因为它是对僵化物、陈腐物、多余物、无用物、有害物的有效清除,是向新领域、新视野、新境界、新情趣的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