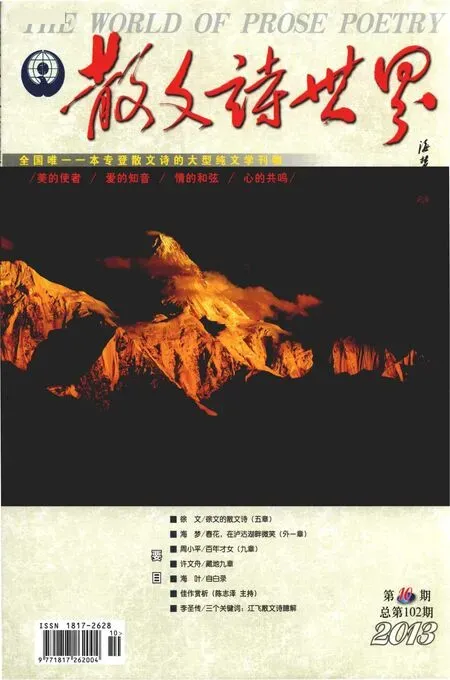沫沫的关键词
保定七中 赵东哲
习 俗
沫沫,你是我的小王子,是你开启了新一天。
张大的眼眶里,晶亮的眸子缓缓游动,像明星,像灯火。如豆小口开着合着,忽然吞吐出一个奶声奶气的喷嚏,津液横流了。护在左右的奶奶飞来灵感,她吼出了三个字——“一百岁”,这是一个辈辈传下来的好口彩,在驱除什么,也在企盼什么。沫沫连喷第二个,“二百岁”随之,打到“三百岁”后,大家却巴望着第四个。我们都笑了,沫沫却没有超出这个记录,小巧的你也不是为了破掉这个记录,而是为了一只小鸭雏的破壳而出,为了暖融融的阳光刺穿彤云,所以你只是若无其事地整理了糗容,晃动着并不牢靠的国字头,头里的混沌正慢慢地开化,就像黎明将至的天地,蒙!、熹微,终会明朗。此时,小小的脑瓜里刚刚露出一颗惺忪的启明星,用粗线条渐渐描摹出脑际的风物。
目 光
他心纯无碍,他一声不响,看着我的眼睛,一眨不眨,两瞳却微微地闪动,放射出幽幽的清光。上身挺个笔直,紧攥了两个小肉捶,似猎手不息地盯着猎物。不错,正是猎物,世间的一切都被他那双渐大的瞳孔囊括、捕获了去,仿佛一只小豹子用它那锐利的眼光扫描草原的广布、森林的繁茂、鹿儿的伶俐、斑马的矫健。
我累了,想斩断这久长的交汇,怎料,他小小的两颊竟然敛出两颗白皙的鹅卵,眼睛、嘴巴拉长,撇向两边,慢慢绽出了笑容,燃烧的小火苗不懈地炯炯地烛照着我。
小王子,除了你,还有谁能如此不羞地看着我,你那天地间至真至纯的面影,怎能不柔软最刚硬的铁骨,你那洁如玉的肌肤如何不净白大地的芜杂呢!
愿 望
沫沫熟睡了,双手上举,做了一个投降的英姿。平静的小脸上,间或浮现一个戏剧化的小插曲,他或者撇出了下唇,凝上了眉峰,要哭的样子,或者,瞬间漾出一朵甜美的笑,缀满了幸福。一旁的奶奶说:“小家伙在做梦。”呵呵,我笑了,这小小地脑袋开化几何?梦如何?几近为零的人生经验,梦有怎样的奇幻?这追问仅仅是追问,是诧异,不会有结果。只知道在梦中,他的人生也如醒时,忽而欢颜,辗转又哭,眨眼工夫,破涕为笑。这节奏,是任何大师也弹不出的精彩,这片阴晴难料的海天,我以默默的静观为无上的光荣,轻抚他肥白的小手臂,亲吻他做着吮吸动作的两片小唇,如果可以,我更愿意化作他身下那一方绒毯,承着他,融着他,含着他,直到那对美的欲望淌出不可遏制的溪流。
童 话
我斜倚在床上阅读,小王子接近了我。他坐在奶奶设于怀中的宝座上,已经睁圆了双目,丰满的下巴微微上翘,小小的粉舌半吐,为杏核般的嘴开出了一圈圈水泡泡。
我读书读出声音了,他停止了环顾,一心注视着我的书、我蠕动的嘴。读完一段,看上他一眼,好像在故意讲给他听,他长久地不动,似听得全神贯注。我问道:“小沫沫,好听吗?”他感觉出了不同的语调,融化了一脸的郑重。
“你小小的脑瓜,听出了什么精彩?”
“啊……咿呀……”神奇的世界里,小王子回答我了。原来,他真的听懂了,那低估他智力的人,不正是贬损人类自己的潜能吗?那神秘、清澈的黑眸,那微微皱起的小眉,致密、细嫩的面颊,也许在告诉人们:我懂得一切,你自以为掌控了我,哪知我正以自己的哲学博笑于你,我的笑里蕴含着精致的成人所不了解的童话。
空 气
还未踏进家门,早已听见放怀的嬉戏声了。沫沫平躺在床上,扑棱着腿脚,无邪而脆亮地尖叫,犹一只撒欢的小鸟雀。小鸟雀在收取调笑的时刻,更带着它那纤细、潮湿的鹅黄软化着成人的神经。
奶奶抑着嗓音,吐出一曲曲银环般叮铃的歌谣,歌词唱道:没牙颗,吃饭多,见人来了盖上锅,见人走,呼噜呼噜喝两口。这小孙子,被逗得牙床外露,真是一片光秃秃的沃土。呵呵,这室内的空气原是僵硬的、凝重的,沫沫的降世,在清一色的蓝天上,勾画了一朵悠悠的白云,这抹童真,凝聚着家庭每个成员的神经,令我们从繁杂的喧闹中松弛下来,重获久已失落的人生真谛。
是啊,入家,门关闭的那一刻,所有的烦恼、忧伤都成了身外之物,于我这个世外之人没有关系了。我所了解的只是,尽情的脱掉负荷了一天的沉重、面具,令本真主宰自己。
这是我们的共识,而它们都是沫沫的赐予。
泪 水
我的泪水多了,我顷刻间明白了一切。
针头刺进了沫沫的胳膊,痛感还未抵达沫沫的大脑,已经酸楚了我的内心。时光整整将我们阻隔了三十天,三十天我日日拿着他的照片看,看着看着泪奔了。盗车的匪徒盗走了两个月的男婴,在审视良心的关口,他释放的,是灭绝人性的残忍,我把持不住了,如果父母是我——我设想,我会疯掉,我会绝望至死。
就像歌中所唱:至少十年不曾流泪,至少有十首歌给我安慰,可现在我会莫名地哭泣,当我想你的时候。我的不曾流泪何止十年,可是,沫沫,有了你,我这蓄积的满池的泪水,能够顷刻而至,会和着鼻涕俱下,会沾湿半面衣襟。
诵到杜甫的“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读到郁达夫的《一个人的旅途》,看到灾难中,死去的父母,活着的孩子,得到升华的我,顷刻之间,明白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