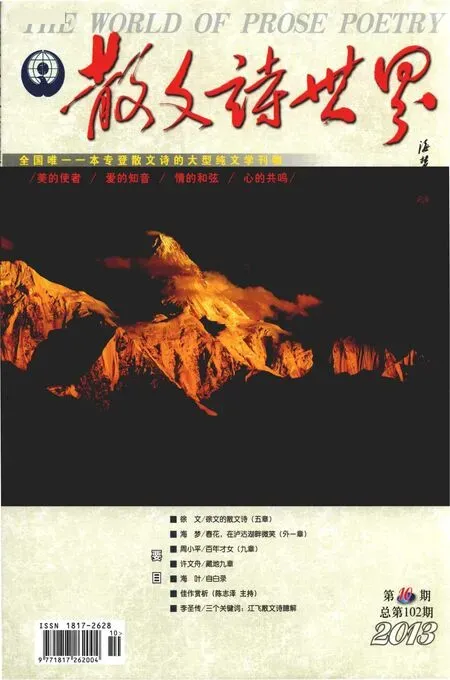时光的侧面(组章)
山西 李 需

静
月亮静下来,在天际,寻找河流的影子;
屋脊静下来,在尘世,寻找风的脚步;
我静下来,在深处的岁月,寻找一个人,从时间缝里漏下来的那一声轻轻的、微微的
——叹息!
夕阳下的村庄
夕阳下的村庄,是一幅简约的勾勒。该亮的地方亮,该暗的地方暗。
巷道里,那个奶孩子的母亲,撩开一小块的白,就生动了一座村庄的寂寞。
院落上,母亲晒了一天的豆酱,像另一种暗。但,站在远远处,我也会和风一起闻到它浓郁的香味。
最后,村庄在夕阳“砰然”滑落的瞬间,就会一下子亮出来:
一柱一柱炊烟的旗帜!
站 立
树的站立,只有一种姿势。
而我,却用各种姿势站立——站成树的形态。
一片片叶子的唇,都在承纳着阳光和遥远的雨意!
之后,我身体的每一部分,是否也就成了树的每一部分?
春日小景
天边,油菜花开成一抹,极细极淡的那种,像谁放在那里的一条黄纱巾。
紧挨着的是一片麦田。一片绿色的水,汪汪的,在阳光下闪烁、飘忽。
接着,又是一片更大的油菜花,闹哄哄的像在集会。让人目光不忍碰触。仿佛,目光一碰,就碎了,飞了。
一片油菜花,一片麦田;
一片麦田,一片油菜花。
就这么黄着、绿着;绿着、黄着。从天边铺下来、铺下来。
一直铺向我低矮的、土头土脑的故乡!
那个人
那个人,远远地,低头走在乡路上。
那个人是谁?
天空,道路,冬天的风。
那个人,一会儿很重,像一种久远的积淀;
那个人,一会儿很轻,像被时间任意提起又放下,放下又提起的,一个飘忽的影子。
大太阳出来时,那个人,一下子就不见了。
那个人呢?
在旅途,或不在旅途。
我回头看了看被拉至很后面的村庄,突然就想起两句著名的唐诗来: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爱
爱过土地、河流、山脉,再爱你的鸟鸣、露水和草木。
爱过房屋、炊烟、道路,再爱你的岁月、日子和月色。
爱你灵魂里的纯净,爱你骨头上那一点点的光芒。
爱时光漏下的一声微微地叹息。
站在近处爱你。你秀发飘逸,在一马平川的故乡,多像我美貌的姑姑!
站在远处爱你。你苍茫裹身,在雪花弥漫的故乡,我的胸中始终都燃着激情的火焰!
爱上山坡散落的一群羊,是谁漂白的思念?
爱上黄昏里的一头牛,是谁沉淀在生命里的记忆?
爱过你布谷声里那个湿润的早晨,再爱你秋霜里那一片柿叶的红。
爱那沉重的轱辘,还在遥远的风里吱吱地响。之后,迎春花开得一抹一抹,春天了,静静铺展的故乡,像谁画在那里的一幅画?
推车的人
推车的人,在久远的乡村土路上,泊着。像时光不经意间留下的一点擦痕。
偶尔,这小小的擦痕也会渐渐放大。大到阳光明亮的夏天,那个人,弓着身子,亦步亦趋。
这样的造型古典、粗犷,散发着荡气回肠的味道。
最后,我还想说的是,他到底使了一种什么样的魔法?
这个推车的人,推着,推着,就把那个夏天推远了;
这个推车的人,推着,推着,就把自己推没了。
如今,站在时间里的只有风。
风吹一次,我的心口就会疼一次;
风吹两次,我的心口就会疼两次。
时间之外
放下流水,放下远方的儿女;放下道路,放下田野一穗玉米的重量;
放下骨头缝里吱吱作响的声音。
放下一头牛的哞声,放下半夜的月色和一阵一阵的咳嗽;
放下五谷杂粮,放下日子和时间。
放下牧羊的鞭子;
放下劈柴的斧头;
放下一场风里的晃动;
放下一场雪里的凛冽。
放下刚刚燃旺的炉火,放下眼睛里燃烧的火光,和最后的一点蓝焰……
之后,你在时间之外的黄昏,站在河岸。像一尊苍茫的雕塑,或者,仅仅只是一处废弃多年的旧码头。
夜来了。我望见一河的星星,爬上岸,走到天上。
我不知道,你是最亮的那一颗,还是最暗的那一颗?
一座村庄的写意
河流吐出帆影和碧空,时间在历史中停顿了一下。
一座村庄没有停顿。
它跨过历史和无数的瞬间,走进了另一个世纪第十三年的夏天。
阳光绽放,灿烂明亮。
一位年轻的母亲怀抱着她的孩子,像村庄一幅暖色的动画。
她打开了这座村庄的小欢喜。
沿滩的几处烧瓦窑,向河流吐出它刺鼻的怪味和浓稠的黑烟。
属于村庄的只剩下几只鸟儿厌烦的啼鸣;
只剩下一只蝴蝶在飞。
我看到的那个男人,怀抱着另一块天空,跳下长途汽车。
他迈着急匆匆的步子,向那位怀抱孩子的女人走去。
此时,一座村庄就这样安静下来。
时间在这个夏天,匆匆而过。
村口一棵树
如果时间能够向前推移,村口一棵树,一定还和时间一起站着。
黄昏辽阔。
时间像碎了的鸟鸣,有一声没一声。
如果时间能够再向前推移,村口一棵树,一定还和岁月一起站着。
黄昏依然辽阔。
岁月如一件古老的陶罐,闪闪烁烁,发着一些若有若无的光。
如果时间能够推向遥远,村口一棵树,一定还和母亲一起站着。
一场风在吹,一场雪在落。
我不想虚谈她的爱,更不愿言及我所有的感恩。
我只想再次回到那遥远,天天,都能抚摸到——一个人温暖的眼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