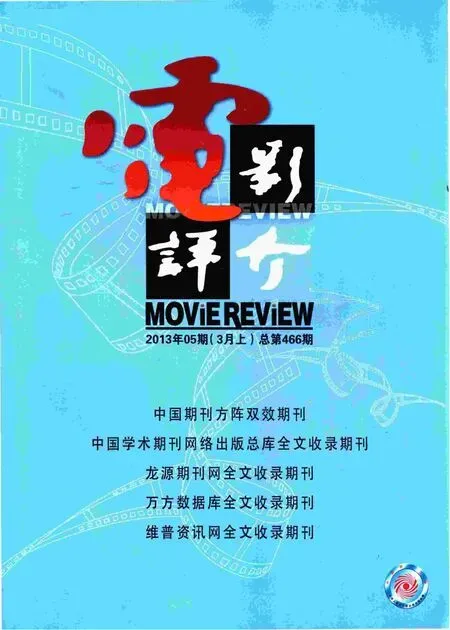小人物的悲情狂欢曲——从张猛的《耳朵大有福》、《钢的琴》说起
2011年7月,暑期档,好莱坞电影大片扎堆中国银幕,国内导演纷纷选择避战。张猛的小制作电影《钢的琴》7月15日上映后自然被推到风口浪尖处,当所有人为他扼腕痛惜时,其电影却以460万(首周)票房胜利收市(制作成本不足百万)。虽然与一些大片的吸金力无法相比,但是其“无差别交口、零恶评”[1]的好口碑着实为国产电影挽回些许颜面。
《钢的琴》是中国第六代导演张猛的第二部作品,他的处女作是2008年由范伟主演的贺岁片《耳朵大有福》。东北出生的张猛对工人有特殊情结,他的作品聚焦的对象也是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工人阶层,这些人出生于五六十年代,曾意气奋发地挥舞着钳、锤、焊,而后在轰轰烈烈的国企改革中,由共和国长子变成了弃婴,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无从适应。犀利的张猛窥视到这些无助,比如《耳朵大有福》中王抗美的四处碰壁,但是他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就有了《钢的琴》中陈桂林敢于造钢琴。这两点构成了张猛对于工人阶级的人文主义关怀,也使其将着力点放在了小人物与新时代的错位碰撞上。本文试图从电影音乐元素、电影语言、画面等视角分析错位碰撞而形成的张力美。
一、电影元素:用音乐唱响一个时代
张猛拍电影之前曾经是赵本山团队的春晚御用编剧,为赵本山精心打造的《功夫》、《说事》连续两年获得小品类一等奖。多年的小品舞台实践使其深深懂得了什么时候该抖包袱,怎样逗观众笑。而另一方面,电影如果是纯粹的傻笑未免太过庸俗,张猛想达到的是一种“黑色的、笑中带泪的、带有一些悲情色彩的、让人看了心焦”的喜剧。基于此,他聪明的截取东北退休、下岗的工人为对象,并将其置身于新时代的浪潮中,形成一种旧与新、逝去与存在、过去与现代的错位对抗,这些小人物幽默地与新时代对话,也不得不心酸地告别老时代,苦中有乐,笑中有泪,这就真正达到了张猛追求的“高级”喜剧。而他探索较为成功的一点就是在电影中植入音乐,用音乐说话。
1.巧妙植入音乐
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歌曲。张猛喜欢用音乐来宣告一个时代的开始。《耳朵大有福》中他以《运动员进行曲》暗示王抗美的光荣下岗,以《长征组歌》征兆老王的无奈,用《天路》、《隐形的翅膀》、《月亮之上》、《眉飞色舞》等与周围鳞次栉比的高楼构建了一幅现代化城市图,结尾以王抗美在雪地中的高歌宣布一种小人物在新时代中的落寞。
在《钢的琴》中除全部人员均干着与音乐有关的工作,导演还用俄罗斯摇滚大鳄“柳拜”乐队、德国天团“17嬉皮士”,以及贝多芬钢琴曲、台湾民谣《张三的歌》,香港流行天后徐小凤的《心恋》,情歌王子姜育恒的代表作《跟往事干杯》等近45首经典歌曲贯穿。据悉,在拍摄《钢的琴》时,张猛还专门邀请俄罗斯作曲家为影片量身裁衣。可以说,张猛用音乐构建起了主人公的命运,也用音乐暗示着一切。
2.两股“流行”的碰撞
在《耳多大有福》中王抗美的歌是共和国成长的歌曲,是生于五六十年代人口中的“流行”,而《月亮之上》此类是消费时代的歌曲,是生于八十年代的人口口传唱的,也是他们的“流行”。这两个“流行”的碰撞形成了一股张力。首先,新旧“流行”相互对抗。比如,影片中王抗美四处相告自己曾是“铁路文艺队”的男独唱,这恐怕是他最引以为豪的事情,而对什么流行歌曲他基本上是排斥的,而后,到了二人转剧组面试,老板让他试嗓子,问:“啥唱法?流行还是怀旧?”老王说:“算是怀旧吧”,于是在二人转的说唱背景下,老王在高音部分戛然而止,唱不动了,他双手一抹泪花,或许他自己也深知台下观众的不屑,自己的“长征”对于别人已经是过去式。其次,老王想要融合进新“流行”。影片中老王在《眉飞色舞》流行歌的带动下蹬三轮车愈发起劲,并引来众人旁观,或许一个过时的人还能满大街奔时尚让人很是稀罕。可惜,老王年龄已大,再加上哮喘病发作,只好收手。这已经是一个老王永远也追不上的时代了。
而在《钢的琴》中,音乐的痕迹也颇浓厚。陈桂林下岗后和一帮朋友组成了小乐队,为别人婚丧嫁娶演出。这是一代听着俄罗斯歌曲长大的人,影片中为了“洋钢琴”加入了“洋音乐”,比如《山楂树之恋》、淑娴唱的俄语歌,以及他们开头的送葬歌曲《三套车》。与王抗美不同的是,陈桂林这一代是“解放思想”的一代,他们虽然有自己的回忆和“流行”,可是在客户面前也没有坚持什么。你点什么样的歌曲我就唱什么样的。这样,从一个时代的代表到另外一个时代的代表中,就形成了一股蔓延的笑流。比如,开篇从俄罗斯送葬的《三套车》到欢快曲子《步步高》,让人忍俊不禁。其次,影片中多次调侃瓦解一个神圣的音乐来造成笑果,比如,陈桂林给女儿造假琴时说“你忘了我给你讲过的贝多芬大爷的故事,贝大爷就是耳朵背”,成了影片最大的笑点,并让高雅支离破碎。
二、电影语言:解构新时代的一切
今天的社会是快速发展的社会,尤其是高科技时代的新玩意让人眼花缭乱。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我们敢于说人类进步了,其实这恰恰是一种退步。在导演张猛眼中,新时代的汩汩浪潮自然压抑不住,可是在其奔流向前中也会卷走污垢。
1.对高科技和高雅文化的解构
张猛的作品中用通俗、戏谑的语言将现代化的崇高和伟大解构开,从而缅怀一个时代。比如,在《耳朵大有福》中,王抗美想用高科技为自己算命,先讨价还价:“一块半只算后半生,行不行?”这先是一个笑点,而后在高科技算命选照片时,王抗美看着一张张超人照、可爱照、装嫩照片磕碜不已,也是导演让旧人物和新时代的第一次融合,结果自然是不伦不类。这次尝试已经为影片的感情奠定了一个悲剧的基调:“抗美援朝”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后,高科技为王抗美算的命是:一生荣华业兴隆,家境丰厚福禄红,妻儿老小皆如意,不须劳碌子亨通。听此话,回望王抗美的底层困境:妻子住院,儿子不务正业,女儿闹离婚,弟弟打麻将,父亲没饭吃,这很难为有福之相,也捣碎了高科技的“扯淡”,这也可以说是张猛对现代化、高科技时代的反讽。此外,导演也揭露在市场经济进程中,人人为了生计而生的伎俩,比如公园里的转盘,完全是一个圈套。
而在《钢的琴》中,也每每出现解构的细节。比如,从影片的题目上说,原本高雅的钢琴被肢解成“钢的琴”,这除意蕴工人阶级敢于制造钢琴的刚强意志外,还用东北口语的土方法重新包装,就突出“钢”,预示这钢琴也只是一块钢做的琴,没什么了不起,把钢琴做代表的高雅文化瞬间解构。此外,影片对市场经济体制下金钱的无所不能也是一个嘲讽,陈桂林虽然为了钱可以在外人面前低声下气,还规劝二姐夫说“这才叫解放思想”,可是在面对妻子跟卖假药的好上时,他开始嘲讽“小菊终于过上了不劳而获的日子”,并嘲讽卖药的坑蒙拐骗,这也是对“有钱阶层”的一个解构,他们有钱靠的也就是一些坑蒙拐骗和不劳而获。后来,小菊和他为孩子的抚养权而打官司,孩子还在父亲面前许下最让其为难的心愿“谁给我买钢琴,我跟谁”,也是一个钱横在父亲和女儿之间,或许童言无忌,可是市场经济下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已经扩展到了每一个狭缝中,甚至亲情。最后,陈桂林决心自己动手做一架钢琴,这不仅是对高雅文化的挑战,还是对金钱结构的反讽,妻子有钱可以买琴,陈桂林没钱却让用双手的劳动和工人阶层的毅力造琴,影片展开的不仅是妻子与丈夫的夺子战,更是金钱与劳动的对抗。最终,陈桂林制造出了“钢的琴”,工人阶级无所不能的战斗力暂时打败了市场经济下的金钱结构,可是女儿还是跟着母亲走了,并从继父的轿车中走出弹奏一曲,或许这跟被炸的烟囱一样,是工业时代的挽歌。
2.对革命话语体系的解构
影片《耳朵大有福》中,王抗美除了极度的物质贫穷外,其精神层面的空虚也不容小觑。他是和共和国一起长大的一代,连名字都是取自“抗美援朝”,他经营了四十年的职业就是当一名长征歌曲的独唱,王抗美身上时时刻刻流露出革命情怀。可是在长期“铁饭碗”体制的层层保护下,他对于时代的发展是固步自封的,也从未有过关心,退休后,突然被放逐在这个陌生的时代,他才猛然发现自己熟稔的革命话语现代人已经早已不念。“当下的话语是追求快感、刺激、娱乐化”[2],这与革命话语完全是两个时代。尤其经典的一幕是在网吧里,年轻人在网略的虚拟环境中寻求刺激厮杀,而王抗美看的电视剧中正是红军《长征》,当二者被切入一个画面时,我们思索许久,红歌已经没人继承,它销声匿迹在年青人打游戏的快感中成为一个尴尬的过去符号,甚至一片废墟,无人问津。革命话语的消逝对王抗美这样的人是一种莫大的伤害,甚至是信仰上的危机,他无比信任的革命信仰被新的时代瓦解,甚至吟唱长征而被人看似异类,也把他的高傲自尊踩在地上。
而在《钢的琴》中,革命话语的更多传承在工人阶级的身上。在新中国成立时期,工人这是光荣的职业,曾是共和国的骄子。而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机器生产开始代替手工,流水线作业已经不需要那么多工人,他们一夜之间下岗,自谋出路,离开自己引以为豪的职业。于是,工人这个词在现代化中被人摒弃。比如,陈桂林与妻子离婚,究其原因也是工人阶级没钱;女儿离开他,因为工人阶级已经没有支付高雅文化的钱;他去工厂偷琴被抓,因为没钱而竟干这些鸡鸣狗盗之事,或许这些我们可以一笑了之,但是不能忘记工人阶级的光荣时代已经被悄悄抹去,连带着最后小元义无反顾跟了母亲,陈桂林知道因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让“桂林山水甲天下”的愿望落了空。此外,在电影院追打人中,我们依稀还能看见“巴黎公社”的字样和革命烈士为国捐躯的崇高场面,可是它的另一面是年轻人在这里聚众打台球,犯了错落荒而逃,谁还记得这些英雄伟人。
三、黑白画面的两重天
张猛是学美术出身,所以其画面运用,尤其是黑白交叉的手法让观者身临其境感受一个逝去的时代。比如,在《耳朵大有福》中,满大街都是五颜六色的电视广告、内衣促销、美女走台步,这是一个彩色世界。而后出现的是王抗美家的阴暗,低矮的房子,狭小的空间,微弱的风光,这又是另一重天地,明显与新时期的大环境不对称。这两重天的强烈画面感,一方面让观众感受到新时代的先进气息,另一方面也将底层小人物的悲悯生活困境展示出来。
而在《钢的琴》中,这样的画面感更是不时凸显。比如,在影片开始,陈桂林的小乐队为别人送葬,后边是冒烟的大烟囱,这是工业化时代的象征。而后,他骑车去接父亲回家,一路上引人注意的是黑压压闲置的旧机器,而后抵达他住的鸽子楼,房子的外表都是黑色,让人压抑不已,但这正是钢铁时代的真实影像。而与其形成最大对比的是陈桂林妻子的白色衣服和白色轿车,如今的她是一个你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能在陈桂林的破旧家里住过的人,她光鲜亮丽的衣着与陈桂林的破旧不堪难以和谐,这就形成一种无声的反差:一个有钱过活,一个没钱养家。那么亲情的归属自然是女儿要跟着有钱的。这更揭示了小人物在新时期的可悲命运:没有钱,连亲生女儿都保不住。
黑白画面的真实运用,缅怀了真实的时代,也愈发让逝去时代的那些人的心无法安放。
与此前的《高兴》、《人在囧途》、《我叫刘跃进》等喜剧片相比,张猛的小人物系列电影颇有亮点,也让观众感受到一股悲痛的力量。之前,听到“钢的琴”片名,我曾不以为然,自猜就是父爱那点事儿。片名直观的感受曾让导演张猛苦恼不已,还为片名引发了一场讨论,而后张猛还是坚持原名。看过电影后,我猛然觉得电影只能是这个名字,其中的意蕴也只有此方能表达。这两部电影为张猛在影坛上奠定了一席之地,而种种奖项的获得也让之前的辛酸尘埃落定。
用音乐叙述,拿一切调侃,让崇高和现代在笑声中成为齑粉,让齑粉扑入眼睛,抵至内心,流出感动的热泪,这是张猛的目的。如果你只是傻笑,那对不起他;如果你只是傻哭,那更对不起他,他要的是苦中含笑、笑中带哭的五味陈杂。可惜,过犹不及,过高的要求让观众前半截一直傻乐,后半截该哭时却已无声,甚至还怪其又温情了一把。
注释
[1]笔名小熊 《<钢的琴>为何叫好不叫座?》
[2]谢丰、李国珏:后现代语境下小人物的悲情——解读电影《耳朵大有福》文艺评论;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