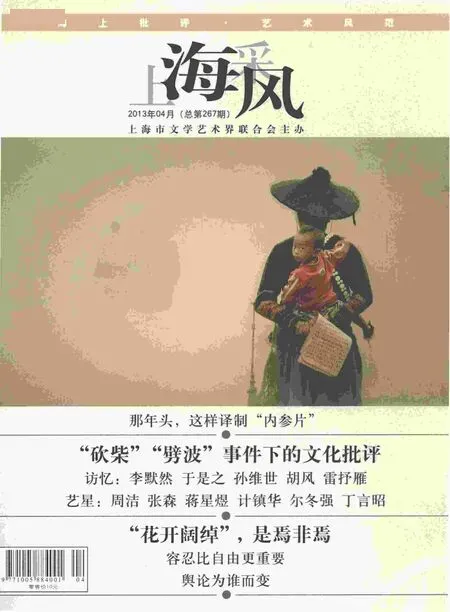观点集粹
两会要有高质量的讨论
成都商报刊文说,今年的地方两会,会风比往年大有改进,这无疑是八项新规出台后的好现象。但在赞赏地方两会会风转变的同时,亦不能忽视另一个或许更为重要和本质的问题,即如何提高两会的质量。为什么要强调会议的质量?因为两会是代表委员讨论国家大事和地方大事的会议。公众的利益能不能得到尊重和体现,国家和地方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如何布局,政府的钱怎么花……都要在两会上决定。一个质量不高的两会,很难达成社会利益最大化、于国于民最有利的发展方略或政策法律。开好会议的条件和要求很多,但像两会这种的重要议政场合,开好会议的一个关键要素就是代表委员能真实表达自己的看法,对报告的内容、议题和所形成的决议有坦率和深入的讨论,形成一种直抒胸臆的讨论氛围。因为每个代表和委员看问题的角度,所代表的行业和阶层不同,对问题的认识和看法也就不可能完全一致。只有讨论,才能达成共识,从而使会议制定和出台的法律制度及做出的决策和部署,符合实际和民意。没有真正的讨论,或者讨论不充分,这样的效果很难实现。当然,我们的两会有分组讨论的安排。但实事求是地说,讨论的氛围还不是很足。代表委员们纷纷发言,不可谓不踊跃,但表态式、学习式或感受式的发言居多。谈点感想,表个态,说些永远正确的话,似乎就算尽到了一个代表委员的职责。但这不是讨论,讨论必须要有观点的碰撞和思想的交锋,允许多种声音存在。国外议会开会时,议员们往往就某一个话题唇枪舌剑、互不相让,为此争得面红耳赤是常有之事。通过多轮辩论,最终取其合理的部分,尽可能地避免议事的片面性和决策失误。我们虽不一定要亦步亦趋,但在两会这样一个“议事”场所,也应提倡公开讨论和辩论。没有讨论辩论,大家都人云亦云,你好我好他好,这势必会降低议事的效率和质量。所以,笔者希望不仅在会风上,而且在对问题的讨论上,也要有个大的改进,形成讨论风气。为此,领导应先带头,在讨论时不作长篇大论式的讲话。与其他代表委员一样,领导在两会上没有特殊待遇。同时,应鼓励代表委员尤其是来自基层的代表委员大胆发言,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讲错了没关系,不善于表达也没关系,一次不行,有第二次,二次不行,有第三次,多发几次言,就学会了如何表达。如果两会很好地做到了这点,也就贯彻了民主原则,参政议政的质量就会提高。
什么样的笼子才能关住权力
京华时报刊文说,习近平在中纪委全会上表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那么,什么样的“笼子”才能关住权力呢?习近平强调了三个机制:“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这就为“笼子”打造了三个层面的刚性之墙,彰显出源头反腐的理念,而不仅是着眼于打击腐败分子。要打造刚性的笼子,即是要着眼于这种“源制度”的建树,使“一把手”的权力不要过大。腐败之所以出现“一把手现象”,根本原因在于制度设计上,没有形成“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当然在理论上,这样的“笼子”还是有的,但在实际中却容易变成“纸糊”的。在社会生活中,只要有权力的地方,往往就存在利益勾兑的情况。哪怕是一个看门的人,只要想进门的人输送一点利益,在一些守门人那里门就能轻易失守。哪怕是瘦肉精有十八道严密检测,只要送上200元,检测的人就可能直接放行。当权力天生就有容易腐败的特性,一个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权力尽可能地从不必要存在的地方退出,也就从根本上减少了权力寻租的机会。比如,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上的“新两个凡是”理念:“凡是公民能自决的,凡是市场能调节的,政府都要退出”,之所以引起热议,就在于它体现的正是这种让权力不能腐败的理念。
中国经济当与高增长勇敢“吻别”
新京报刊文说,当前恰是应与经济高增长勇敢吻别的时候了,否则中国经济将很容易在未来某个时段出现人们不愿接受的断点均衡,进而致使经济失去自主修复能力。这并非杞人忧天,而是目前中国经济不论是从经济社会可承载能力,还是环境资源的可吸纳能力等,都难以支撑GDP的高速增长。首先,历经2008年以来的经济刺激计划,政府、企业和居民等都陷入了难以承载的高杠杆负债水平,继续倚重高负债搞大规模的投资拉动(如某些研究机构认为新型城镇化会在未来带来40万亿投资盛宴),将很容易陷入整体性的债务风险、坏账危机之中。同时,伴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中国真实储蓄率将步入持续下降态势,若国内的投资无法从国外吸引非本国储蓄资源,那么经济增长将与通胀呈显著正向关联。其次,目前国内的能源和劳动力资源等早已不支撑经济快速增长。如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将意味着未来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时期已结束,在通胀等压力下劳动力工资将应景式上涨。更为重要的是目前国内自然环境的可承载能力已到临界值。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33个城市的可吸入颗粒物每立方米连续超过300微克,阴霾天气笼罩在全国主要大中城市。这预示着若继续践行粗放式增长模式,维系唯增长主义理念,中国将在不远的将来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由此可见,若继续通过投资拉动,以政府调动资源的能力,今年保持8%甚至重新站上两位数的GDP增长都是可以做到的,但这是以透支未来,增加未来经济社会风险为代价的。
中国需要新的社会政治哲学
南风窗刊文说,2012年7月,习近平在清华大学举行的“世界和平论坛”上指出:一个国家要谋求自己过得好,必须也让别人过得好。这句话非常形象地表达了一种理念,一种具有战略性的智慧:利他才能利已。
而就国内问题来说,这句话更具有解释和规范的能力,而且更为紧迫。因为很多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在政治经济社会的一系列博弈中,占优势的群体,没有考虑也让处于劣势的群体过得好造成的。
曾经一段时期,我们的社会政治哲学是:把整个社会假定为一个“我—敌”系统。改革开放后,新的社会政治哲学开始说话,“我—敌”系统瓦解,变成了“我—他”系统。合理利己主义,以及后来的“理性经济人”假定被广泛接受。而在博弈中,握有权力、资本、知识等稀缺资源的人,慢慢走向了一种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贫富悬殊,分配不公。群体事件不断。只顾自己吃肉,让别人汤都没得喝,这是一种具有自败性的社会政治哲学。
在今天,“谋求自己过得好,必须也让别人过得好”是一个超越性的理念,一种谋划。
各个阶层的人共同构成了一个在其中博弈的社会,如果制度设计没能让弱者获得改变不公平局面的预期,估计强者对未来的预期也很成问题。
拒绝“路遥文学奖”的理性与冷静
工人日报刊文说,“路遥文学奖”在京宣布启动。而媒体报道,路遥的女儿路茗茗觉得目前条件还不成熟,不同意设立“路遥文学奖”。在浮躁的时代背景下,路遥的女儿能如此冷静面对“路遥文学奖”的诱惑,可谓难得。能有一个用父亲路遥的名字冠名的文学奖,这既是很体面的一件事儿,同时也是对路遥及其作品的最好纪念。面对这样的好事儿,路茗茗的拒绝似乎有些不合情理,但在喧嚣浮躁的今天,我们恰恰需要这样的冷静。路遥的家人之所以拒绝“路遥文学奖”,一是担心“路遥文学奖”不严肃、不严谨;二是担心“路遥文学奖”出现意外状况影响路遥的声誉。这样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设立“路遥文学奖”当然是好事,启动仪式也很好搞,可作为新设立的一个文学奖项,“路遥文学奖”如何运作,如何发展,这些问题的确需要三思而后行。其实向文学奖说不的并非只有路遥的家人,同样冷静的还有巴金的家人。巴金老先生去世后,上海市作协也曾表示要设立“巴金文学奖”,但是巴金的女儿李小林明确表示拒绝。记得当时李小林的理由是,一方面巴老生前为人非常低调,不喜欢如此张扬;另一方面巴金清醒前就表达过,认为国内文学奖项已经太多了。我觉得“国内文学奖项已经太多了”这条理由很有说服力。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冯牧文学奖、冰心文学奖、郭沫若文学奖、老舍文学奖、沈从文文学奖、曹禺戏剧文学奖、艾青诗歌奖……数数我们国内大大小小以作家名字命名的各类文学奖,着实已经不少了。尽管奖金数额大小不等,但奖项设置、评委专家、评选程序大同小异。即使像茅盾文学奖这样比较权威的奖项评选,也曾闹出过抄袭的丑闻。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设立路遥文学奖,如果不能做到足够的含金量,实在意义不大。
央视播出“禁片”让人感到惊喜
中国青年报刊文说,最近央视6套播出电影《V字别动队》。这部曾经一度禁播的电影自上映以来首次在大陆公映,该片中的经典台词如“艺术家用谎言道出真相,政客用谎言掩盖真相”等,在网上广为议论。网友惊讶于央视会播放该片,更直呼央视越来越好看了。《V字别动队》原名“V字仇杀队”,讲述一个关于战争、毁灭、无政府主义、法西斯的故事。故事假定德国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沦为法西斯国家,人民生活在没有政治和人身自由的境况下。一个叫“V”的保安员在街上悄悄奔走,试图唤醒人们的反抗意识,把英国从法西斯魔掌下解救出来,几乎就是一个人挑战一个国家机器。据说,许多国家在六年前之所以禁播该片,是因为它除了虚构的极权恐怖之外,V的反抗方式仍然是恐怖主义的。如此说来,当初被禁也是情有可原。我国电影引进审查制度,长期以来带有行政管理性质,存在较多“雷区”和“禁区”,虽然引进片数量在增多,仍集中在主流商业大片上,以场面大、视觉效果强烈、节奏快的娱乐性影片为主,对血腥、暴力以及民主、自由等敏感题材,自会拒之于国门之外。这是把握社会舆论导向的必要之举。此番,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好莱坞制作的最怪异的电影”的《V字别动队》,在央视“解禁”,前所未有的“一刀未剪”,真的让人大感惊喜。这是否表明我国对引进片的审查尺度正在不断放宽,对所谓的敏感题材影片有了更大的宽容度,恐怕尚需观察。不过,它至少表明了管理部门的思想越越来开明。早有论者指出,“没有开放的心态,没有宽松的氛围,就不会有文化的繁荣”。确实如此,时代在变,人的思想在变,整个社会都在变,影视剧早已不是民众接受思想洗礼的唯一途径,引进片的意识形态功能也不必再像以前那样被无限地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