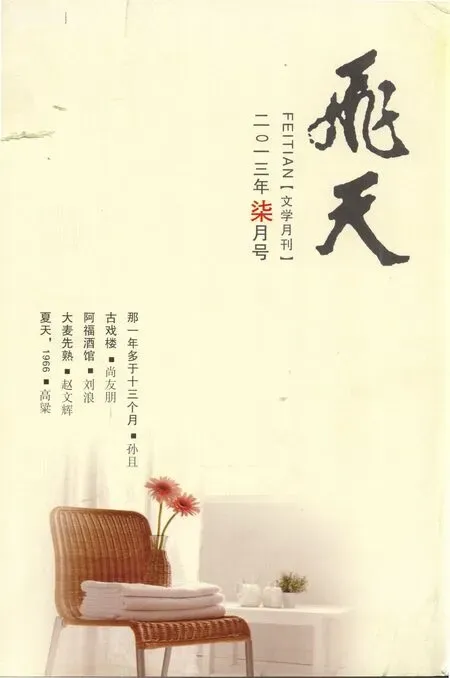甘南印象
▶ 胡 杨
当周草原
大凡印象,则不一定准确。而有了印象,又不容易抹去。因而印象这个词一直被用来用去,去了某个地方,不管怎么着,都用得着印象这个词。
我是第一次去甘南。甘南的朋友说,你四十岁了才去甘南,你年轻的时候干什么去了?说话的意思中有点抱怨,也有点讥讽。就是说,你第一次出远门,就应该去甘南。后来在班车上遇到一个藏族姑娘,问起年龄,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她知道我四十岁才来到甘南,很惊讶,就好像我四十年白活了。
回忆起整个甘南的游历,我并不觉得朋友和那个藏族女人的话有多么矫情和夸张,相反,我真正认为自己没有及早地来到甘南是一生的错误,但无论怎么说,还是来了,来了,就没有遗憾。
我是在当周草原上感受到这一切的。那是一处丘陵起伏的草原,草很茂盛,低洼处有水,高处也很湿润,草看起来鲜嫩鲜嫩的,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我喜欢这处草原的缘故,是它的自由奔放。单单是起伏的草原,单单是鲜嫩的草,它还谈不上自由和奔放。我说的主要是那些马、牦牛和它们的主人。我仔细观察过,牧马人和牧牛人把皮大衣铺平,躺在草地上看云起云落,我实在崇尚这样的生活,忍不住走过去看一看牧人的神情,一看,果然不出我的所料,是那样的自得和安逸。更有甚者,在草坡上弹琴唱歌,还有边走边唱者,确实是悠闲得不得了。是这些构成了当周草原的自由和奔放。在一个大场子,当地人修建的固定藏包和高高架起的扩音器,就多少让人不喜欢了。扩音器里的歌声太刺耳,草地上跳舞的藏族姑娘,又太具表演性,太煞风景了。
在草原上,应该做一个独行者,这样才能体味草原的精髓。我走上一面高坡,远处的草原也是由一面面高坡连接起来,无际无涯的样子,突然间的空阔,让我莫名地悲伤起来。世界是这样无涯,人生是这样有限,能让人产生真正悲伤的,也就只有这样的环境。我想象着一个牧人赶着它的羊群和牛马,驮着帐篷,从一面草坡走向另一面草坡,脚步停下来的时候,一定是什么拴住了他的眼神。是什么呢?这里的草和那里的草,如此相像,如出一辙,那么是什么呢?说不清楚。
当周草原就在合作市的边缘,一个城市和一片草原互不浸染,很难得。走过许多草原后我知道,所有的草原城市都是由牧人们展示马上功夫的赛马场演变而来的。合作市也不例外。牧人们呵护着自己的草原,端详着自己的城市,为自己的子孙留下了自己往昔的身影。因此,我更愿意把当周草原看作一匹酣睡的牦牛,它的毛发是那样的鲜嫩啊!
谁会选择当周草原,在这里支起一顶属于自己的帐篷,游牧余生,那他差不多就自由了。我有这样的愿望,也有这样的心情,但我终究还是背负尘世的拖累,无法放下积累已久的虚伪。在当周草原上,我学会了检讨自己。事实上,我早已忘记了对自己的检讨。很久以来,我在一种堕落的状态中津津有味地生活。
是当周草原挽救了我,至少,我知道我的缺陷。
米拉日巴佛寺
在合作市,有一处必须要去看的寺庙,名字叫米拉日巴佛寺。我觉得一座寺庙的有名,和它的名字没有什么关系,你记住了这个名字或记错了这个名字,佛都会原谅你的。说实在的,在草原城市,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寺院的,我很少去这样的寺院。但在合作市,因为主人的盛情,我有了一个例外。
这座寺院的建筑外观实际上就是一座放大了的碉房。碉房是藏族人尤其是我所见到的藏族人最普通的建筑样式。我曾有过居住碉房的经历。碉房至少都在两层以上,最底下的一层是用来圈养牛羊的,二层和三层是佛堂和人居住的地方。那是一个精神、灵魂和现实共居一处的奇妙之地。
走进寺院,香火缭绕,为了保护古迹,也可能是表示虔诚,前去参观的人都要脱去鞋子,套上一个塑料带。寺院的碉房式建筑共有九层,讲解员在讲述那些大大小小的佛像和雕塑的渊源以及米拉日巴佛的本生故事,据说在全藏米拉日巴佛的供奉庙宇只有两处。这些具体的细节我不关心,我只是感受其中的气氛,那的确是一种神圣的氛围,不由得你敛声静气,你为信仰的力量而倾倒,或者说有说不出的感觉让你肃穆。我就是这样。
我一层层拾级而上,在寺庙的最顶层,放眼望去,我看见了晾经台,那是一年一度的隆重佛事——晒大佛的场地。巨大的唐卡佛像在僧人的护卫下抬向山顶,佛像徐徐展开,万人俯首,我曾经看见过那样的场面,因为记得,忘记了拍照片。朋友还说,那就对了。拍了照片,就是对佛的不敬,你又积了善缘。这时候,我已两腿酸痛,但也按照当地人的习俗顺时针转回来。下了楼以后,沿着寺院的周边走,寺院的一周都是经桶,每个人都努力转动经桶,表达自己的虔诚之心。随行的朋友说,做恶深重的人,要绕寺院走七圈,才能解脱尘世的恶行。我相信,但我实在走不动了。想一想,按照佛家的教义,我们这些凡人,是“罪恶深重”的。
谁是我的前身,谁是我的来世。离开寺院,我在周边的藏式民房间走动,泥墙高耸,房门紧闭,一趟房和一趟房间的走道,竟然长满了草,看来是久久无人居住了。这在汉人聚居区是不可想象的。这里的居民也许在草原上,也许是在转经,也许他们在自己营造的精神家园中安睡,总之,他们的巢穴是自由的巢穴,因为不自由就要离开。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我是这样揣测的。
在合作市的宾馆,夜极静,夜色极黑,我分享着一天来的收获,回忆在米拉日巴佛的经历,就像走过了一条洗涤灵魂的通道,很是安静,就像这夜色一般开阔。
什么是平台化?杨斌解释说:“平台化指的是,通过整合产业上下游企业,用先进的PNP智能管理采购SaaS系统,促进资源智能分配,助力生产企业的信息化建设。简单地说就是,通过阳光印网这样的平台化建设,让平台服务于客户的能力越来越强,黏住客户,客户一想到印刷品就能想到阳光印网。”
野蛮的桑科
我的朋友写过很多桑科的诗,说起桑科就能想起他的诗。在我的想象里,桑科是个藏族男人,有一股子豪气。就在我要去桑科的那个早晨,我喝了一杯马奶酒,朋友说,这样你才可以去桑科了。我不明白其中的原由,但我知道,这是桑科的礼节。
桑科是一片草原。在没有去桑科之前,我曾断言:中国最好的草原在山丹。去了桑科之后,我又断言:中国最野蛮的草原叫桑科。
仅仅是无边无际、形式多样的草,还称不上野蛮,我说的是那条河,他奔腾不息、滚滚向前,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横冲直撞。而那里的藏族汉子无论是舞之蹈之,还是马背上撒欢,都有着这条河流的性格。有人说,那条河流叫大夏河,没有大夏河,就没有桑科草原。汇集长江黄河两条水系,整个甘南是滋润的,有了大夏河,桑科是滋润的,但他没有丧失野性,这完全是一匹良驹的品行。在桑科草原,一个人在草原走走看看,四野的风吹来,人很有可能会成为一匹有奔驰欲望的马,就像我终于撕开矜持的表面,狂奔了起来,狂呼了起来。这是自然而然的事。人的天性只有在草原上才得以展现,才得以发挥。你看草原上的汉子和女子,唱歌的时候,尽情地唱,旁若无人;跳舞的时候,忘形地跳,动作自如。人们说草原上的人是天才的舞蹈家和歌唱家,其实那是天性使然,也完全是自然的造化。这一切也都透露着一股子野气。应该声明的是,我这里所讲的野蛮,完全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境界,是自然的本相,绝无有半点贬义与愤恨。我向来讨厌那种一本正经的斯文,喜欢天性淳朴的真味。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桑科的朋友们招待我们的晚餐,其中的一道菜让我们眼界大开,一个鼓胀的牛肚热气腾腾地摆放在了桌子上,当时吃饭的人们大呼小叫,都不知道这道菜的名字,服务员说叫牛肚蒙牛肉。随后,一把刀子把牛肚割开,牛肚里烧红的石头已经把牛肉蒸熟,有扑鼻的香味,吃起来也是风味特别。朋友说这是桑科乃至全国最独特的一道菜。后来,我在研究嘉峪关新城魏晋墓砖壁画中的饮食时,意外地从文献中查到了这道菜的名字叫胡炮肉,记载中的做法跟桑科草原上的一模一样,只不过也有用羊肉羊肚做的。
应该说,这道菜也充满了野气,它绝对是桑科草原性格的组成部分。
海仁草
海仁草并不是什么草,而是一个藏族姑娘的名字。海仁草说,她的名字大概就是“度母”的意思,是美和善念的集合。在藏区,姑娘们都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卓玛”的居多,央金卓玛、萨仁卓玛等等,都有“度母”的意思,而“度母”又有“绿度母”、“白度母”等等,总之,名字的寓意美好极了。
海仁草不仅是名字好听,人也长得漂亮,有气质。在藏区,这样的姑娘很少见。海仁草出生在甘南草原上,至今,弟弟妹妹们仍然在草原上放牧,只有她考进了天水林校,毕业后在合作的一个林场上班。后来又调进了甘南人民广播电台。
海仁草向我讲述了她的信仰。她说,在草原上她应该是个知识分子,但仍然有自己的民族信仰。从前家里穷困的时候,每天只能点酥油灯敬佛,现在富裕了,可以捐钱给寺院,也可以在家里供佛焚香,节日的时候,还可以到寺院聆听讲经说法。无论何时何地,心中有佛,生活就更加踏实。
我清楚地知道海仁草所讲述的是真实的生活方式,我也知道,在草原上,人如果失去了信仰,就失去了一切。我记得一位草原上的行吟歌手曾唱道:在草原上,要么你相信一棵草上挂满了笑容,要么你悲哀。这是确切的心境。我曾说过,草原上那些目不识丁的牧人是伟大的诗人。这些话并不过分。
在与海仁草离别的那一刻,我说,你是一个诗人。海仁草羞涩地一笑,轻轻地走了,就像草原的天空上那一朵游走的云。
草原的凉爽
夏季的酷热在草原上熄灭。从另一种意义上说,酷热是焦躁的表情。而草原上的那种永恒的幽静,可以融化任何焦躁的内心。从戈壁绿洲到广大的草原,我像回到了冥想中的故乡,一切都显得熟悉,河流、草地、帐篷、牛羊,自然的东西,真切而又亲切。
小时候,在敦煌湿地,我幻想着长大后能有属于自己的羊群,我赶着羊群走向最远、最茂盛的草地。但是我还是发现,那片草地太小了,湖水的尽头开始荒芜,荒芜之外就是沙漠了。到了甘南,却不一样,那种绿色鲜嫩而虚幻,一直铺展到天尽头。老夫聊发少年狂,我虽没有步入老年,但也早已是心态老矣,尽管如此,也还是嚎叫了几声。是那渗透了骨髓的清凉,使我有了少年的壮怀激烈。
雾是草原的帷幔,阳光的手把它轻轻拉开,草原的舞台开始展现。草原上的桑吉卓玛打完了奶子,熬好了酥油茶,手搭凉篷看了看远处的草坡,此刻,她在盘算着要出牧了。这是一天的开始,男人的褡裢里装着酸奶疙瘩和甜奶疙瘩,军用水壶里装的是酒。一阵喧闹,一阵牛羊的鸣叫,场面显得凌乱,但等这一切都安静下来,牧人和牧群就远了,覆盖草原的仍是平静和清冷。我注意到,桑吉卓玛有条不紊地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把皮褥子晾晒在帐篷前的铁丝上,把马车架起来,去河边装水,表情平静如水。这其实就是草原的凉爽。
草原的自然地貌、山水与人的情形如出一辙,也是那样的平静而安详。
从一个帐篷到另一个帐篷,从一处草场到另一处草场,沁人心脾的清凉,使我的心境更加悠远。作为一个草原上的匆匆过客,我所有的新鲜感受,可能会随着时光的流逝渐渐消退,但不会变更的是那种挥之不去的清凉。
一次穿越草原的经历,使我认识了一种刻骨铭心的清凉。
清凉是雅致的前奏,也是草原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