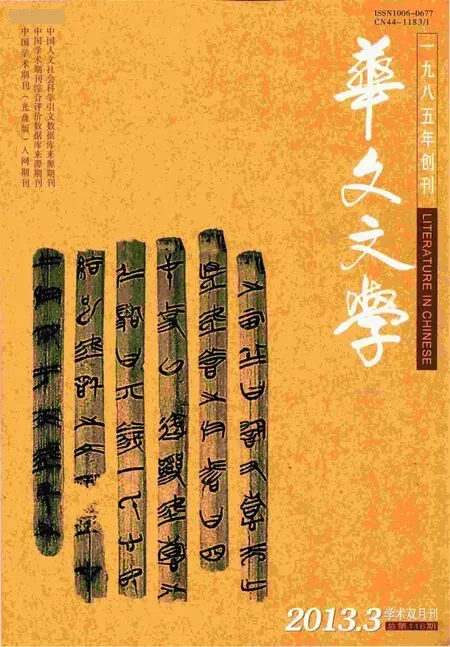文学政治一元论批判
李泽厚 刘再复
刘再复(下文简称“刘”):到美国来之后,我对这个世纪的文学,特别是创造社的革命文学、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延安的农民文学,以及解放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作了一些反省和重评。这些文学中有一些好作品,但是,就整体来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政治性太强,把文学等同于政治,文学创作转达政治意识形态,这事实上是一种政治式写作。罗兰·巴特《写作的零度》中谈论政治式写作,相当精采。他说政治式写作,一种是法国革命式写作,这是流血的祭典,为流血革命辩护的写作;还有一种是马克思主义式的写作,这种写作的进一步发展就是斯大林的。
李泽厚(下文简称“李”):这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政治压倒一切,也压倒文学。
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批判区分政治与文学的二元论,主张政治一元论,把文学界定为政治的附属品,要求文学附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要求文学成为政治的工具和另一种形式的军队,这种政治一元论对后来的文学影响太大了。
李:其实就一个作家来说,他本身也不可能是完全一元的。例如巴尔扎克,他在现实政治上,是一个保皇党。但是,他的内在感情和他的政治立场有矛盾,因此,他的作品反而是对保皇主义的嘲弄,是对当时各种人物和人性的真实描述,极有价值。
刘:我讲文学主体性时,就是要说明作家作为现实主体和超越主体要分开。在现实层面上,作家可以有自己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可以加入政治集团,但是在艺术层面上,也就是参与文学活动时,应当是超越主体,不应当以政治集团之成员的资格参与文学,而应当以一个独立人格的人参加,以艺术主体的资格参加,这样,他才能与现实事件保持距离,以超越的态度对事件进行反思、观照,此时,作家确实需要有高高在上的日神精神与品尝事件的酒神精神。
李:我支持这种看法。作家可以有自己的政治信仰和政治态度,但不要用政治信仰来干预、取代文学,以为政治一对,学术观点也一定正确,文学创作也一定成功。其实,创作往往与政治信仰分离或者根本无关。
刘:文学所以有存在的价值,恰恰是它大于政治,大于各种主义,它能完成政治、主义不能完成的事。政治的所谓“进步”,绝对不意味着学术与艺术也是先进的。绝对没有这些等式、逻辑和捷径。
李:我也可以举一个学术的例子。山东大学的《周易》专家高亨,他在解放前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自然也没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周易》,结果获得成就。解放后,他政治上“进步”了,自己觉得读了不少马列,已经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周易》了,结果其研究成果相当牵强,没有多少价值。最有意思的是,他解放前的研究成果反而接近马克思主义,而解放后的研究反而离马克思主义很远,妙就妙在这里,学术研究尚且如此,更何况文艺创作者要把马克思主义变作自己的东西并不是那么简单容易的。
刘:游国恩先生在解放前研究《楚辞》的东西也很有意思,1958年他作为白旗被批判后,他又自我批判,宣布自己过去的研究是资产阶级的,以后要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但是这以后他对《楚辞》的分析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李:我在1955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曾批评游国恩找出屈原作品的“民”字的多少来说明屈原的“人民性”,这简直太荒谬了,实在可悲。
刘:许多有艺术感的作家,都陷入一元论的困境。前几年,我讲何其芳的后期现象,就是发现何其芳的这种苦恼。何其芳在青年时代是一个很有才能、很有艺术感的诗人,但是,他到了延安以后,接受了政治一元论,创作就退化了。所以他曾两次感慨,说很奇怪,为什么我思想进步了,而艺术退步了。他是一个真诚的作家,所以才敢承认自己的退步。这种“思想进步,艺术退步”的现象,是我国当代作家的普遍现象。
李:他们就是吃了政治一元论的亏,以为政治进步了,思想改造好了,政治细胞多了,一切政治化了,艺术就会长进,这就大错特错了。我讲历史与感情的“二律背反”,讲历史和感情各有价值,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东西。在历史层面上,以感情代替历史、代替政治,就会出现反理性判断,造成对历史运动的破坏;在感情层面上,则相反,如果以历史以政治取代感情,就会扑灭感情,取消感情。
刘:文学艺术的存在价值,恰恰在于它完全不同于历史层面的东西。它必须超越历史层面,对历史进行反观反思,与历史保持距离,才有自身存在的理由。一元论就是抹煞这种距离,要求作家完全置身于现实的层面和历史的层面。一个作家,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可以有自己的立场,也可能不得不置身于一个政治集团之中。但是,在进入文学创作时,他应当超越政治集团的立场,抛弃政治集团成员的资格,而以作家的资格,即以作家特有的人道眼光和心灵参与艺术。这时,他就会与现实政治斗争拉开距离,把现实的残酷斗争视为一种人类尚未成熟时的不幸现象,并从中叩问人生的困惑和人类的命运,从现实的形而下境地进入超越的形而上境地。可是,政治一元论完全把文学艺术拉入现实的层面。
李:历史的要求,政治的要求,都非常明确,一点也不能含糊,但是,文学艺术则必然追求模糊,感情是个复杂的东西,爱中有恨,恨中有爱,错综复杂。一定要去追求确定、明确,就不是文艺了。当然也有比较明确的文艺作品,讽刺诗、马雅可夫斯基的诗等等,包括毕卡索的一些作品,但他们毕竟不是文艺的主要现象。连马、恩都主张少些席勒化,多些莎士比亚。
刘:我写的《论性格的明确性和模糊性》也说这个意思。这是非常重要的。要求文学立场坚定,态度鲜明,就从根本上毁了文学。人类情感中最精采的东西往往是那些说不清的、朦胧的东西。但是,在政治的要求下,什么都要非常鲜明、非常坚决、非常透彻,那么,只有图解最透彻,但是,一旦用政治图解代替艺术感觉,那还有什么艺术呢?
李:托洛斯基倒是主张政治与艺术二元,很有意思。托洛斯基这个人在政治上也很激进,很左,也是可怕的人物。但是他有艺术感觉,他比好些人懂得艺术,所以他不赞成政治一元论。
刘:鲁迅开始也介绍托洛斯基,认为他的文艺思想比较宽容,比斯大林宽容。所谓比较宽容,就是承认政治与艺术的二元发展,放弃政治对艺术的主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批评托洛斯基。
李:陈独秀也是有艺术感觉的,所以当时他特别佩服鲁迅的小说。当时鲁迅只是个一般作家,名气比他弟弟周作人可能要小,更不是什么伟大革命家。鲁迅本人自然极富艺术感觉,可惜后来的作品如《故事新编》的大部份,并不成功。我以为与明晰的政治观念等等有关。
刘:鲁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阶级论之后就是太明确了。观念太鲜明,政治态度太鲜明,这样,思想理念就压倒艺术感觉。《野草》就模糊,模糊反而丰富。鲁迅虽然革命,但不能接受创造社那种“杀、杀、杀”的革命文学。他最早发现革命文学的幼稚病。他对创造社的批评、调侃、讽刺是很有意思的。这些调侃,就是他完全看出所谓革命文学其实并非是真的文学。他毕竟是大文学家,对文学有很深的认识。后期创造社被政治理念毁得更惨。
李:鲁迅后期、创造社后期的创作都不如前期,就是后期太政治化、太明确了,这是一个教训。解放后出现一些很古怪的现象,许多人整天讲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甚至大讲美学,但连起码的艺术感觉也没有,像侯敏泽等人便都如此。他们完全不懂得文学和政治是两回事。
刘:在政治一元论泛滥之后,文艺界从事批评的人,都着意提高所谓“政治嗅觉”,结果,倒是对政治异常敏感,政治感觉器官很发达,但是,艺术感觉很差。所以他们就会一天到晚批判这个,批判那个,用所谓政治标准衡量一切,一进入艺术就完全不行了。陈涌把路翎《洼地上的战斗》的小说说成是丑化正义战争的作品就很可笑,这篇小说因为牵涉到志愿军战士与朝鲜姑娘的感情,他们就觉得这种感情危害政治,他没想到,连这点残存的、脆弱的感情都不允许存在,是不会有什么文学艺术的。
李:政治一元论走到这种极端,对文学艺术的危害就非常大了。
刘:陈涌评论长篇小说《古船》也是如此。《古船》是青年作家张炜写的。我很欣赏这部长篇。这部长篇的长处和过去土地改革的作品都不同,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其他这类题材的作品都不同。丁玲等总是把文学与现实政治等同起来,因此就把世界描述成两个阶级对立的世界,然后以清算意识作为作家的主导意识,那么,整部作品就讴歌残酷的斗争。作者和事件本身毫无距离,甚至比处于阶级斗争中的贫下中农还激烈。但是,《古船》却扬弃作家的清算意识,而以忏悔意识来重新面对土地改革的历史事件。他对这一事件,无所谓褒,无所谓贬,无所谓歌颂,也无所谓暴露。他和事件拉开距离后,以一种超越的态度来思考人类社会中一种不断循环的不幸现象:一群人欠下另一群人的债,一群人起来报复和索取债务,但是报复者又欠下新的债,一群人又进行反报复。人类就在这种报复与反报复之中循环。这笔债该何时了结?作家在作品中加以叩问。作家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感情是矛盾的、复杂的,也是模糊的。但是陈涌在批评这部小说时,完全用一种政治老爷的态度说,这样写土地改革是“不可以的”。其实,所谓“可以不可以”,是政治法庭中审判的语言,在小说中无所谓可以不可以。陈涌的感觉就是政治感觉,至于这部小说中的艺术变化和感情上的丰富之处,他完全感觉不出来。陈涌毫无艺术感觉,却从事一辈子文学批评,这对于他个人的人生选择来说,完全是“误入歧途”,选错职业;对于别人来说,则是“误人子弟”,危害作家。
李:没有艺术感觉的批评和理论,实在不能说是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可以说只是政治讨伐。可是以前就只有这种文学理论,所以我希望作家千万不要读文学理论,其原因也在此。我在1956年写的第一篇美学论文中就强调文艺批评和批评家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有艺术敏感,以后我反复举别林斯基的例子。
刘:他们对这句话很不高兴。我看到《北京日报》有篇批我们的文章,说这是“霸道”。后来,我在《二十一世纪》上写了一篇《告别诸神》,又支持了你的这个说法。我自己也搞文学理论,但这只是为了解构那些名为文学理论实为扼杀文学的理论。如果哪位作家愿意被他们扼杀,就去读他们的理论。1949年以后,所有作家都吃了他们的亏,中了他们的政治病毒。
李:吃亏吃大了,尤其是老作家,吃了大亏。
刘:许多很有才能的老作家,他们在二十、三十年代很有成就,可是后来他们也相信政治一元论,或者受政治一元论的影响,结果写出来的东西没有什么价值,很可惜。我常为他们感到深深的惋惜——文学的才能无谓地消耗在无休止的政治游戏之中。天才为庸才所骗,这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一大现象。
李:点破这一点,把政治与艺术明确划为二元,很有好处,很有必要。如果文学理论要对作家有所帮助的话,就要指出这一点,就是要抵制一元论,一点也不能含糊。不过我们这种“理论”一定会被看作大逆不道。这还了得,要文学完全脱离政治。其实我们不过是顺着马、恩讲述的不要席勒化的意见,并根据数十年来失败的经验,作些延伸而已。这种延伸是有美学依据的,也有审美心理学的依据。
刘:作家一相信政治一元论,实际上就成了“笔杆子”,还要代圣贤立言,只是这个圣贤变了,不是古圣贤,而是现代圣贤。过去,我以为只有八股文才能代圣贤立言,现在才知道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美术、音乐都可以代圣贤立言。音乐发展到最后是“语录歌”,诗歌最后一律是歌颂红太阳,小说一律是阐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不是典型的为圣贤立言吗?
李:我一直最讨厌“笔杆子”的名称或说法。文人一成为笔杆子还有什么意思,笔杆子的意思就是别人执笔,你只是杆子——工具而已,因此,要你写什么你就写什么。这样,作家就相当于秘书的角色。何其芳到延安后也去当了秘书,诗人作了秘书,当然当时是为了革命,放弃一时并无实用的文学,后来他还是从事文学,但是否受“秘书”角色的影响呢?当上笔杆子,当然光荣得很,林彪说革命要靠两杆子,枪杆子和笔杆子,为革命作宣传、作文告,当然大有贡献,但这些都并不能算文学。所以思想虽进步,艺术却可以退步。因为不再去培养自己的独特的艺术感受了,这一点也不奇怪。
刘:可以说,是个性化的思想为集体化的思想所替代、所淹没。文学是充分个人化的活动,一旦纳入集体轨道,就糟了,当别人的枪使就更糟了。
李:我在哲学界混了几十年,一直当不了“笔杆子”,也一直不愿意去当。我多次拒绝过出题作文,我的确作不出来。有人说我是不识抬举。据说“文革”前康生曾看上过我的“文采”,有人透露这个“消息”给我,我赶紧躲得远远的。那时连田家英不也说康生是东海圣人么?康生的文化素质的确不低,字就写得不错,中国古典、马列经典也熟,比今天好些人强多了,但就是人太凶险狡诈。当然当时我也并不知道,就是不愿见大官而已。据说周扬也想提拔我,这是潘梓年亲口和我说的,我自然是退避三舍,一些人说我“太不争气”了。于是我在哲学所一直挨整,挨各种欺侮,其实当时跟上了周、康,挨的整便更大了。我并无此先见之明,只是抱定不当“笔杆子”而已。
刘:把笔杆子和枪杆子并列,这样,笔杆子就不是一般的笔杆子,而是火药味很浓的笔杆子。因此,文化批判就变成武化批判,文学理论也变成武学理论,整天鼓吹“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满篇文章用的是“阵地”、“堡垒、“拿枪的敌人”和“不拿枪的敌人”等军事术语。
李:军事的术语到处泛滥,至今还流行的如“突破口”、“决战”、“阵地”、“攻坚”等等,都是军事用语。现在文章仍在大量运用,特别是大批判文章。这种语言现象所包含的精神现象很值得研究。在这里,也正好可以补充说一下,我说的救亡压倒启蒙,在四十年代之后,主要是指军事斗争的救亡压倒了启蒙。在军队里,当然一切行动听指挥,不允许有什么个性解放、个人独立、个体自由等等,一切服从战斗需要,人人都是战士,火药和硝烟压倒一切。这在当时当然是合理的、正确的,但把它延续到和平时期的全社会中来,便不合理、不正确了。
刘:这一套转入文学领域,自然是火药味、硝烟味压倒人情味、文学味。军事斗争模式转化为文学叙述模式,自然是两军的对垒,自然是残酷的血的代价,什么都是生死存亡。很可惜,当历史从军事斗争的战争时代转入和平的建设时代之后,也就是枪杆子已不再驰骋沙场之后,笔杆子还是笔杆子,充当笔杆子的人没有回到作家主体的位置上,如果有人想回到这一位置上,所谓文学理论家实即政治感觉器又要加以讨伐。
李:其实,人类之所以需要文学,恰恰是因为历史的进步,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中,科技的进步更需要另一种东西来补充、来对抗、来“解毒”、来解理性过分之“毒”,文学就是一种。所以从性质上讲,文艺不同于科技,不同于社会科学,甚至也不同于人文学科。正如小说中和舞台上的曹操与历史上的曹操并不相符,而两者却可以和平共存一样。你在许多文章中强调文学艺术有自己的一套规律,这是对的。不能用政治的规律、历史的规律,包括科学的规律来取代文学的规律。
刘:我讲文学史发展的悖论,也讲到这一点。就是说,文学不能笼统地讲它随着历史的进步而进步,“进化论”难以解释文学发展现象。因为文学作品一旦产生之后,它就成为一种独立自主的存在。在时间层面上先后产生的作品,并不意味着价值的高低,时间顺序和价值顺序不是同一的。
李:文学艺术其实没有什么“进步”问题。进步是一种价值判断。不能说罗丹的雕塑就比古希腊的雕塑进步,也不能说托尔斯泰就比莎士比亚进步。这种观念发展到极端,就会像文化大革命中那种把过去的文学艺术一律称为“封、资、修”、“名、洋、古”,唯我今天的样板戏最进步、最伟大。
刘:你比较早就注意文学的时代性与永久性的矛盾,注意文学对时代的超越。杰出的文学作品总是既居于它那个时代,又不仅属于它那个时代,具有永恒的魅力。
李:这就是情感的力量,情感的魅力。1955年我提出文艺作品的时代性与永恒性,以后提出历史与伦理的二律背反,以后又提出“情感本体论”,都在说明伦理、情感作为人类本体的特殊的和独立的巨大意义。我强调人类本体是自己建立起来的。艺术的价值就在于此,它与人类的情感本体直接相关,是它的某种物态化了的对应物。艺术可以永恒不朽,它永远打动着人们心灵,塑造着人们的情感。这就远远超过为一时一地的政治、伦理、宗教服务的作用和功能了,正因为如此,一千年之后的人类还会与我们此时的情感相沟通、相联系。政治就做不到这一点。
刘:说文学艺术是“不朽之盛事”,说“文章千古事”,是有道理的。把文学等同于政治,等同于现实,就从根本上抛弃文学这一优点。当然,有些作家艺术家视“文学艺术就是一切”,也不好。对自己估计得太高了,太了不起了。两个方面都不对。政治家把文学看成是自己的仆人和工具是不对的,而文学艺术家也不能把自己看成是超人的。超人也要靠人供养的,不能不吃饭。王国维把文学家提得很高,他说:“一百个政治家也顶不上一个文学家。”
李:但也要看是什么政治家。小政客、小爬虫,当然是一百个不如一个。但是真正的大文学家、大政治家,都有价值。最伟大的文学家在世界上是屈指可数的,伟大的政治家也不太多。不过,有一点是确实的,政治家的作用主要在时代性,政治家只能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代中起作用,他们的遗产对人们,特别是对人们内心成长的作用和影响并不直接、并不重要,只有文艺世世代代直接影响、塑造人们的心灵。所以曹丕才感叹只有文学才是“不朽之盛事”,帝王将相都比不上。但是如果没有秦皇汉武,也就没有今天的中国,所以彼此又不能取代,不必去比高低。
刘:这里也包含着历史前进的二律背反。
李:是啊,历史总是在矛盾中前进。情感的、伦理的东西与政治的东西在不同的层面起作用,有些时候两者协调发展、相互促进,但有的时候,两者的矛盾和冲突又很激烈。
刘:这也是二律背反现象。历史悲剧就是这种二律背反的悲剧,所以那些看到改革中贫富分化的现象而痛心疾首的人,在某一层面上是合理的,这正是历史悲剧。
李:我的意见也是这样,作品的评论首先是感受,不要从概念出发或从政治出发去分析。感受比较复杂,作品给人一种刺激,批评家从这种刺激获得一种感受和理解。这种理解与先验的批评尺度很不相同。如何理性地分析这种感受从而分析这个作品,这是我上面提到的1956年第一篇美学论文提出的主张,但至今也得不到多少反响,批评家们或是从教条出发,或是赶时髦,只研究文本。
刘:沈从文在解放后就是在先验的政治尺度下,被说得一钱不值。然而,一旦文学回到文学本身,一旦以文学的眼光去看文学,就会发现蓄意回避政治、回避政权、回避主义的沈从文倒是有文学价值,他更有生命力。
李:沈从文是现代文学中没有掉入政治陷阱的为数不多的作家之一,他没有成为政治一元论的俘虏。但他停止了写作。
刘:他付出的代价是暂时的,在解放后他经受批判、寂寞,被抹煞。但是他收获的东西却是永久的,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作家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