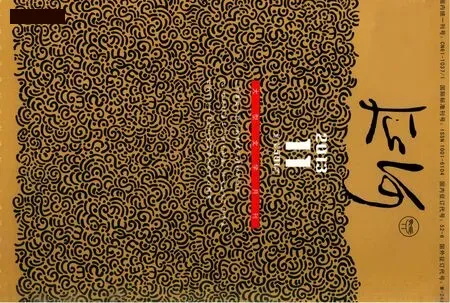怀帆诗辑
张怀帆
中年患者
耳 鸣
我的耳朵里住进了
一只鸟
每到晚上,它就开始鸣叫
那是什么鸟?
声音清纯细长,不像我认识的
所有鸟叫
不管怎样,我想
它来自树林,飞过山水
飞过蓝天,飞过田野
选中我的耳朵
说明这个巢穴一定
与众不同
也许它要给我传递重要信息
那该来自高处 远方
也许它只是喜欢唱歌
把我看作了知音
不管怎样,我都欢迎
这么多年,我听惯了杂音
刚好可以,静下心来
听另一种声音
灰指甲
足浴时,技师告诉我
我的一个脚趾长了灰指甲
那指甲,中间一团血红
像一面日本国旗
起初,我没理会
那指甲,不痛也不痒
想起技师说会传染
我开始有点紧张
当脚趾升起十个红太阳
我不成了汉奸?
我赶快去治疗
涂一种紫色药水
直到有一天,发现指甲的
那团血红,形状变得像
钓鱼岛
眼 疾
我得了眼疾
看什么
都疼
听说花养眼
便去看花
但发现春天的风沙刚过
花都已经沦落风尘
知道美女好看
于是去城里,站在街边
但发现所有的美女都
刺眼
看电脑 看手机
看多了形形色色的人 乌七八糟的事
——我看到的
让我眼疼
晚上,一个人躺在床上
看天花板
看黑暗
以后,要多多看山 看水
看书 看天上的星辰
看脚下的路,和
天上的流云
老年斑
好端端,额上生出几枚斑
模样可憎
便去找大夫,意欲剿灭
大夫翻起眼,从眼镜上沿一看:
老年斑!
我告诉他我也就四十岁
是不是早了点?
大夫说如果说成青春痘
会不会觉得他行骗?
我有些沮丧:
别人中年得痣
我却中年得斑!
但很快就释然:
凡从额头上生出的
必与智慧有关
还应该庆幸,大夫没说是
蝴蝶斑!
蛀 牙
那是一条什么样的虫子
比如一个命里的小人
比如一场刻骨铭心的爱情
在不经意间
把我身体的某个部位掏空
那是怎样一个空洞
比如一件破损的乐器
比如一个时光的器皿
演奏过谎言和废话
镂刻过岁月的酸甜苦辣
却最终,遭遇柔舌的暗算
几十年,我已惯看坚硬的事物
对于人生,对于人
我不会再咬牙切齿
以牙还牙
一颗牙
咽进肚子里
一颗牙,我把它
扔进了大地和人群
剩下的牙
我要微笑着露出
并对生活说
茄子
脱 发
这一丛草
不知它为何占据我的头顶
或者飘逸过我的胡思乱想
或者纠结过我的懊悔
或者,和我合谋过一个女人
但现在,它们对我逐渐厌倦
纷纷弃我而去
在枕畔,在卫生间
还有一次,在无辜的床边
更多的,各奔前程
自由飞散
它们不愿再记录风的形状
愤怒也不能让它们飞身跃起
任由一张手的梳子胡乱摆弄
忍气吞声地让一把剪刀肆意宰割
逐日而稀
像一棵树的落叶
剩下的,还能坚持多久
也许有一天它们全部告别
那将是它们集体完成的
一个作品
发 呆
我常会一个人出走
漫无目的地来到一个地方
坐下来,发呆
在山坡上,看蚂蚁浩浩荡荡搬家
有时竟也打架
看蜣螂悲壮地推动粪球
不远处,一棵针尖大的花
亮莹莹举起杯盏
在小树林里,听蝉,听蜂
听一只鸟和另一只鸟
谈情说爱
一阵风,轻快地翻遍树叶
在一条河流边上
多次看见河水兀自远去的背影
阳光,一点一点越过高岸
更多的时候,足不出户
靠在床头,听绵长的雨
倚在窗前,看花花绿绿的行人
有时,我觉得自己像个
多余人,或者游手好闲的懒汉
在现世中,也越来越像个
呆子
我担心未来有一天
我会不会老年痴呆
但有一次,当我去一座寺中
变得释然
我看见一个光头的人
一动不动地坐着发呆
头上一只小飞蝇爬来爬去
他都闭着眼睛
懒得去管
呵 欠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发现自己的呵欠增多
有时在会场
有时在人群里
还有时,只有我一个人
我不知道,这个不雅的动作
有什么象征意义
是吃得太饱,睡眠不足
还是对许多事情
我已心生厌倦
或许是,许多年,攒了许多话
没有合适的人说出
堵在了胸口,不断发酵
便变成一口气
一吐为快
有一次,在乡间的一棵花树下
我一边晒太阳,一边打着呵欠
听见田野的一头驴
仰天长啸 壮怀激烈
从此,我为自己的呵欠
感到自惭
健 忘
看过的书,多半过目就忘
吃过的饭,总是想不起了味道
去过的地方,往往会张冠李戴
钥匙一次次锁在家里
手机经常要用另一部手机寻找
有时,握住一个熟人的手
寒暄半天,但怎么也叫不出名字
裤子的拉链,已出现多次忘关
晚上脱的袜子,常会
第二天早上就找寻不见
有一次去超市,付完钱后把东西留在柜台
还有一次打的,竟然想不起了租房所在的地名
据说,鱼的记忆只有七秒
我难道正在变成一条没心没肺的鱼?
但我还能看见老早的一个人的雀斑
也能想起一个人暗算我的笑脸
一封竖写的信,一袋新茶,一场纷纷扬扬的雪
一杯咖啡,和临窗桌子上冒着的热气
一个八斤四两的孩子,一道肚皮上的刀痕
一场瘟疫,一场地震,一场家门口的比赛
是一个拳头大的心脏,还是两个半球的大脑
让成为鱼,永远是梦里的事情
但明天起,我还是要背诵老婆的生日
儿子布置的作业
我还是要不断念叨:我爸是农民
我爸的爸是农民,我爸的爸的爸是农民
而我,只是一介书生
失 眠
这一生,我对不住枕头
遭遇这样一颗不安分的头颅
算它倒霉透顶
将来走时,我愿意把它带上
在另一个世界好好珍惜它
或者,如果有来生
让我变成一只枕头
替它到人世遭罪
我为什么要在深夜里
胡思乱想那些人间的破事
多年后,我已经养活不住头发
并学会和黑夜妥协
我还在坚信,在某一个深夜
我会听到高处不为人知的风声
或者另一个世界传递而来的讯息
我的失眠,不过是等待和考验
我已做好了准备:
只有躺在棺材里,才不再失眠
现在我愿意相信:失眠
离上帝很近,离死亡很远
雪落小镇
小旅馆
她举着身份证
勘察我,像核对一个要犯
她还仔细地翻检我的背包
似乎要寻找一个隐藏的炸弹
她漂亮的脸,不动声色
像一件冰冷的瓷器
绕了几截逼仄的楼梯
我走进一个房间
一张木床,床单苍白
对房事已经冷淡
临床的木桌上,一只雪白的搪瓷杯
小资,有洁癖,对床下
两只塑料拖鞋,孪生的乡下兄弟
不屑一顾
一台老式电视机,隔世的道具
卫生间,曲径通幽,闻流泉之声
没有毛巾,没有香皂,更没有避孕套
只有瘦骨伶仃的牙刷,醉倚在自己的酒缸里
我断了任何非分念想
这样的旅馆,让我安心
一觉醒来,天下大白
小米粒
我住在小米粒大的小镇
小米粒大的瓦房
颜面上小米粒大的黑痣
把小米粒大的秘密珍藏
我仰望小米粒大的星星
闪耀小米粒大的光
俯视小米粒大的蚂蚁
把小米粒搬进我窗下的洞房
我怀着小米粒大的情爱
小米粒大的梦想
我的生活有小米粒大的疼痛
小米粒大的蜜糖
我坚信小米粒的金黄
小米粒的香
死后愿做小米粒被麻雀衔走
种在陕北向阳的山坡上
其实,地球在宇宙里
也只是一颗小米粒
安静地,闪着
小米粒的光
雪落小镇
山白了,地白了
房子白了,树也白了
但是,通向小镇外的那条柏油路
还湿漉漉地黑着,唯一的公共汽车
昨晚停靠在车站路边,不再等行人
雪花飞到它喜欢的去处
把其他地方覆盖,让小镇戴个帽子
露出
小街上,稀疏的行人
步伐缓慢,似乎都漫无目的
麻雀也不见了
偶尔会碰见一只毛茸茸的狗
但是,街上的小酒馆还开着
卖糖葫芦的大爷还推着他的小推车
顽童,在哪个地方
偶然点响爆竹
我是说,远方来的朋友
就不要急着回去,留下来
我们一起喝酒
五棵梨树
楼前的五棵梨树
决定今年不开花了
一场雪,一场春天的
葬礼
夜晚,我隔窗望见一轮满月
像圣母,在梨树头顶
又一个晚上,树梢上只挂
一粒寒星
清晨,疯女来到梨树下
一个人低着头,梨花般地笑
她也许知道了梨树的秘密
夜里,我听到一只小犬
掏肝掏肺
又一个夜里,是一只
异地的鸟鸣
去年,我在梨树下
等到了一个人
今年,我在梨树下
将等不到一颗梨子
火车头帽子
戴火车头帽子的男人
我在售票厅排队的人群中看见他
方脸,浓眉,一脸雕塑
我猜他来自钢铁厂
或者建筑工地
戴这顶帽子,显得庄严
不敢冒犯
我喜欢坐绿皮火车
长长延伸的铁轨
缓缓掠过的风景
车轮的节奏,时而欢快,时而悠长
拨动人在旅途的淡淡惆怅
这样的火车
一定开向希望的大地,温暖的家
开进美好的未来,春天的原野
戴火车头帽子的男人
是大厅里唯一戴火车头帽子的人
这是旧历年关,外面已零星飘起雪花
我相信,这顶帽子会给他带来好运
让他顺利买到火车票
在大雪降临前登上绿皮火车
回家的路途,火车头帽子伴在身边
护佑火车,一路平安
可我买到的是动车票
动车头,像鸭舌帽
在动车里,听不到火车的心跳
呜——只有风
睡一小觉,睁开眼
发现已到
我尤其不想
成为戴鸭舌帽的男人
过年的事情
又是一年春节
妈妈在厨房里
炖一只乡下亲戚送来的土鸡
整个屋子,都弥漫着久违的香气
父亲和我坐在桌前喝酒
一种父亲珍藏的高度数的高粱酒
我只能浅尝辄止,他却总一饮而尽
我们聊天,都是乡下的事情
其实,我更像一个旁听者
不过,我很耐心很认真
很多年了,难得和父亲
这样坐在一起
不知什么时候,我们竟然
轻松愉快地谈起了死亡
父亲说他将来还是要“回”乡下老家
埋在爷爷的坟前,妈妈听见
就从厨房里出来反对
她说那就你一个人去吧
她要跟孩子们在一起
鸡肉端上餐桌,热气腾腾
妈妈把一条鸡腿夹进我碗里
窗外起了鞭炮声,我们吃饭
说起了其他事情
好像又坐在老家窑洞的土炕上
院子里,有公鸡打鸣
红灯笼照耀的小镇
把窗玻璃擦亮
把一年的好光景擦亮
我的瑞雪照耀的小镇
在旧历的年关,空气清冽
每一个屋前,都飘出温暖的清香
该打烊的都已关起店门
只有卖对联的大叔,还在忙碌地挥舞着毛笔
卖水果的大嫂,还笑着红扑扑的脸
我的红灯笼照耀的小镇
鞭炮声已零星响起
孩子们,已迫不及待地追着新年
春风已走在半路,就要翻过剩下的几座大山
枝头的雀儿梳洗着羽毛,也准备过年
我的阳光照耀的吉祥小镇
正在准备出炉新年的第一个太阳
这个时候,来,我们抓紧贴对联
这个时候,让我抓紧写下迎接的诗行
圣诞节,探望父母
小城里我的父母
农村来的移民
还没听说过圣诞节
也不知道耶稣
这样刚好,他们就不要为
包饺子赶早买菜忙到捶腰
这样刚好,他们还会在开门时
惊愕地喜出望外
从始至终
父母都欣悦地打量着我
好像我还似他们的圣婴
而我也貌似虔诚地听他们的絮叨
好像他们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圣经
也只有这一次的告别最温馨
父母穿着厚厚的棉衣站在门口
笑呵呵地
像两个慈祥的
圣诞老人
生 日
一个人,他惦记着我的生日
其实,他更惦记的是那个蛋糕
另一个人,记住了我的生日
更像是提醒我别忘记了她的生日
还有一个人,三十九年
一次不差地自己给我过生日
但我却很少想起她的生日
甚至,忘了那个具体的日子
剩下的她的生日,再一次也不能忘记
不然,就只剩下了忌日
归 家
在所有的交通工具中,我最喜欢火车
飞机清高得有点身影孤单 云里雾里
汽车有些轻浮,斗牛一样鲁莽
想得见却望不见尽头的铁轨
刚好可以装得下我的寂寞和思念
在所有的铁道线中
我最喜欢西安—延安的旅程
我在西安城墙外的一个地方上班
偶尔喝酒 写诗,想起延安
小城边上,挑着我小小的家
在西安—延安的所有列车中
我最喜欢T次这趟
白净的床单,刚好适宜我半躺着看书
临窗的座,刚好适合我轻微地发呆
下车前,我喜欢把看过的书放在座上
并且相信会被下一位旅客拾起
一直传递,多年后又与我不期相遇
下了车,火车泊进港湾,很快安静
小城的灯,正次第亮起
趁着暮色,我拉着手提箱
不为人知 轻轻地穿过街道
远远地,就看见一盏灯
精神抖擞地亮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