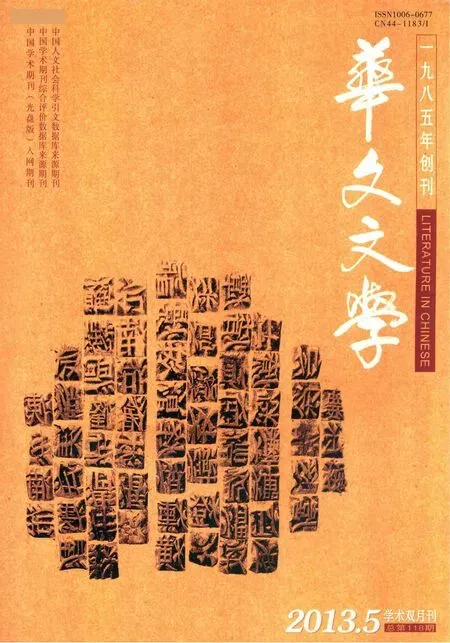《跨文化视野下的北美华文文学》序
[美国]陈瑞琳
王亚丽,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2010年的春天。我应邀去她任职的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讲课,讲的题目是“当东方遇到西方”,即从东西方文化的交战谈到海内外文学的挑战。会后,亚丽告诉我,她正在陕西师大就读在职博士,论文已经开题,她的心愿就是研究海外华文文学,主要是北美的华文文学。我抑制住自己内心的感动和惊喜,仔细端详着这位来自内蒙古大地的年轻女子,她的眼睛里有一种燃烧,身心里有一股坚定的顽强,多么像二十多年前走在校园里的我!一时间百感交集。
时光回溯到1989年,我在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首次斗胆开设《台港及海外文学》选修课。这是一门崭新的课程,犹如一股清新拂面的春风,立刻吹皱了当代文学的一池春水。前来听课的学生挤满了阶梯教室,他们激动地告诉我:“在西北的所有高校中,您是第一位开设这门课的老师!”走下讲台,遥望天地悠悠,那时的我感觉自己在手持一柄星火,等待着有一天野火燎原。
1990年,我将自己那一年草创的“教案”收入在了《中国当代文学》(雷敢、齐振平主编,陕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一书的第九编中。在那一刻,我有一种预感:关于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将会成为中国当代学坛的一门“奇学”,甚至发展成一门“显学”。这丛奇妙的火焰正在从东南沿海的学界燃烧过来。而我的心里也正在孕育着一个梦想,那就是地处周秦汉唐的大都西安,也必将成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内陆重镇。在这片泥土厚重的土地上,将屹立起一代放眼世界的学者,他们以自己穿越时空的锐利目光,将东西方的文化长河打通,并架构起新的文学桥梁。
时光终于到了2012年,怀着多年的梦想与期待,我读到了王亚丽博士的这部《跨文化视野下的北美华文文学》研究专著。作为陕西师大文学院历史上第一部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博士论著,虽然来得稍晚了一些,但让望穿秋水的我依然是激动不已,依然是感受早春的那般惊喜!感谢她的导师李继凯先生,这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资深学者,敢于放手,给自己的学生一个广阔飞翔的空间,让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扩展到一个崭新的领域,实乃学术胸怀的壮举。
关于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可谓是中国当代学坛新兴的也是最年轻的一门社会科学。说它是一门“奇学”,是指它在学术的内涵和外延上正在迅雷不及掩耳地扩展和延伸。与此同时,这门学科正在为中国的当代文坛产生双向交流的现实意义:其向外的意义是传播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向内的意义则是借鉴性地引进海外的新文化。宏观地考察海外华文文学,有两个凸显的研究重心,一个是对中华文化的纵向传承,另一个就是在新的层面上进行中西文化的对话。
著名学者刘登翰先生在他的《华文文学——跨域的建构》中曾指出:华文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包含着一个理想,即“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这个世界,有共同的文化脉络与渊源,又因为是跨域的,便凝聚着不同国家和地区华人生存的历史与经验,凝聚着不同国家和地区华文书写的美学特征和创造。这样正可以形成一个可以对比的差异空间。有差异便有对话,而对话能够使我们更深刻地认清自己,不仅是特殊性,还有彼此的共同性。这段话正是点出了华文文学研究的意义所在。
研究海外华文文学,首先面临的正是区域性特征。如东南亚华文文学、北美华文文学、欧华文学、澳华文学等,他们虽然各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内涵,但也都具有着例如“寻找文化身份”的总体特征,都经历着从华侨到华人再到华裔的演变过程,一方面以所在国的异乡文化重新辨识和书写着自己的华族文化,同时也以自己的母文化坚持进行着失语的抵抗,防御着异文化的压迫与消蚀。正因为海外华文作家具有着面临多元文化的优势架构,所以当他们展开海内和海外双重经验的书写时,特别是在表现他们的中国经验与中国想象在不同地域、族裔、社会、文化领域的独特内涵时,就产生了极其宝贵的关于“离散与边缘”的美学理想追求。
随着海外华文文学的不断创造和成长,美华文学的研究日渐凸显其重要的学术地位。可惜在美国的高等学界,多以英语文学为其主要研究课题,华语文学则被列为少数族裔文学,因而很难进入学科研究的重点。正因为此,美华文学的梳理和研究亟待发掘和整理。欣喜的是这个庞大的崭新课题如今正在国内的学界逐渐展开。
关于北美华文文学的历史性贡献,王亚丽博士在她的著作中做出了非常清晰的整理和论述。她以极其宏观的视野,精确地把握了中国对世界的早期贡献、华工对美国的贡献、现代留学生对美国的贡献、台湾留学生对美国的贡献、大陆新移民对美国的贡献等。尤其是她在纵向的研究中,看到了北美华文文坛发展长河中的三个主要浪潮,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北美“新移民文学”所取得的重大收获。
在王亚丽的整体论述中,她抓住了海外作家“边缘书写”的精神特质,找到了“文化认同”的内在通道。特别是能够从历史的渊源脉流上梳理出海外华文文学跨文化的意义,达到了当今华文文学研究崭新的理论高度。更难能可贵的是,她一方面在剖析异质文化的内涵冲突,一方面深刻地阐释了家园记忆的原乡想象和故国书写。与此同时,她创造性地发掘了在“性别意义”下完全有别的文化认同危机和心理特征,尤其是对男性作家的分析非常独特到位。她甚至还涉及“城市书写”、“唐人街的文学意义”这些极具学术挑战的新领域,对北美华文文学的研究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令人敬佩的是,在此书中,作者使用了大量的联想和对比资料,从而使得她的思考打破了传统的藩篱,在丰富的立体结构中具有了逻辑判断的力度。让我更感动的是,作者由于阅读资料的翔实和广阔,有关“北美新移民文学”的研究取得的成果尤为显著。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浪潮,“海外新移民文学”逐渐成长壮大,尤以北美文坛阵容最为强大。仅从1978年到2007年底,中国大陆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120多万人,而以北美人数最多,占到总人数的百分之八十。据统计,整个美国的华人人口目前有270万,大陆新移民的比例已占到三分之一。正可谓百万大军乘桴于海,移植到异国他乡。在广袤的北美大地,他们带着自己纷繁各异的自身经历,沧桑深厚的文化印痕,扑入一个全新的国度,其中的苦乐悲欢纷纭复杂、跌宕起伏。因为时代的变化,他们比诸上一代作家,在汹涌而来的西方文化面前,显得更敏感更热情,同时又不失自我,更富思辨精神。他们减却了漫长的痛哭蜕变过程,增进了先天的适应力与平行感。他们浓缩了两种文化的隔膜期与对抗期,在东方文明的坚守中潇洒地融入西方文明的健康因子。他们中很快就涌现一批有实力、有创建的作家和写作人。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闻到了东西融合的气息,也观览到新一代“地球人”的视野与胸怀。
在王亚丽的北美华文文学研究中,她特别注意历史的纵向线索以及横向的基本脉络。她除了系统地研究了北美“草根族”文学的奠基,以及台湾版的“留学生文学”,大陆版“新移民文学”,还看到了来自近、现代文学史上海外作家的先声。近代可追溯到黄遵宪、容闳、梁启超等,而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则大多数都具有海外经历的情结。如当年留学欧洲的作家:徐志摩、老舍、巴金、林徽音、苏雪林、凌叔华、陈西滢、戴望舒、许地山、钱钟书等,他们不仅在海外有精彩的创作,而且从欧洲带回了写实主义、浪漫主义和人道主义等思潮流派。当年留美的作家则有:胡适、林语堂、梁实秋、冰心、曹禺、闻一多等。胡适从西方拿来的新文化火种,正感应着“五四”时代“民主”与“科学”的呼唤,他的哲学和文学思想整整影响了一个世纪。另外构成现代文学的一部分重要作家就是当年的留日学生,他们是鲁迅、郭沫若、周作人、郁达夫等,海外生涯及创作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已为历史所公认。
我的思绪又回到2012年的春天,我和亚丽坐在古城西安环城南路上的一间茶馆里,竹门竹椅,茶水最后喝到没有颜色。我既为她欢喜,也直面向她指出不足,比如对北美“草根文学”的研究上有明显资料上的缺乏。还有,关于北美的纪实文学、网络文学、报刊文学、社团文学等领域都还关注得不够等。但我相信,她的学术架构已经建立,这些都是有待加上去的砖瓦,未来都可继续“穿越”和“跨越”。
惊回首,看百年耕耘,百年沧桑,百年孤独,百年收获!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长河对外是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战”、“交融”中递进式成长,对内则是继承了“五四”新文化所开创的面向世界的精神源流。它的可贵,首在解放了心灵,卸下了传统意识形态的重负,因而能坦然地面对外部世界,并冷静地回首历史。海外华文作家,不仅仅是要告别“乡愁文学”的门槛,还有对“个体生存方式”的深入探求。新的历史造就了新的一代“乘桴于海”的中国人,就必然造就新一代的移民文学。
当今世界,东西方的文化磨合与融合已成为二十一世纪的主旋律。综观全球,正是因为移民浪潮的归去来兮,一个民族才得以迅速地吐故纳新,不断强大。我们有理由相信:海外华文文学,将写下更加绚丽的篇章,也有理由期待王亚丽的北美华文学研究再结硕果。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