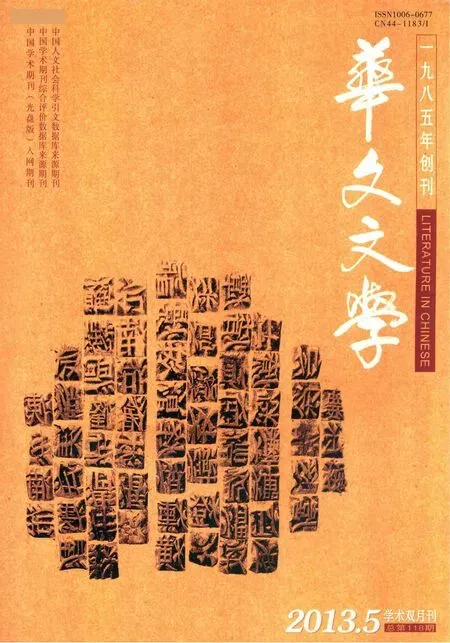欧阳昱《关键词中国》序
杨 邪
整整三年前,我便读到了欧阳昱的《关键词中国》的开头部分,甚是欢喜;之后过去两月,接着读到第二、第三部分,三者相加,约六万字。他在邮件中说:“不知道今后是否有可能再续?”可当时我便想,看架势,再续已是必然。事隔两年,果不其然,他已经把《关键词中国》续写成一部洋洋三十三万言的大书了。
如今,这部三十三万言的《关键词中国》即将出版发行,它被编排成PDF格式的电子文档,在我的电脑桌面摆放近一个月了。此文档的赫然摆放,缘于欧阳昱的嘱托——他嘱我为序,而我一时激动加上一时兴起,慨然允诺。
然而我迟迟没有落笔。每每夜阑人静,当我把这长达三百多页的文档一页页细读下来,不由得懊悔再三——如此庞杂又奇崛、广博又精深的一部大书,我竟敢再在它脑袋上扣一顶灰不溜秋、不尴不尬的大盖帽?
每回懊悔过后,却又忍不住要继续细品《关键词中国》,因为我觉得又有大不妥——既然不知天高地厚答应了下来,那便应该勉力兑现自己的承诺捉笔为序,宁可尴尬,宁可犯大错,也不可失小节,我得先做个守信之士!
好了,此刻我读完了《关键词中国》。不是一遍,而是两遍,其中诸多篇什,是读了三遍四遍。
透过这些关键词,我看见了什么?
正如在澳洲长期老死不相往来地居住会导致精神病,在中国,仅仅一件事情,会让人的心都长瘤子。机场大巴满座,人人都把旅行包抱在怀里或脚边或过道上,而本来应该是放包的头顶存包处却亮铮铮地固定了不可动摇的三(又是那个老子的一生二二生三的三)根钢栏杆。决没有可能把任何行李放进去。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些亮铮铮的钢栏杆。从尾部看着车头的车内电视。我无法理解地去理解并习惯中国的这一现代化的钢瘤。
——《无处藏包》
站在诗歌的角度,我认为,透过这些关键词,我看见了诗歌。欧阳昱首先是一位诗人,并且是一位极其高产的诗人,写作诗歌差不多成了他的生活方式,似乎无论何时何地,任何一种体位(或坐或躺或站,或在空中飞行)他都能不断地写诗。这些关键词,便是他源源不断的不分行的诗歌,至少是诗歌的“原浆”,我能从中感知到诗意的律动与膨胀。
在手绢几乎就要淘汰出局的时代,写手绢差不多也是同样落后的事。记得有一年在中国和朋友同桌吃饭,擤了一下鼻子,掏出手绢来揩,不料被朋友注意到了,说:哎,你怎么还在用手绢啊!我们都有十几年没用手绢了!是的,我几条手绢,不断洗,不断揩,用了几十年,始终也没有养成用纸巾的习惯,总觉得那东西太不方便,也太污染,而且一旦忘记带,就很难堪,也很难看。实际上就发生过这种事。
说起手绢,难以不让人想起中西差别。西方人写的小说中,经常可以看到关于中国人脏的描写,比如在大庭广众掏鼻子而旁若无人。殊不知,西方人就擤鼻子这一条来说,也是脏得不行。掏出一条看上去就不很白的大手帕,蒙住包括鼻子在内的半张脸,仿佛爆炸一般地往里一阵狂轰滥炸,发出几乎震耳欲聋的声音,同样旁若无人,同样满不在乎,把擤出来的秽物七包八裹,团成一团,就往兜里一塞,该上课照样上课,该发言照样发言。如果一次,尚可原谅。碰到那种乐此不疲者,就让观者和听者难以忍受了。只要想一想把曾经擤出的秽物重新贴上鼻尖面庞的感受就够了!
不过,没想到在澳洲住久了,要丢弃手绢,还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手绢》
站在小说的角度,我认为,透过这些关键词,我看见了细节乃至故事。欧阳昱同时是一位小说家,这些关键词,便是一个个丰盈而精确的细节,有时候,一个细节便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或者起码是背后隐藏着一个完整的故事。这些关键词,让我想起那部著名的《契诃夫手记》,作为小说家的契诃夫在生活中记录下来的一部“文学创作备忘录”。
China这个字还很有说头。从前翻译叫“支那”,有贬义,小写则指瓷器。这是常识。近有一个画家,根据China的发音,做了一个“拆哪”的系列,因为China本身就意味着“拆哪”,一天到晚在热火朝天地拆这拆那,天翻地覆慷而慨地拆。
英国人中,用国家当姓的不少,墨尔本Meanjin杂志的前主编Ian Britain,姓就是“不列颠”。姓“英格兰”的也相当之多。至于说到名,就像中国有人名叫“中国”,如著名小提琴家盛中国,英国人也有叫China的。据今天墨尔本The Age报报道,有一位英国作家名叫China Mieville,刚刚出了一本新书。此人属70后,学士、硕士、博士一古脑儿拿到,专写幻想小说,曾经放言,要把各种门类的长篇小说样式统统写书发表。令我感兴趣的是,他为何要起一个China的名字。因为无法查证,只能推测。大约他的爱好学问对中国的崇拜学识不无关系。而且,此人还信奉马克思主义。这又跟中国拉上了一层关系。只是如何把他的姓名翻译成中文而不失掉China,这可能是一个小难题。若音译成赤那·梅尔维尔,这个“赤那”一像“吃哪”,二像“赤佬”,都不好听。“支那”肯定不行。“拆哪”更不可以。如果请我给他翻译,倒不如干脆汉化,像盛中国那样弄成“梅中国”,只是“梅”谐音“没”,中国“没”了。不太好玩,不玩了。
——《China》
欧阳昱还是一位翻译家。站在语言的角度,我认为,透过这些关键词,我看见了抽象的文字符号如何演变成形象的语言洪流。《关键词中国》,在语言上无疑是活色生香、妙趣横生的。此奇异景象,首先得益于作者在中英文字、中西文化上的左右逢源与纵横捭阖。然而,这只是表象。事实上,这种如鱼得水,来自作者三十年来脚踏两只船,自由进出中英文字、中西文化之后对两者的深切体悟与见微知著。此外,作者仿佛每时每刻都带着一肚子的幽默,幽他者,也幽自己一默,并且往往是不着痕迹的,这显然又给自己的语言镀上了一层非凡的光彩。
关于语言,有一点,我必须着重指出——精雕细琢,似乎绝对应该是一位翻译家的操守与美德,也自然应该是一位作家的操守与美德,但是,欧阳昱完全冲破了这种几乎为全行业所遵守的“行业准则”。请注意我在上文中用来描述的“洪流”一词。没错,“洪流”一词用来描述“语言”,再也没有比它更带劲的词语了!洪流是泥沙俱下的,它欢腾、咆哮,不容他物的阻碍,只有它来开辟道路,不许他者对它试图驯服、规范。读《关键词中国》,我随处可以体会到作者对语言的娇惯与放纵,而恰恰是这种态度,让语言变得粗粝、富有质感,无比的元气淋漓。所谓“脚往哪里去,我便往哪里去”,随心所欲,这是一种大境界,这种大境界,是对“精雕细琢”这种操守与美德或者说“行业准则”的蔑视、嘲弄与公然挑战。这种挑战,不是对抗,而是有力的反拨——我认为,这正是作者提供给大家的一种美学原则和深度示范。
世界上什么字最狠?“不”字。我以前写过“说不”没有“不说”厉害。看了某人的书,如果什么都不说,那要比什么都说厉害得多。我之所以说“不”字厉害,是因为想到三个人。一个是奥地利作家伯恩哈特。据百度百科,“在他1989年去世前立下的遗嘱中特别强调,他所有发表的作品在他死后著作权限规定的时间内,禁止在奥地利以任何形式发表。”这种以死亡为代价的“不”,比任何个人和国家都厉害。至少说明:国家甭想超越个人。第二个人是萨特。据百度百科,“1964年,瑞典文学院决定授予萨特诺贝尔文学奖金,被萨特谢绝,理由是他不接受一切官方给予的荣誉。”这一点至少说明:诺贝尔奖别想超越个人。第三个是马克·吐温。昨天来自美国一家出版社的电子邮件消息称,他的自传将于自禁一百年后,即他去世一百周年的2010年11月开禁出版。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是作家朝出版商脸上的一记耳光。总以为出版社最狠,不出版你的书,却没料到,作家最狠的一招就是:你不出,我还不想给你出呢!
“不”这个字是一个“一”字,横在一个“个”字上。如果把“个”看成个人,则那个“一”就像他拿着的盾牌。如果把“不”字侧过来,那个“个”字就像一把飞镖,扎进前面的木板,扎得木屑从两边飞溅。“不”,听起来很像放屁声,那是往往看似最柔弱、最不堪一击的作家对国家机器(如奥地利)、授奖机器(如诺贝尔委员会)、出版机器(如美国的出版社)放出的响亮之屁。不,很好!
其实,“不”最厉害的就是那个横亘在一切之上的那个“一”,说一不二的“一”。你用什么东西都穿不透它,哪怕以国家的力量都不行。
——《不》
欧阳昱也是一位批评家。作为《关键词中国》的作者,这一重身份至关重要。我私下以为,一位理想的批评家,他的批评对象,不会仅仅是文学,更不会仅仅是某一文体,他更应该着眼于文化、社会、世界、未来,只有这样,具备大视域,他才能站得高,高屋建瓴地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而欧阳昱正是这样的一位批评家,凭借他渊博的学识,每天神驰万里,正应了陆机《文赋》所谓“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另外,他去国二十多载,站立在广袤的澳洲大地远眺疮痍满目之故国,这一个姿势是极富意味的——作为一部批评之书的《关键词中国》,于某种意义上而言,亦即作者的一次漫长的不愿怀乡的怀乡。此处所谓“不愿怀乡的怀乡”,只是我的一个猜测——如此越来越沦落不堪的中国,作者总算与之脱离干系了,月明之处即故乡也罢,心安之处即故乡也罢,反正是,懒得怀乡了,但潜意识里,“中国”这个烙印岂是可以轻易抹去的?于是乎,懒得怀乡,不愿怀乡,也得情不自禁怀乡了!而怀乡之病,不正是一个人心灵幽深处最柔软又最尖锐之痛?
这儿得提一下这部书的文体了。《关键词中国》,它是一位诗人、小说家、翻译家、批评家所做的片段式的笔记,原本,称之为“笔记”是最稳妥的做法了,那么何以欧阳昱要自己创造一个词——“笔记非小说”——来冠名呢?我想,恐怕是他特别不敢苟同“笔记”此一文体之模棱两可吧!也许他由随笔记录之“笔记”联想到中国古代盛行之“笔记”,而对后者之“笔记”里的“小说笔法”持保留意见,或至少在《关键词中国》里不愿使用“小说笔法”也不愿读者误以为他使用了“小说笔法”吧!
行文至此,我还有喋喋不休下去的必要吗?
且慢,容我再饶舌一回——
窃以为,此番《关键词中国》出版发行的只是“繁体中文版”,看似有大遗憾存焉,然形式上,却不能不说堪称完美——非以缺憾为完美,而实是,汉字被简化净身达半个多世纪之久以后,面对一个个形迹可疑的干瘪符号,我辈时常萌生匪夷所思的恍惚,以为自己已然痴呆甚或目不识丁,可一旦转而目睹被称呼为“正体”之“繁体中文”,一个个符号遂变得栩栩如生,丰满、灵动、蓬勃、飞扬起来了。试想,案头备有一册“繁体中文版”之《关键词中国》,厚厚、沉甸甸一大部,轻轻掀开来,即是三十三万个鲜活的携带有原始生命气息的汉字在蠢蠢欲动,不亦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