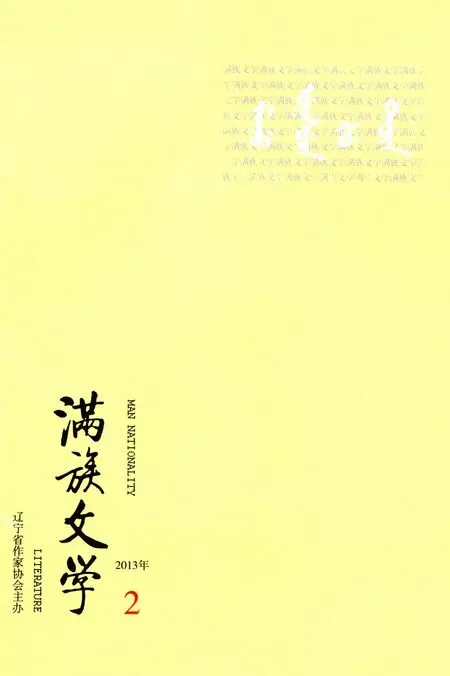右 手
〔满族〕于秋彬
六岁那年,记住了德子,他住在我家隔壁。
德子的腿有残疾,走路不灵便。德子十几岁时失去父母,被生产队定为“五保户”。德子家的院子与我家的院子隔一堵墙,但沿着德子家屋檐下开出的小道,可以走到我家屋檐下。中间竖着一道木栅栏门。
那年,德子四十多岁。四十多岁的德子显得有点苍老。六岁那年,我还不明白苍老是什么意思,就觉得德子有抬头纹,很深,像刀刻上去的。德子的脸黑乎乎的,像从没洗过。德子有浓密的硬硬的粗胡子茬,在下巴上一簇簇地立着。德子的眼神很亮,眼窝很深,鼻子高高地挺着。仔细端量德子的五官,还算耐看,可惜那张脸显得很埋汰,遮蔽了五官的周正。
平时,德子喜欢穿黑色的对襟衣服,盘的麻花黑翻扣,上衣的颜色已洗得发了白,肩膀那块儿贴了两块补丁,针脚细腻。裤子也是黑色的,从腰到裤裆,大开口的“前拉门”。他的裤腰很肥,裤腰中缝经常跑偏,喜欢系条红布腰带。
我妈说,德子这套衣服是他妈在世时给他做的,转眼他妈去世多年,德子也早学会了照顾自己。那些小针脚是德子自己缝的,连平时做饭、洗衣、收拾家,德子都在行。我妈一直想给德子找个媳妇,可每次媒人领着人家姑娘来看完后,见德子那双腿,嘴巴一撇,扭头就走。那时,兴许是穷怕了,有一姑娘的妈看上了德子,跟自己的姑娘说,他长得埋汰,可以倒饬倒饬嘛,他腿脚不好,也不影响生儿育女,还有他家那三间房,好好收拾收拾,住进去暖暖乎乎的,多少人家半辈子都盖不上三间房。德子家的三间房,顶盖上是稻草,快近屋檐那块儿,镶着五排红瓦,红瓦是生产队为德子换上去的,上面的稻草因多年的风吹雨淋,变得黑乎乎的,像大鸟的巢。不过,三间房往那一立,在那个时代,还是很不错的。德子家的院儿,沿房门到正街,有五十来米,宽有二十来米,大大一个院落,可以种植很多蔬菜、瓜果。德子家的院落常年飘着果香、菜香、苞米香,芬芳扑鼻。这么诱人的条件,上哪找去啊!可任凭姑娘妈、媒人说破了嘴,姑娘还是摇头。转眼,四十好几的德子还打着光棍。
每天,德子都会来我家坐坐,每回来,都拄着拐,德子的腿到底是怎么残疾的我不知道,好像打小生下来就这样。他的拐是用后山上最常见的柞木棵子做的,不太直溜,倒很结实。他来我家,从不上炕,也不坐炕沿,就拄着拐倚在我家里屋门旁边的板柜前,斜趄着身子,和我妈唠嗑。唠到兴奋时,经常哈哈大笑。他们在唠嗑时,我和妹妹偶尔会在德子腿跟前窜来窜去。
德子姓连,他妈是我们老于家的姑娘,但属于远房亲属,他管我妈叫舅妈,我们管德子叫大哥,那时我也不知道辈分怎么论,就知道一口一口地叫大哥。
四十多岁的德子大哥还是很关照我们姐妹的。小妹特别喜欢去德子家,有时去了,随便就掀德子家的锅盖,看看锅里是否烀着地瓜、土豆、芋头啥的,看见锅里有吃的,抓起就吃,从不打招呼。有时,小妹还去德子家的院子里摘梨,德子家的院子好几棵梨树,有苹果梨、尖把酸、黄秋皮和酸梨。每年梨熟时节,德子会把采下来的梨子分我家一半,剩下的也基本上被我和小妹在去他家玩时“呛”进肚皮里了。我和小妹对德子像对自家的哥那样心不设防。夏天,德子家的菜园子支起了芸豆架,苞米长高了,果树遮天蔽日,特别适合我们藏猫猫,我们藏猫猫拱来拱去,德子并不干预,而且十分乐意地看我们东躲西藏地胡闹。藏猫猫时,我们常从我家院墙翻过跳到德子家的院子,或者再从德子家的院墙翻过跳回我家的院里。我家靠近德子家院墙中间那块地界有口洋井,洋井旁边砌着石台阶,石台阶的高度要高于菜园子的高度,从石台阶往德子家院里跳,很方便,因为那高度不高不矮,恰好够我们的个头儿。在跳院墙时,我们先是攀上墙头,蹲在院墙上,两条手臂前后摆动,撅着小屁股,“嘭”,再跳下去!最初跳院墙玩藏猫猫游戏时,我们谁也没注意德子在做什么,后来我发现,每次跳院墙时,德子都喜欢坐在对面五、六米远的一块石板上。从那仰视,他正好可以看到我们往下跳时,花裙子飞舞起来露出的小裤头,那时我妈还未给小妹套上裤头。每次德子在看时,眼神间总有种说不清楚的复杂的色彩,他的右手还会伸进裤裆……
有一次,在跳院墙时,我脚没落稳摔倒在菜园子里,裙子掀了起来,碎花的小裤头露了出来,德子扔下拐杖飞快地扑到我身边,左手“噌”地一下抓起我,同时闲着的右手在我的下身胡乱地摸了一把,又在我的小屁股上狠狠地拧了一下,又疼又吓的我“哇”地一声哭了。德子慌忙抽出右手,连哄带骗地摘来几个梨给我,这事似乎就算过去了。但,从那以后,我便不再跳院墙去德子家院里藏猫猫了。小妹看我不去藏猫猫,后来也不去了。有时大人喊我去洋井旁抽水,就连走那块石台阶,我都心存芥蒂。
我妈并不知道这些,我也不想和我妈说。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不懂德子到底想做什么,不懂他眼神里写了些什么。但我惧怕德子的行为,讨厌德子的右手。
小妹还照常不误地去德子家掀锅盖,扒锅底灰,她总是能从那些地方找到好吃的。德子家的锅里有烀土豆,锅底有烧土豆,两样美味在那个年代还是很眼馋人的。可我不爱去德子家。即使我妈喊我给德子送过去点啥,我也都是在越过那道木栅栏门后,快速地走近德子家的锅台,放下盘碗便跑。对德子和德子的家,我有种惧怕。
德子还是经常来我家,来我家时,依旧站在老地方,一个姿势地趄着,聊到兴奋时,仍喜欢大笑。他的右手扶着我家板柜,我甚至开始讨厌他右手扶过的位置。他走后,我会拿抹布蘸上水使劲地擦那块地方。那年的除夕到正月十五,德子在我家吃饭,吃完饭再回到自家睡觉。我妈对德子照顾得极为周到。德子也乐意让我妈照顾。有时我觉得德子可怜,有时又觉得可恨。这两种情愫始终在我童年的心灵中交织、纠缠。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我这种心理。
九岁那年,我去了中心小学。中心小学与我们村子间有条一公里的山路,那条山路小路蜿蜒,荆棘丛生,荆棘长势旺时越过横道,上、下学的孩子有时在路上疯跑稍不注意就被扎着了。为此,每年村里都组织社员砍掉路边的刺槐,以防其“横行霸道”。偶尔也有自发去的,砍完后,再把它捆回家当柴烧。越过那片山路,是座水库。冰冻后,水库的水形成白花花的一片冰湖。冬季,和小伙伴们最喜欢做的游戏是去光溜溜的冰面上打哧溜滑,上、下学的我们更不会放过溜冰的机会。偶尔我妈会嘱咐:走石桥上下学,别走水库,危险!我们哪管这些!
那年冬天的一个黄昏,放学后,我和同学们背着书包撒着欢儿地跑进了那片白花花的冰湖打哧溜滑。那刻,并不知道危险在一点点靠近。当时打哧溜滑的还有二三年级的几个孩子。我在岸上拾到块不知从什么上掉下来的铁片,当作宝贝似地放在脚底板上,踩着铁片就滑在了最前头。大约在距离岸边二十多米远的位置,我回头冲他们几个喊道:快点滑呀!追上我啊!就在大家嘻嘻哈哈地往前追撵我时,忽然,我的脚下“嘎……嘎嘎”几声响,一惊,低头一看,不好,看似十分坚固的冰面突然裂开了一道口子,并迅速扩大、延长,“嘎……嘎嘎嘎”的脆响不断响起,水库上的冰,像被重击的钢化玻璃一样,裂痕马上向四面八方扩散开去,越来越多,而且在朝着那几个同学的方向蔓延……我还没反应过来该怎么办呢,就脚下一空,一条腿掉进裂缝里。在我忙着抽脚的工夫,他们也畏惧、惊慌起来。我的脚并没抽上来,而这时的冰面又连续“嘎嘎”地响起来。其他几位同学眼见我掉进裂缝,急得大喊:“坚持住,我们想办法救你!”就在大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时,德子拎着拐不知从哪里一瘸一拐地跑过来了,他的“跑”是跟头把式的。他老远地就喊:“三儿,别动!你先把背上的书包扔出去,趴在那!”不知怎地,我照着他的话做了。他又“命令”其他几个孩子马上离开这片冰面,然后往前走几步,趴在冰面上,伸出握着拐杖的右手,冲我喊:“来,把双手张开,一点点用胳膊肘往前使劲儿,轻轻地往上拽那条腿,轻点!”他在安慰我。我在冰水里的一条腿已经麻了,那条没落进冰水的腿还能正常用力。我的双肘攀住冰面,身体轻轻地往上窜,努力地让另一条腿浮出水面,就这样,一点点地往前爬。那刻,仿佛时间都静止了。趴在冰面上的德子也在往前慢慢地靠近我,终于,我的左手够到了他的拐杖。“来,慢慢地,握紧它,我拖住你,别怕……”德子边对我说着话,边向身后的岸边退去。我紧紧地握住他那支不太直溜的拐杖,爬回了岸边。危险过去了。
那夜,德子成为我家的功臣。
我妈请他上炕头坐,他不;我妈请他坐炕沿,他也不;他还是站在板柜前,拄着那支拐,看着躺在炕头上捂着棉被吓得发抖的我,眼神里充满温和与关切。我妈说,“今天多亏了德子,要不,三儿的小命就交代了。”德子说,“没事了就好,当时我正在离水库不远的路上砍刺槐呢,本寻思赶在傍黑前把那些刺槐砍完背回家,晚上好架火,这两天天气阴,稻草不好烧,炕头不热,谁知,竟出这档子事,还有那几个孩子,当时站在那,也挺危险。”听完德子的话,躺在热炕头上烙着被冻麻的腿,我的心里有种说不清的滋味。望望他扶在板柜上的右手,想想他趴在冰面上拖我时的情景,心里酸酸的。
九岁时的我,已经懂得了愤怒、怨恨、感动以及感恩这样的字眼。对德子的恐惧,从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那刻起,似乎可以放下了。而对德子右手的厌恶,也从他匍在冰面上向我伸出右手的那刻起,开始消失。
不过,我始终没再单独靠近德子,即使走近,身边也有我妈、我妹。
德子病危时找邻居捎来话,想见见我们一家。早已搬迁进城的我们,雇车去了乡下。躺在竹席子炕上骨瘦如柴的德子努力地伸出右手,拉住我妈的手,眼角流出浑浊的老泪。我望望德子,有同情,有怜悯,更有感激和难过。我没有忘记当年他救过我一命。我从妈的手里拉过德子的右手,瞅瞅他塞满灰尘的手指甲,从背包里掏出指甲刀,“咔、咔”地帮他剪起来。他的手粗糙、僵硬,像柏树皮,摸起来扎手,让我心痛。我轻轻地握着他的手掌,剪得很用心、很细致,剪刀落下后发出的声音清脆、悦耳。他安静地躺在那里,眼神定定地望着天棚,久久地没有说话。
在我们去看德子的第二天傍晚,夕阳刚落下西山的时刻,一直单身的德子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