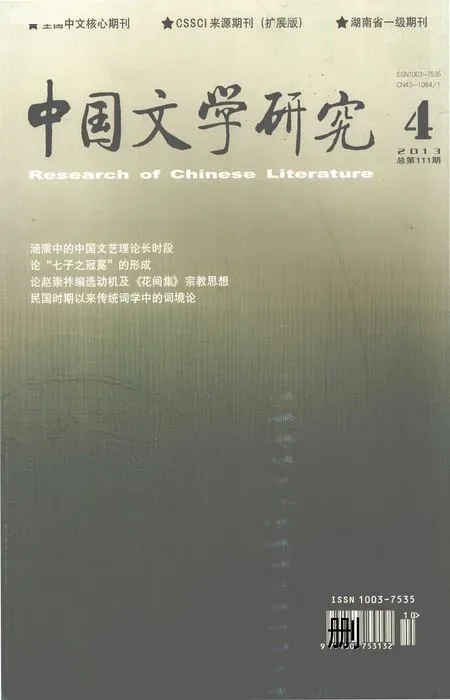错位下的日本想象:甲午前晚清士人的日本游记研究
杨汤琛
(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40;暨南大学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研究中心 广东 广州 510632)
一
较之欧美诸国,日本无疑是一个让大清帝国情绪复杂的国家。欧美西方诸国,在晚清士人的想象视域里,终究是一个陌生体,它或被诋毁或作为普遍性的价值被向往,无论如何,西方的过去与晚清的现在是隔阂的,缺乏历史的纠葛与回顾;但日本却不一样,自古以来,日本长期与中国历史相纠缠,处于中华王朝居高临下的想象视野内,作为正史的《汉书》开始了对日本的正式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稍后的《后汉书·东夷·倭传》则云:“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远在汉代,日本在中国史家的视野中是前来朝拜的朝贡者,日本王权的存在需要汉王朝的册封与印绶的赋予,古代这类有关日本的现实抑或想象性认知反复强调的是中国对于日本的权力与控制;至隋唐盛期,日本将中国视为政治、文化上的朝圣地,大量的“遣唐使”远渡重洋来中国求学,这种交往历史不仅让中国津津乐道,而且也被日本历史所承认,为此,关于日本,中国一直有着上述的顽强记忆,即中国与日本存在着文化大国与附属国、施者与受者的不对等关系,日本被限定在这类固化的静态的认知视野内,从而成为一种具有共时的本质性的事物。
拘囿于上述被固化的日本印象,晚清士人极少去关注真实的日本现状,黄遵宪在《日本国志叙》(1887)中曾谈到晚清士人对日本的妄识:
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邹衍之谈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诞不足论议也者,可不谓狭隘欤?
直至鸦片战争爆发前夕,中国对日本的印象仍然是渺茫虚浮,“近世作者如松龛徐氏、默深魏氏,于西洋绝远之国尚能志其崖略,独于日本考证阙如。”开风气之先的魏源与徐继畲在他们有关外国介绍的著作中对日本的认识也非常模糊,甚至甲午战争前,朝廷不少士大夫还妄自认为日本国力甚小,“倭不度德量力,敢与上国抗衡,实以螳臂挡车,以中国临之,直如摧枯拉朽。”或许,对于日本的这种不屑的认识来自于认知模式中的惯性力量,它以了解一切、掌控一切的顽固自信维持着它自以为是的中日格局。
但这类处于静态认知系统内的中日模式,却随着时代发展的冲击,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变迁,首先是战争的契机让千年的中日交往模式乍然颠倒,鸦片战争后,中国以屈辱的方式走向世界,与此同时,随着明治维新一系列的西化变革,日本惟中土文明为马首是瞻的信仰如堤溃散,晚清逐渐丧失了凝滞时代对于日本的政治与文化的双重控制,历时性被必然引入这一静态认知系统中,日本学者实藤惠秀从日本的角度描述了这一变化:“千多年来,日本在思想、文化、制度,以及衣、食、住等日常生活上,都深受中国影响。日本人因而对中国敬仰有加……”“踏入明治时代(1868-1912),日本急剧地吸取西洋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关心渐趋淡漠,但对中国尚未采取轻视态度。不过,从明治末年起,日本步西洋列强后尘,开始在亚洲大陆蠢蠢欲动。在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中,日本赌以国运,诚惶诚恐地悉力以赴,结果大获全胜。从此,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为之一变,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或文化上都轻视中国,并侮辱中国人为清国奴(chankoro)”世事变迁,不仅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从微妙到激烈的转变,中国对日本的态度也发生了应激性反应。
现实境遇是,甲午战争之前的日本正在西化的途上蒸蒸日上,并日益成为清帝国一个重要的威胁,由此,曾被视为稳定的日本逐渐变得不可捉摸,不那么稳定了,甚至逐渐转化为一个巨大的威胁与强悍的他者,这类微妙变动最先从日本游记中凸显,通过阅读甲午前这批晚清士人的日本纪游,我们不难发现,其纪游文字清晰地展示了这类现实叙事与固有的想象视野之间的冲突与覆盖,暗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比如世界日趋变化的现实、成长与衰落的对比、中日分离的细节等,而成为一个关于历史追忆与现实接纳之间发生断裂的时代叙事。
二
如果说出游欧洲的晚清士人,多汲汲于经世致用的社会考察,那么,游日的士人们在日本展现的却是另一种姿态,吟风弄月、诗酒征逐成为游日者的惯常姿态,日人源桂阁曾如此描述何如璋、李筱圃等游日的士大夫们:
皆以诗赋文章,行乐雅会,善养精神,故性不甚急也。……高卧幽栖,诗酒自娱之人,宜交清国人也。
何如璋使日期间曾辑有《袖海楼诗草》一书,卷上专收与栗本锄云、三岛中洲等日本文人的酬唱诗什,足见何氏在日本诗文酬唱之盛。黎庶昌两度使日,据载他曾五次在日本举行登高诗会,日本汉学家三岛毅在《奉送黎公使归清国序》中这样描述此种诗文唱和的盛况“公使鸿胪交际之暇,每逢良辰佳节,必率僚属设宴于东台芝山景胜之地,招集我文人骚士,诗酒应酬,继以谈笑歌舞,宾主相忘,而汝互呼,吐肺肝尽,情好而罢,如此者不下数十次。”这种呈现了晚清士人闲情逸致的文人情调也普遍出现在彼时游日的士大夫身上,典型如文人王韬。
王韬在日本沉溺于风花雪月,期间“文酒谈宴,殆无虚日,山游水嬉,追从如云”,翻阅他所录的《扶桑游记》,不难发现他在日本的关注点多囿于清景美妓,文中屡屡提及的多是携妓而游的风流韵事,艺妓、妓等俨然作为王韬最难忘之景观屡次被他反复描摹,初到日本,他就以工笔的手法细细描摹了日本的艺妓形象:
一年仅十四五龄许,雏发覆额,憨态可掬。顾其装束殊可骇人,唇涂朱,项傅粉,赤者太赤,白者太白,骤见不觉目眩。…………凡客至,必有妓侍饮,名曰艺妓;但能为当筳之奏,不能为房中之曲。”
随后,王韬又多次提及这些既能载歌载舞,又兼宽慰身心的人间尤物,在光绪五年闰三月二十日的日记中,他详细记录了自己在日本招妓荐寝的经过:
始招一妓,年若徐娘,而容如嫫母,因遣之去。继至,则十五六龄小女子也,身材琐弱,灯下视之,洁白无比。余倦已甚,拥之而眠,不觉东方之既白。
上述关于日本歌妓的描述与《漫游随录》中多以仰慕之态来描述才貌兼备、知书达理的西方女子迥然不同,王韬在《漫游随录》中所悉心关注的是美丽多才的西方女子,“皆花妍其貌而玉洁其心,秉德怀贞,知书守礼,其谨严自好,固又毫不可以犯干也。”在她们曼妙的身影背后是整个冠冕堂皇、技术发达、文明有序的西方社会,她们相互辉映、共同缔造了王韬关于西方乌托邦的美好想象,激起的是他对西方女子的尊重之意与爱慕之情;同样是在异地、遇见异地女子,王韬在日本的关注点与书写方式却截然有别,王韬在日本更为关注的是这些具有消费性与娱乐性的风尘女子,在引录的前段描述中,王韬俨然是从外貌、装扮、举止等方方面面对艺妓进行把玩式的细细赏玩,这种由上至下目光的抚摸显然与尊重、平等无关,不仅直接讥讽艺妓的妆容“赤者太赤,白者太白”,而且轻薄地感叹她们“不能为房中之曲”,语言佻达、轻浮,充分凸显了一个临幸者的高高在上;同样,津津谈及招妓经历,王韬无不兴致盎然,始终抱有优越姿态,他先嫌弃第一个日本女子太丑状如嫫母,对第二个日本女子似乎也不甚满意,说她“身材琐弱”,只好将就拥之而眠,王韬日本游记中的肆意与放浪在漫游欧美的书写中是断乎难寻的,他在日本的这种放荡、狭玩的情态与他在英、法两地所展现的谦谦儒者形象也颇不同,这不能不牵扯到因地域之别而怀抱的心态之别,在彼时王韬及其普遍士大夫的意识中,日本不过是一个文化、礼仪处处附属于中华的“蕞尔小国”,是一个大清帝国阴影下不值得正视的“小日本”,在被视为小国与文明附属地的日本,来自文明大国的王韬在观看日本女子时自然会有着东方情调式的把玩意味,当面对一个自以为比自身弱势的群体时,王韬的精神状态彻底放松下来,作为旧文人趣味的狭邪之态也在两者的遭遇下没有顾忌地释放出来。
这种高高在上、自以为日本文明之宗的大国心态在甲午之前可谓是一种普遍的心理模式,以致我们在甲午前的日本游记中发现,除了如王韬般以精英的姿态把玩日本的美景与女人之外,在日本刻意地寻旧、访古、重温日本的中国痕迹、回顾中华昔日的辉煌等都成为游日者强调大国意识的另一脉重要叙事。涉足日本,晚清士人似乎总难以抑制回顾昔日辉煌的冲动,以骄矜的缅怀姿态来追溯中日曾经的文化渊源,成为不少游者的重要叙说:
日本自神武创业,……汉武时通使,自称大夫。降至魏晋,音问不绝。通百济,受《论语》,圣教始被东土。隋唐以来,屡遣人受学中国。(何如璋《使东述略》)
云龙游历之国六,假道之国五,而以日本始。或曰:此岛国耳!讵知地背以相反而鉴,日本正以相因而观。以彼学唐而后至于今,已一千二百年有奇,事事以中国为宗。(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馀纪》)
何如璋、傅云龙们在日本游记中的这番追溯显然是为了孜孜强调中土文明笼罩日本的辉煌历史,他们通过追溯悠远的历史来定格中日之间的普遍格局,二千余载的交往模式被凝固成一种终极类型,那就是在文化上日本始终受教于中国,并处处以中国为宗。
这类源于历史认知的大国思维使得游日文人多将目光聚焦于能够激起文化溯源与优越感的日本景观,凡能印证中日文化渊源的景色器物经常被印诸笔端,诸如唐馆、孔子庙、徐福墓、仿中式的盆景、园林、崇汉学的日本遗老等均成为游记中反复描述与感慨的对象。何如璋游日本孔子庙,自豪感油然而生:“夫子未尝浮海,而殊方异俗,千载下闻风兴起,教泽之所被,何其远哉!”又随后在《使东杂咏》中赋诗以记:
浮海乘桴寄慨深,千秋谁识圣人心。
殊方今日入祠庙,洙泗环门杏满林。
孔子,作为中华儒家文明的缔造者与代言人,其学说不仅流传中国几千年,而且泽被遥远的日本国,并被日本以庙宇供奉的高规格方式加以尊崇,这让何如璋在当时“靡然以泰西为式”的日本国寻找到了印证中华文明强大能量的有力证据。源于同样的文化自信,出使大臣傅云龙在游历日本期间对日本正在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革事物大多寥寥数语一带而过,显然兴趣不大,反而对日本源自中国的古迹与文物津津乐道,甚至长篇考证日本所藏的中国古籍,重新发扬故去文化的余温。
日人作为中华文明朝拜者、倾慕者形象,也在游日记录中频频出现。1854年,国人罗森以舌人的身份随美国柏利舰队抵达日本,在罗森时代,舌人即翻译的身份无异于三教九流,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谋生之道,然而侧身日本,一些崇汉文的日人纷纷前来拜访、索要题扇的热忱不免让他骄矜而自得:
日本人民自从葡萄牙滋事,立法拒之,至今二百余年,未曾得见外方人面,故多酷爱中国文字诗词。予或到公馆,每每多人请予录扇。一月之间,从其所请,不下五百余柄。
李筱圃亦记载其在日期间,日本文人来访络绎不绝,有静冈县人藤沼纫来求教“语极谦恭,亦崇汉学而能文者”,又有“日本九州地肥后人汤地文雄来见,”,“连日来呈诗求教者甚多,俱略为改窜而已。”
诸如此类的有关中华遗迹与古文物的盘桓,以及游日者被部分崇尚汉学的日人所尊崇的情境,它们都着眼于孜孜强调中土文明泽被日本的现实证据,努力构造中华帝国的美好的生活方式,这些印下中国优势文明的古迹有效区分了真实的历史进程与文化遗产,前者是持续变动的,因而是危险而令人尴尬的,流动的历史带来的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现实的挫败与日本的文化出走;而作为文化遗产的后者是过去的、静默的,它铭刻着中华文明的荣耀,记录了日本曾经对中土文明的虔诚与向往,因而它们是安全的、美好的。文化遗迹与遗老遗少的尊奉掩盖了现实境遇下中日关系的变迁,也抹去了中华文化风光不再的真实情境,在这类抚摸古迹、追溯历史渊源的回顾性荣耀中,晚清士人再一次加强了中国是日本文化宗主的历史记忆与惯性认知。
三
然而,对照其时日本的现实境况,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努力书写自我辉煌背后的自我幻觉化的表演。当鸦片战争一役刚打碎中国天朝帝国的迷梦时,彼时还在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日本就出现了“举国沸腾,人心惶惶”的局面,为了避免重蹈清廷覆辙,日本开始奋力摆脱清王朝的阴影,全面学习西方。1868年,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果断结束了封建藩属体制,迅速走上了西方式的发展道路。当清帝国还经历着谋求内部变革的同治中兴时,明治天皇已经在誓文中声称日本将“为帝国统治根基的强盛,拓新知于海外”。以明治维新为契机,日本在狂飙式的现代化进程中,狂热的“西化”与坚决的“去中国化”可谓并驾齐驱,1885年,福泽谕吉于《时事新报》发表了《脱亚论》一文,成为号召“脱亚入欧”的公开檄文,他号召全面西化的合理性,并将中国视为“恶友”:
我日本之国土虽在亚洲之东边,其国民之精神既已脱离亚洲之固陋,转为西洋之文明。……今日之支那、朝鲜对于我国不仅没有丝毫的帮助,而且西方文明人也会因为三国地利相接,或许会等同视之,以支那、朝鲜之评价来衡量我日本。……唯有依照西方人对他们之态度来对待他们,亲恶友者不可避免与之共
恶友名,吾要诚然谢绝亚洲东方之恶友也。中国对于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而言,不仅不再是值得学习的文明古国,反而成为阻扰日本前进的障碍,成为福泽谕吉所号召的亟需摆脱的“恶友”。何如璋、李筱圃、傅云龙以及稍后的黄庆澄等是在日本明治维新后全面变革之际涉足日本的,对于日本这种由谦卑至轻视乃至敌对的变化,他们不能不有所感知。何如璋一踏上日本就发现西洋事物在日本蜂拥而现,“凡制度、器物、语言、文字,靡然以泰西为式”,而“汉唐遗风,间有传者,一旦举而废之。”日本一边对西方亦步亦趋地进行模仿,一边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中华文明,这类情景无疑对何如璋的中土感怀构成了强烈的反诘;李筱圃也敏感到日本维新后的新情境:“日本自维新政出,百事更张,一切效法西洋,改岁历,易冠裳,甚欲废六经而不用。遗老逸民尚多敦古以崇汉学……”俨然,西方文明已经成为日本的普遍性追求,作为中华文明传承的汉学此时只有一些遗老遗少才去理会,日本的启蒙先驱福泽谕吉在其《文明论概略》(1875)中就已经将中国列为“半开化”国家,福泽谕吉的理论当时被主流的日本阶层所拥戴,游记中所载的与晚清士人们吟诗怀旧的日本儒者大多已经成为当时日本变革潮流下的遗留物了。
甲午战争前一年,时人黄庆澄受朝廷派遣到日本游历,发现明治维新浪潮中的日本“学西方有成效”,狂奔于变革途中的日本对于中土文化已经不屑一顾,“查东人最好古,往往有隋唐以前书中土已佚者,彼国犹珍存之。自西学盛行,此风一变,昔所存者,弃若弁髦。”对于仍沉浸于自我中心意识的中国而言,日本这种舍中趋西的文化姿态本身就构成了对中国现状的揭露与嘲讽,现实的日本叙事正处处昭示着日本的今非昔比与日趋强大,日本的“脱亚入欧”之举也处处提醒着中国文化的日趋无力,日本,作为曾经的“小中华”,它正绝尘归西,面对日本这种无可挽回的变迁,甲午前的晚清东游者却鲜有能反躬自省者,大多从大国意识出发,让这份文明优越感转化为一种固执情绪,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日本的明治维新。
的确,日本明治维新以来“脱亚入欧”的维新事业不仅打破了历史惯性,而且乍然中断了晚清士人的自我中心幻觉,一点点消灭着有关中土文明的辉煌回忆,面临这种断裂,何如璋对明治维新充满了讽刺与质疑:
举数百年积弊,次第更而张之,如反手然,又何易也!讵前者果拙,而后者果工耶?抑时事之转移,固自有其会耶?此不可得而知之矣!
何公将明治维新的变革事业视为“如反手者,又何易也!”,充分表达了对它的不信任,而“后者果工耶”的诘问也是在貌似疑问中对明治维新提出趋于否定的质疑。
相对于何如璋的暗讽,李筱圃则立场鲜明地指责明治维新使得日本“国以日贫,聚敛苛急。”:
国王乘此夺其政,……大权一归于国,曰维新之政。今则非但不能拒绝远人,且极力效用西法,国日以贫,聚敛苛急,民复讴思德川氏之深仁厚泽矣。
有效促进了日本现代化转向的明治维新在李筱圃的视域下成了祸国殃民的失败举措,这也是当时不少士大夫对于日本明治维新的一种较有代表性的看法。1874年,陈其元还在《日本近事记》中大力攻击日本仿效西方,使得“人人思乱”,甚至建议清朝廷派兵帮助德川幕府复辟。可见,在彼时中国,晚清士大夫们坚持认为中国传统文明是最高级的文明形态,“晚清大批中国人走进日本社会,尽管中国已经不及日本先进和发达,也已经完全失去中华帝国君临天下的优越性,但中国人没有失去文化上的自信,也相信文化的话语霸权仍然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种文化自信决定了他们在对待日本学习西洋文明的态度上往往有着本能的反感与质疑。日本这种倒戈式的文化选择,无不隐绰地指向中土文明的现实衰败,比照鸦战以来屡次的割地赔款、丧失国颜的挫败,这不能不刺激中国士大夫脆弱的神经,对于倡西学的明治维新,他们用这种不无谴责的语调指摘其弊端,也不失为一帖宽慰自我的缓解剂,隐藏了中土文明风光不再的失落与不安。
从甲午前这批数目不多的日本游记中,我们看到在相同的时间纬度上,当日本奋力向前并急欲摆脱中国文化时,涉足日本的中国士人还犹然抱有“天朝上国”的优越心态,毕竟在漫长的中日文化关系中,中国一直处于文化施予者位置,自然,中国也天然地对日本葆有文化母国的优势心态。当晚清士人以文化大国的姿态俯视日本,他们要么将视点集中于日本在历史蜕变中所遗留下的中土印痕乃至部分的遗老遗少,要么着意于对日本清景、美人、男女同浴等奇风异俗的描绘,而对日本蒸蒸日上的明治维新事业多以贬斥、负面的情绪加以勾勒,以这样的观照视角所构成的日本想象自然遮蔽了真实而深刻的日本现状,晚清游记中的日本由此成为混杂了文化自大、历史缅怀以及虚弱而不平衡等复杂心绪的文化混合物。
〔1〕黄遵宪.日本国志叙〔A〕.日本国志〔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2〕薛福成.日本国志序〔A〕.日本国志〔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3〕蒋廷黻.中国近代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4〕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M〕.北京:三联书店,1983.
〔5〕(日)源桂阁.芝山一笑.后序〔A〕.晚清东游日记丛编.中日诗文交流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6〕王宝平:晚清东游日记汇编.中日诗文交流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7〕中村正直.扶桑游记序〔A〕.扶桑游记〔M〕.长沙:岳麓书社,2008.
〔8〕王韬.扶桑游记〔M〕.长沙:岳麓书社,2008.
〔9〕王韬.漫游随录〔M〕.长沙:岳麓书社,2008.
〔10〕甲午以前日本游记五种〔M〕.长沙:岳麓书社,2008.
〔11〕罗森.日本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5.
〔12〕黄庆澄.东游日记〔M〕.岳麓书社,1985.
〔13〕(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14〕(日)福泽谕吉.福泽谕吉集〔M〕.筑摩书房,1975.
〔15〕张哲俊.东亚比较文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