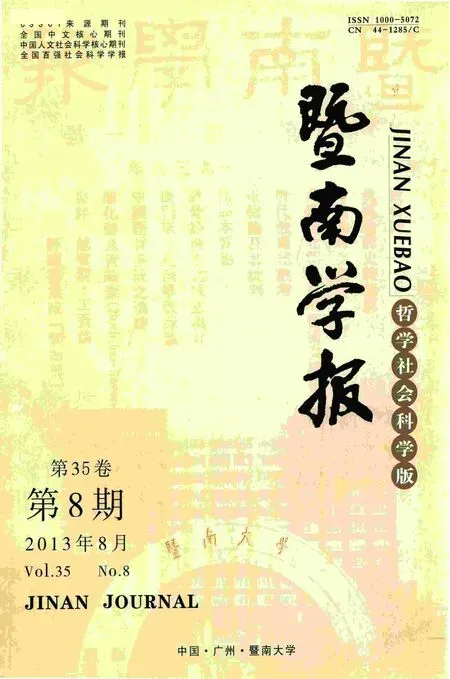论碳排放权交易本土化的法律完善
张华
(西南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院,重庆401120)
一、碳交易迎来后《京都议定书》时代
为缓解全球气候变暖进程,国际社会于1992年5月9日在纽约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第三次缔约方会议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中提出了排污权交易、联合履约和清洁发展三大市场灵活机制。《京都议定书》的三种灵活机制都涉及到不同国家之间的碳排放权交易(以下简称碳交易),它们是实现减缓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重要机制,可以赋予各国在温室气体减排投资费用上的灵活性,从而实现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费用的有效性分配。这些合作机制刺激了国际投资,并为全世界各个国家实现“更清洁”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施手段。
碳交易市场主要有强制市场和自愿市场两大类。强制市场主要是指京都议定书、欧盟排放贸易体系等运用强制性手段促使参与者减排的交易市场;自愿市场主要指分散的场外交易(OTC)和芝加哥交易所的自愿交易。不同的市场适用的碳信用各不相同。1997年《京都议定书》规定了排放配额(AAU)、减排单位(ERU)、核证减排量(CER)和脱碳单位(Removal Unit)四种碳信用,其中“核证减排量”(CER)是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的主要交易单位。自愿市场的交易主要以经核实减排量(VER)、预期减排(PER)为场外交易的主要单位。理论上讲,市场化的碳排放配额交易制度可以调动区域和产业部门的内在积极性,使它们主动地、持续地减少污染物排放。《京都议定书》第一期承诺于2012年底到期。
2011年12月,《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7次缔约方会议会(COP17)暨《京都议定书》第7次缔约方会议(CMP7)“德班气候大会”同意《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在2013年生效。大会要求《议定书》附件一中的缔约方(主要是发达国家)从2013年起执行第二承诺期,并在2012年5月1日前提交各自的量化减排承诺。对此,发达国家态度不一。欧盟在参与第二承诺期的同时要求大会在2015年制定“涵盖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具法律约束力的减排框架”,并于2020年后生效。但是,美国、日本和加拿大等对《京都议定书》本身持消极态度,拒不考虑第二承诺期的减排指标——《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有名无实”。
2012年12月8日,《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8次缔约方大会(COP18)和京都议定书第八次缔约方会议(CMP8)通过“多哈系列协议”(Doha Package)。多哈气候大会上,发达国家自身减排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转让技术的政治意愿不足,倾向于淡化“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其历史责任。因此,“多哈谈判”并未在德班减排目标上有新的提高。这些不仅带来了今后气候问题国际社会合作的巨大障碍,也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节能减排将付出更大的经济代价。
至此,《京都议定书》所创设的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伴随着国际气候谈判的模糊与迟滞,陷入徘徊境地。后《京都议定书》时代,我国碳交易不能过度的依赖国际谈判的进展速度而放缓进程,而应当未雨绸缪,转而发掘碳交易制度的合理性及其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优势,培育本土市场,促进碳交易制度的“本土化”。
二、本土碳交易当下的困境及法律原因
(一)碳交易的发展现状
1.国际市场困难重重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资源国家和碳排放较大的国家。然而,现实情况不容乐观,表现如下:其一,国际市场方面,欧洲多数企业采取停产报价的措施应对欧债危机,欧盟市场投资疲软,直接导致欧盟碳交易市场冷清局面的产生。其二,我国境内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申报激增,但难以获得国际碳市场交易“入场券”。从数量上看,我国政府批准的CDM项目为较多,但仅有约三分之一的项目获得联合国注册,获得核证减排量签发的项目不超过十分之一。其三,在国际市场上,中国既没有定价权,也没有话语权。中国的企业大部分都超标,因此国内许多企业会买国外的配额,继而形成变相的资本输出。
2.本土市场门可罗雀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已经在多个城市进行过大气污染物及其配额的排放权交易的试点,并建立了有关排放权交易的部门规章和地方法规。2008年8月,国家级环境权益交易机构之一的北京环境交易所正式挂牌,随后上海、天津等地相继成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2009年11月,亚洲排放权交易所启动筹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0年底,中国已有近20家碳交易所,但能提供成功运作经验、具备全球资源的交易所却并不多见。2008年长沙建立了环境资源交易所,只有1笔交易;2009年设立的北京环境交易所,2011年才刚刚达成第一笔交易;2010年10月深圳成立排放权交易所,碳交易尚未开锣。碳交易所面临着“昨日热闹开张,今日门庭冷落”的尴尬局面。在本土市场上,国内碳排放交易价格仅仅相当于国际平均价格的一半。尽管如此,目前国内没有一桩真正的碳排放交易,有潜力的碳交易主体可谓是“心忧炭贱愿天寒”,碳交易的本土市场培育绩效不高。
(二)碳交易为何“有价无市”
1.法律理念模糊
在碳交易问题上,有“产业主义”和“环境主义”两种不同的理论支撑。产业主义是把扩大生产规模,实现生活富裕作为社会福利,而“环境主义”则是把谋求生活的舒适快乐与安全作为最大的公众利益,利用政治的力量来达到改善环境的目的。以哈贝马斯和蕾切尔·卡逊为代表的环境主义的根本理念在于公共性。发达国家从1970年以后开始对改善环境加强了行政力度,不仅各国都设立了环境部,对于无主(无所有者)或是无管理状态下的大气、水、土壤、气候等资源,从“公共性”的角度出发,按照国家以及国际惯例的标准强化了对其的管理。碳交易要求建立一种直接对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进行市场交易的市场运作机制,来达到调节二氧化碳排放量利率的目的。然而,即使买卖“排放许可”(emission permit),至多也只能使排放量不超过环境容量许可的范围,不可能真正做到削减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因此,从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出发点来看,碳交易不应该仅仅是单纯的市场行为,这一市场行为同时还应该体现出基于“环境的公共性”的环境行政管理的色彩。因此,环境行政管理的缺位必然影响碳交易市场的正常发展和交易公平。
2.环境法律制度缺位
其一,强制减排和强制交易制度尚未确立。基于“共同但有区别”的国际环境责任承担原则,我国政府提出了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然而,目前既没有规定企业二氧化碳排放上限,也没有法律、政策对企业的排放量加以强制约束。单位或个人通过碳交易完成减排目标更多地是一种自觉行为,一些交易所都只做碳排放自愿交易,国内的碳买家也大多为履行社会责任的单位或个人,不仅强制市场没有建立起来,自愿市场的规模也非常有限。
其二,公共性管理被人为分割,碳交易所“地方化”。2007年以来,我国各地相继成立了多种类型的交易平台,有环保部门授权成立的交易所、环保部门以外的其他机构成立的交易所、当地人民政府批准建立的交易所和原有的产权交易所主导的交易所等。各种类型的碳交易所“你方唱罢我登场”,其优点是促进了各地碳交易的发展和区际碳减排竞争,其弊端是加深了各地区之间交易方式、管理模式、信息交流的不一致性。碳交易的区域合作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管理成本的增加、造成了各地碳交易市场的重复建设。
其三,统一碳交易标准缺位。目前,我国尚无广泛适用于各行业、各地区的碳指标体系,如北京环境交易所制订的“熊猫标准”适用于泛农业领域,天津碳交易所的交易标准适用于建筑领域,其他各地的碳交易所的交易标准和规则也各有不同,客观上造成碳信息的不对称。这种情况,一方面容易由于环境信息的不公开,限制了公众和环保非政府组织参与碳交易;另一方面容易导致企业在参与国际、国内碳交易过程中,因碳减排指标缺乏足够的公信力和透明度的原因受到制约,无法顺利开展交易。
其四,政府干预市场的手段“失灵”。一方面是政府干预不当,碳排放权定价机制不合理情况有待改善。由于受到政府制定的初始排放份额的约束,交易价格受到人为的扭曲;而我国相关部门主要关注的欧盟价格也很难反映出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真实价格。另一方面是政府干预不够。如,由于碳交易意识和碳交易能力培养制度的薄弱,中国企业对CDM项目以及碳市场缺乏充分的认识,CDM项目的注册率较低;由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碳交易程序过于复杂,客观上增加了交易成本;由于市场交易监管力度较弱,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安全、交易的公信度有待提升等。
三、“后京都时代”完善碳交易法律政策的利好基础
(一)碳交易法律体系发育初具雏形
究竟如何运用法律手段管理“大气”这一最大规模的社会共通资本呢?
我国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曾先后制定和修订了《环境保护法》、《森林法》、《草原法》、《可再生能源法》、《清洁生产促进法》、《节约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民用建筑节能条例》和《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地方立法也较为丰富。可以说,碳交易的法律制度初见雏形,虽然缺乏专门的、完整的法律、法规,但是与碳交易相关联法律、法规已经初具规模。未来尚需理清大气资源使用的自由性、区域性和大气资源的整体性的制约关系,明确政府在开发、利用、分配大气资源和环境保护中的职权与职责,明确规定碳交易的主体、碳排放权、碳交易所的法律地位。
(二)碳交易的环境法制度基础业已形成
排放许可证制度和总量控制制度是实施碳交易的前提和制度基础。事实上,排放权交易的表现形式就是买卖排放许可证。1989年《环境保护法》确立了排放许可证制度,即以污染物总量控制为基础,规定污染源(点源)可以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数量的制度。由于排放许可主要指向“点源”的环境控制,为了解克服点源控制的局限,保证“面源”环境质量,1996年9月国务院《“九五”期间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正式提出总量控制环境政策。随后,《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污染防治法律中明确规定总量控制计划的法律地位;在一些流域或地区法规中,已经比较全面地规定了总量控制的要求。
(三)国内碳交易市场呈现整合趋势
我国环境保护部《中国碳平衡交易框架研究》报告建议在中国以省为单位推行碳交易制度。该报告首次提出以碳排放作为硬性指标,对经济活动加以监测及调控,建立“碳源-碳汇”交易制度。碳平衡交易框架拟在全国三十一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碳源—碳汇”的平衡账户,收取、支付碳基金和生态补偿金。若某省碳源总量高于碳汇总量,须按照超出部分的比例支付现金,用于补偿碳汇贡献大的地区,用于国家推行清洁能源计划、节能减排技术等;而若某省碳源总量低于碳汇总量,可获得生态补偿金。这也意味着,国家可以逐步建立起覆盖全国的排放权交易体系,通过买卖排放额度影响排放权价格,以达到宏观调控目标。
(四)碳交易强制减排指标分解工作进展顺利
2011年,首次写入国家五年规划的单位GDP碳强度指标已初步完成分解。包括二氧化硫、破坏臭氧层的物质、重金属、化学需氧量以及温室气体将纳入排放权交易的标的体系;碳交易可能将由单一的自愿减排交易向强制型交易转变。政府强制减排指标的制定可能会激发更多的企业减排的动力,碳交易的市场参与度可能增强。各级政府也期待着通过激励企业参与碳排放交易,或者通过植树造林、增加碳汇,拓展交易范围、发展绿色经济来解决本地区温室气体减排和能源利用率问题。
(五)国际气候谈判催生新型交易方式
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后,中国企业曾热衷于申请CDM项目。然而,2007年以来中国CDM项目屡屡遭到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拒绝。继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后,2010年11月,墨西哥坎昆会议成为各国互推减排责任的新战场。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复杂性和谈判结果的不确定因素给我国带来巨大的气候谈判压力,促使我国探寻新的地区之间碳交易的灵活机制,充分运用市场手段促进企业实现节能减排,尽早在国内建立起完善的碳排放交易机制,避免在国际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
四、“后京都时代”碳交易法律政策的完善建议
(一)行政管制立法的必要性
纵观碳交易发展演变的过程,不论是2002年英国最先确立的碳排放交易机制,或是2005年欧盟实施的碳排放量配额制度,还是我国排污权交易的个别地区实践,都是在政府控制碳排放总量基础上,将碳排放量分配给各个排放单位,然后设置一定的法律规则,使拥有碳交易排放配额或许可证的单位之间进行交易。哈丁“共有地”理论提示着,如果大气资源一旦彻底开放,碳市场就将陷入紊乱的境地。因此,传统的做法是将大气资源的碳排放许可与大气资源的所有权联系在一起。并非只要拥有碳排放许可证这一资源使用权就可以随心所欲,恰恰相反,这种使用权尽管从定义上看具有排他性,但是其内容体现了公共特征,大气资源作为共有资源的基础应该是自由意志与地域的共同性的彼此制约,应该建构基于自由意志(交易)的“制约体系”(管制)。在环境政策中引入市场机制是政府应对经济发展中的环境污染风险的有效方式。Callan和Thomas认为构筑污染物排放许可证交易体系需要具备两个关键因素,其一,确保在某区域内有足够的交易许可证,其二是,在该区域内应该要有交易这些许可证的条件。而这两项条件,无一能离开政府合法、有效的市场干预。
从碳交易的发展趋势来看,政府对碳交易体系的调控不仅仅局限上述功能,其法律干预或管制的功能将逐渐拓展至新的领域,如,建立区域统一的碳交易机构;确立碳交易的市场法律规则;构筑多方共同参与碳交易平台,使得政府机构、温室气体审核机构、认证机构、投资机构、保险机构、银行、市场买家、碳基金、咨询方、项目业主以及金融和商品交易所等多方主体全面系统地参与碳交易。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首次以国家规划的形式,为碳交易列出了实施时间表,提出要在“十二五”期间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政府运用管理控制手段对碳交易市场合法、有效的干预是如期达成碳交易市场建立目标的必要条件。
(二)明确行政管制下碳排放权的公共属性
具有行政管制特征的欧盟总量控制与交易体系是减排温室气体的成功范例,Peter Cramton和Suzi Kerr认为,“控制—交易”体系的关键在于如何分配碳信用证。从中国市场情况来看,基于配额的碳交易要优于以清洁发展机制为代表的基于项目的碳交易。碳排放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是指向剩余的排放许可证的交易;是基于国家按照环境标准、环境质量要求及经济发展的需要所确定的、经由许可证方式发放的碳排放指标的交易。因此,一方面碳交易是总量控制和环境达标前提,另一方面,其交易指标指向剩余的碳排放额度,虽有可交易的特征,但却不归属于用益物权,而具有浓厚的行政管制色彩。
(三)基于碳环境标准行政规范,公平分配大气使用权
科学分配碳强制减排指标、明确碳排放权是我国建立碳交易市场的基础。我国需借鉴欧盟“碳排放权交易”机制,走“总量控制—许可证—碳交易”政策路线。公开碳排放信息和明确义务是碳交易的基础,在未形成国际统一的标准之前,我国应当提升认证和注册的公信力,将碳排放权的指标分配明朗化。在信息公开的基础上,一方面,通过强制减排的方式,将碳减排指标纳入到环境保护规划当中,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强制减排工作,通过环境规划和减排指标的强制,开拓碳交易的市场参与度。另一方面,应当发挥市场的配置作用,还可以在国内成立自愿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森林碳汇纳入交易框架,建立碳排放权交易的平台。
(四)建立环境整体主义基础上的自由交易平台
从国际国内形势发展趋势来看,我国最终会加入强制减排国家行列,部分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碳交易所,我国如不能尽快建立交易机构,将丧失碳交易的定价权,在国际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从形式上看,我国各地虽然相继成立了一定数量的碳交易所,但是缺少全国性的碳交易平台,各地区之间迫切需要在碳交易管理模式、碳交易方式和碳减排的信息互通等方面进行有效的区域合作,以避免资源浪费和重复建设。从内容上看,亟待达成综合、统一的碳指标体系、交易规则和交易标准,使得碳减排指标更加具有公信力和不同地区之间的可交易性,从而从根本上化解公众、民间团体和国际交易伙伴的犹豫度。
(五)运用行政管制,拓展碳交易法律主体资格
就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现状而言,可以参与碳交易的主体身份比较单一,更多表现为有剩余碳排放许可证的企业或单位;政府、民间环境保护组织、家庭和个人尚未成为碳交易的现实主体。西方学者运用“准则—激活”原理研究发现,私人主体更倾向采用减排和购买的方式实现碳中和,政府和社会应该为其提供更充分的信息服务和帮助。有学者研究发现:让个人和家庭直接参与到碳减排市场,管理成本可减少一半。由于非政府组织(NGO)和非营利组织(NPO)在环境保护中曾经发挥的重要作用,应该确认政府部门和民间力量的通力合作,广泛参与到碳交易当中来,实现法律主体的多元化。
[1]刘伟平,戴永务.碳排放权交易在中国的研究进展[J].林业经济问题,2004,(4).
[2]WorldWildlifeFund(WWF).Makingsense oftheVoluntaryCarbonMarket:AComparison ofCarbonOffset Standards[R].WWFGermany,2008.
[3]宋蕾.碳市场发展趋势与中国碳交易研究[J].生产力研究,2010,(2).
[4]冷罗生.构建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法律思考[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
[5]邢佰英.中国或成全球最大碳交易市场[N].中国化工报,2011-04-14(5).
[6]宋蕾.碳市场发展趋势与中国碳交易研究[J].生产力研究,2010,(2).
[7]邵好,胡雅君.碳交易所为何交易不起来[N].中国化工报,2011-04-14(5).
[8](日)佐佐木毅,(韩)金泰昌.地球环境与公共性[M].韩立新,李欣荣,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邵好,胡雅君.碳交易所为何交易不起来[N].中国化工报,2011-4-14(5).
[10]罗胜.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问题与对策分析[J].中国—东盟博览,2011,(1).
[11]Callan/Thomas.Environmental Economics&Management-Theory,Policy and Application[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12]Peter Cramton and Suzi Kerr.Tradable Carbon Allowance Auctions:How and Why to Auction[R].The Center for Clean Air Policy,1998.
[13]Michael P.Vandenbergh and C.Steinemann.The Carbon-Neutral Individual[J].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2007,(82).
[14]Michael P.Vandenbergh,Jack Barkenbus,Jonathan Gilligan.Individual Carbon Emissions:the Low-hanging Fruit[J].UCLA Law Review,2008,(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