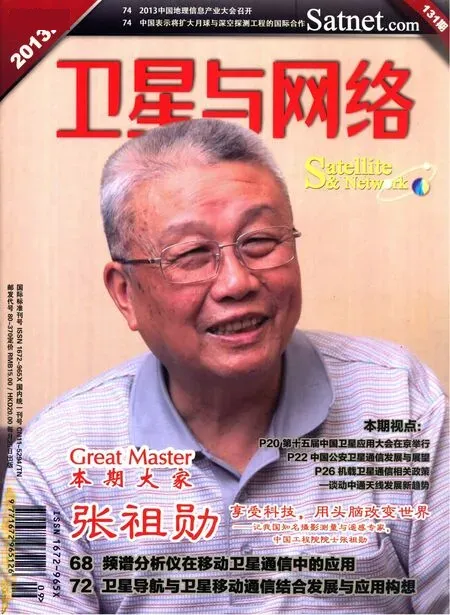享受科技,用头脑改变世界——记我国知名摄影测量与遥感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张祖勋
+廖芳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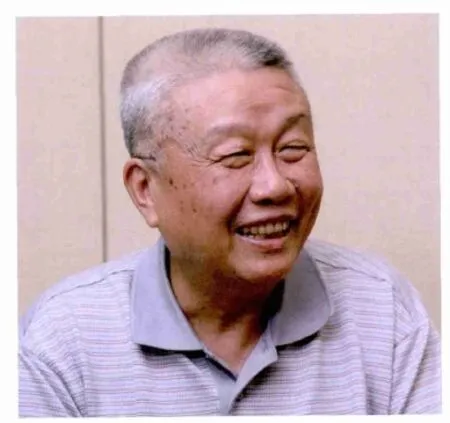
一脸慈祥的微笑,是第一印象,在谈笑间,他轻描淡写地讲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可就是这样一位看似平淡无奇的老先生,引领了我国摄影测量的颠覆性改革;就是这样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先生,用自己的坚持,捍卫了中国的知识产权;就是这样一个精神矍铄的老先生,76岁仍然在坚持自己的科研和教学之路。他把经历当做财富,把艰难当做磨练,把工作当做生命中最重要的使命,他可以用14年的时间,在最艰苦的环境之下,纯粹地开展科研工作,最终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他就是我国知名摄影测量与遥感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张祖勋。
张祖勋院士长期从事摄影测量与遥感的教学、科研工作。主持完成了多项国家和部委重大科研项目,为推动我国摄影测量的产业革命做出了突出贡献。他系统全面地发展了摄影测量的理论,在数字摄影测量理论、影像匹配的理论与方法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就。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多项国家和省部级奖励
潜心修行,14年探索全数字化测图科技
在上世纪80年代,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胶片是影像最好的载体,但是王卓之先生却在1978年提出了摄影测量的全数字化。在当时,王先生的想法犹如晴天霹雳,颠覆了当时传统的理念和认识,在一开始并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同。作为王先生最优秀的助手,张祖勋院士鼎力支持王先生,积极开展科研。没想到,张祖勋一口气坚持了14年,终于在摄影测量全数字化方面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
记者:张院士,您好!非常荣幸您能够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您作为我国知名的摄影测量和遥感专家,我们首先想请教一些专业方面的问题,请您给我们的读者普及一些这方面的科普知识。您大学的专业就是摄影测量相关的吗?
张院士:是的,我起步于上海同济大学,成长在武汉测绘学院,读的是测绘相关专业,毕业就留在学校从事相关研究和教学工作。
记者:您真正开始摄影测量的专业,大型研究是什么时候?
张院士:1978年的时候,我的导师王卓之先生提出摄影测量的“全数字化”,在这个时候,我国甚至国际上,都普遍认为影像只可以保留在胶片上面,而影像“数字化”这个理论在当时显得非常异类,大部分人都不理解,觉得不可能实现。这不仅仅在国内,即使在国际上反对声也是络绎不绝,直到1992年华盛顿ISPRS大会期间,还有人拿了一张230*230毫米的航空胶片做了一个“旋转”动作,用计算机不可能像模拟仪器那样实现“实时旋转”为理由对摄影测量的数字化提出质疑。当时我作为王先生的助手,我觉得王先生这个想法很有意思,很有挑战性,不管它最终能否用于生产也是值得一试,多值得为之一搏。现在看来人生就是在这样的探索中前进,在看似不可能的事变为可能中成长。由此我开始走上了摄影测量“全数字化”的专项研究课题。
记者:当时这个课题项目成立的背景是什么样子的?
张院士:首先,在理论积累方面,摄影测量全数字化在我国还是一片空白,我们要做这个项目,就必须从零开始,在国内没有任何的参考资料,在国际上也寥寥无几。回想80年代初,德国摄影测量专家、国际摄影测量遥感学会秘书长G·Konecny教授来武汉测绘学院讲学时,我对于影像匹配问题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实在有失礼貌。在资金方面,国家拨款120万元,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但是相对于“全数字化”而言,正是少之又少。我们花费25万美金由英国购买了影像数字化器、数字影像输出设备、与NOVA 3/12计算机,当时还没有屏幕显示器,更谈不上“图像显示”,它只有64K内存,利用汇编语言才可能扩展到256K内存,相对于一张影像上百兆的数据量与今天具有几个G内存的计算机而言,实在是太简陋。这对我们的全数字化研究来说,很多东西我们必须要像傻瓜样的一点点去做、蜗牛似的一点点的爬。这又使我想起王卓之在60年代对我说的一句话:“不怕慢、就怕站!”。
记者:你们这个项目组当时有多少人呢?
张院士:最开始,我们有十几个人,可是到后面,有一些同事转去做教学工作了,也有一些同事转到其他领域去了,一直到最后做完整个项目的就几个人了。
记者:在做这个项目的过程中,您遇到了哪些困难呢?
张院士:在上世纪70、80年代,做大项目都比较困难,很多项目会因为资金匮乏或者研究周期太长而搁浅。尤其是周期太长这个问题,让不少人望而止步,周期太长,不容易见成效,因此在考核、绩效方面就比较困难了。因此,我们项目也遇到了人力方面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项目从一开始的十几人,变成最后的几个人的重要原因。
记者:您这个项目是什么时候开始渐入佳境,开始有所成就,得到同行认可的呢?
张院士:项目大概是1979年启动的,开始的时候,我们所进行的试验时除计算机外全人工,就是说计算可能只要半小时,而人工的准备工作需要几天。当时我还经常去北京北沙滩遥感所,希望利用他们开发的“影像数字化器”进行试验。直到1982进口了全套设备,试验开始正常化,前后共经历了整整六年的艰难的历程。到了1985年,我们的全数字化自动测图软件编制成功,这意味着我们第一阶段的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记者:六年时间,太不容易了,当时你们编制的这个全数字化自动测图软件在国际上处于什么样的水平?
张院士:我国自动化摄影测量技术起步很晚,我们这个全数字化自动测图软件可以说是我国首个全数字化的自动测图软件,全面颠覆了我国胶片摄影的传统技术。就是在国际上,我们的这套软件也是非常先进的,让国际上很多专业人士刮目相看,可能这也是为什么90年代初有两位外国知名教授希望能共同合作开发成商品的原因。
记者:软件编制成功之后,这个项目就算是完美画上句号了吗?
张院士:当然没有,1985年的这套全数字化自动测图软件还只是个理论的试验,不仅仅当时的速度慢得像蜗牛,而且地形是复杂的、影像是复杂的、总之实践比理论实验要难得的多,总之理论还需要实践的检验。我和我的同事开始了漫长的把理论转化为应用的过程,在这个阶段,我们碰到了数字化过程中一个难题,就是如何让计算机从两张不同角度的航拍照片几百万个点中“快速而准确”找到相同的匹配点。经过苦苦寻觅,我看到一本讲人工智能图像处理的书籍,获得了灵感,终于找到影像匹配这一世界性技术难题解决的途径。就这样,我们完成了理论转变为应用的完美转变。
记者:对于这段经历,您现在回过头去看,是什么样的感受?
张院士:14年确实挺艰苦的,但是我们坚持下来了,我和我的同事一起克服重重困难,攻克一个个难题,算是给国家数字化自动影像测绘交差了吧。
从十几个人的队伍,最后变成了几个人的队伍;从数字化影像测绘的零开始,走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从1978年到1992年,整整坚持了一十四年。张祖勋院士选择从零开始,选择了一段注定开始默默无闻的经历,经过十四年的艰苦奋斗,张祖勋院士终于完成了中国首个全数字化的自动测图设备,弥补了我国在这个领域内的空白。1993年全数字自动化测图科技成果荣获了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三种经历,三种历练
经历了大海方知什么是豁达,经历了大山方知什么是沉稳,经历了沙漠方知什么是顽强,什么样的人生经历开出什么样的生命之花。张祖勋院士把艰苦当做财富,他经历了部队生活,知道了什么是钢铁般的一直,经历了农村生活,知道了什么是吃苦耐劳,经历了国外学习,知道什么是超越自我。
记者:在您的人生经历中,有哪些经历让您记忆犹新?
张院士:在我的人生中,有三个半年,三种经历让我感触非常大,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第一段经历是半年的部队生活,
记者:这段经历是什么时候?

张院士: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家测绘局撤销了,测绘局下属的单位,包括学习,生产单位。当时解放军测绘学院下放在河南五七干校,北京的校区由北影占用,这样就在武测校区重新组建军测,从武测大约挑选了二三十个人,这样我就去了军测。由于我们没有当过兵,就穿四个口袋当干部,为了补上这一课,我到了54军162师486团6连当兵。
记者:您到部队里面主要做什么呢?
张院士:在部队里面就是普通的士兵,和班长、战士们住一起,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学习与训练。
记者:在部队里面学了些什么东西?
张院士:部队将纪律和作风,要求被子叠得像豆腐干一样整齐,床单不能够有褶缝,床是不能做的,只能够坐在小板凳上面。
记者:在部队您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
张院士:70年恰逢野营拉练,我们在河南拉练的1700多华里。每人背包、枪支、手榴弹还要背米袋,有五十多斤,就这样背着一路走,一般一天走八九十里路,最多一天走了120里路。当时是在河南拉练了一整个冬天,晚上睡得是麦秆,铺的是地铺,盖着一条薄被子。拉练的时候,最难熬的就是晚上起来放哨站岗,特别是夜里2点到4点的岗哨,再回去睡觉,被窝就很难最暖和起来了。

记者:对于战士们来讲,部队生活还好,但是对于你们这些教师,搞科研的人来说,确实不容易。您说您在农村呆过半年?
张院士:我是1965年搞四清运动的时候下到湖北孝感阳岗,和我一起下去的还有我的老师陈适,他是陈布雷的儿子,那时候农村的条件特别艰苦。
记者:在农村您记忆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张院士:那时候国家经济比较困难,四清有条四不吃的纪律,我们下到农村去就不能够吃肉,每天吃饭一点点荤腥都没有,我们下去的人也是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基本上都不会去吃肉,非常老实。
记者:您后来是到瑞士学习过,对吗?
张院士:1976年的时候,我去瑞士学习了半年,因为从来没有出过国,对国外的生活方式不了解,还闹了不少的笑话呢。
记者: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在瑞士的一些经历吗?
张院士:那时候出国的人比较少,大使馆的人带着我们,第一次去超市买东西,大使馆的人就让买了短波收音机,说是每天晚上9点要收听北京早上4点钟的第一次广播,要听国内的新闻,不要被国外的思想带坏了。
记者:现在出国的人多了,大使馆都不会管了。
张院士:我们从超市买了东西回来,按照国内的习惯泡了2杯白糖水给他们喝。后来,使馆的一个二秘跟我们说,以后招待人,不要泡糖水了,应该用啤酒招待。对比国内,用糖水招待客人,那可是比较优厚的接待,这就是当时我们与国外的差距的典型。
记者:是啊,当时中西方生活方式差异太大,你们是怎么到瑞士的?
张院士:我们乘坐瑞航的飞机,先是从北京到上海,孟买,希腊的雅典,再到日内瓦,苏黎世,飞行了19个小时。当时我们两人一人一套中山装(中山装是国家给的钱做的),一件雪花呢的大衣(借的),一双黑皮鞋,再加上一人一顶帽子,真可谓着装统一。当时自己还感到很神气,可是走在一起下飞机的人群中非常异样。事后到机场接我们的二秘说,你们是全身制服,给人感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来了。对比今天,改革开放几十年的进步有多大。
张祖勋院士喜欢想象,在他的世界里面,所有的事情和事物都变成了多维空间,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中,想象必不可少。在不轻易间,丰富的想象力可以转化为创造力,从而转化为生产力。在长达40、50年的科研工作中,张祖勋院士坚如磐石,把坚韧和想象力完美结合,享受科技,用头脑改变世界。|SAT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