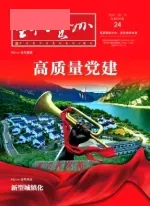民族交融积淀“文化千岛”
文∣张幼琪 史继忠 王哿幸子
(责任编辑/李 坤)
如果用图形表示的话,贵州的多元文化应该是一个多维的网格空间。这个多维网不仅代表着文化本源的49个民族,而且还代表着每一个民族后面所可能拥有的更丰富的文化细分。
“融而未合”的多元文化
贵州处在川、滇、湘、桂之间,是西南民族流动的大走廊,也是古代南方的四大族系,即氐羌、苗瑶、百越、百濮四大族系的交汇地。之后,演变成苗族、布依族、侗族、水族、彝族、土家族、白族、瑶族等多个单一民族,他们都具有各自的文化传统,形成各自独特的文化特征。
在长期的民族迁徙过程中,氐羌民族自西向东发展,苗瑶民族自东向西移动,百越民族自南而北推进,濮人则四处迁徙,汉族主要是从北面和东北面进入贵州。各民族相互对流,互相穿插,形成“大杂居、小聚居”,“又杂居、又聚居”的分布状况。多种不同体系的文化在贵州各自发展,同时因地理环境都打上“山地文化”的特征,但历史、地理及民族分布诸种原因,各种文化在贵州都获得各自的发展空间,虽然互有交融,但往往是“融而未合”、“分而未化”。虽然汉文化在明代以来逐渐成为强势,但并未将其它民族完全“汉化”,呈现出“多元并存,共生共荣”的文化面貌。
在这样的文化空间里,少数民族有自己的语言,同时又兼通汉语或其它民族语言,譬如荔波瑶山的“白裤瑶”都说瑶话,但由于社会交往的需要,大都通汉语和布依语。贵州的汉语均属“西南官话”,以川方言为基础发生演变,黔东南、黔南一带的汉语,混杂了当地少数民族语音。春节本是汉族的节日,与若干少数民族的年节不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几百年时间内,贵州的少数民族也普遍都过春节,而在春节期间的活动又各有民族特点。过去把受汉文化影响较多的称为“熟苗”,把未受汉文化影响的称为“生苗”,虽然清代晚期以来,完全不受汉文化影响的苗族事实上已经鲜见。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前,许多传统民族文化仍然鲜活存在,近20年来由于物质文化传播与现代传媒文化知识体系改变,传统民族文化的改变速度加快。
贵州山川隔阻在古代影响着民族之间的交往,但地理环境的分割并不能完全阻止文化的交流,同一民族散布在许多地方,并不因此变成几种文化,例如苗族;两个不同的民族同住一地,而文化仍各具特征,例如在荔波县,瑶族与布依族错杂而居但文化不同。
历史上,贵州长期实现“土流并治”,对多元文化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黔西北,在历史上长期是彝族土司统治,彝文化在这里自然上升为主流,所以彝文经典,彝文碑刻及其他文化传统在这里相当丰富。黔西南布依族地区,直到民国年间,许多地方仍为“亭目”统治,布依文化在此大量保存。黔东南的黎平、从江、榕江三县,由于交通较为闭塞,“山侗款”制度盛行,侗文化的保存、发展比北部侗族更加典型。黔东南“苗疆腹地”,在清代雍正改土归流以前,长期处于“自治”状态,没有纳入流官管辖,苗族文化得到充分发展。因此,在贵州,由于民族分布,地理环境与历史条件不同,出现了“十里不同风”的文化面貌。就某一文化而言,仿佛是大海中的一个孤岛,这种现象,在文化学上叫做“文化孤岛”。但就贵州全省而言,则是风格各异的“文化千岛”。
600年来的文化积淀
贵州是汉族移民较多的省区,明以来不断有移民进入。大体来说,汉族约占2/3,少数民族约占1/3。移民来自不同地区,带来了各地的地域文化。显出“五方杂处”、“风俗不同”。且因受邻省影响而互有差异。《黔南识略》曰:“介楚(两湖)之区,其民夸。介蜀(巴蜀)之区,其民果。介滇之区,其民鲁。介粤之区,其民蒙。”说明同属汉族,所受的文化影响都不一样。由于汉族移入的时间、地点不同,文化上也有差异。最突出的就是“屯堡文化”,它具有汉文化特征,更接近江南文化,在群体中长期传承,与后来进入的汉族颇多差异。“老巴子”在普安一带,他们是汉人,语言近乎湖南话,与周围的汉族有较大差别,故其语言形成了一个“方言岛”。近半个世纪以来,移民来自四面八方,文化虽渐交融,但有许多故乡的传统仍暗中在家里延续,同乡在一起还是说家乡话。
对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是教育。明以前贵州的学校可谓是凤毛麟角。明代实现“治国以教化为本,教化以学校为先”的方针,把教育作为“敷训导民”的治边国策,从此儒学教育在贵州兴起。不但有官学、书院、农村中大量兴起的私塾,还有专门培训土司子弟的司学,吸收土司子弟进入国子监,对少数民族学生给予优惠待遇,这在贵州文化与智力开发上是一个重大的变化。
明清五百多年,汉文化不断传播。黔西北的彝文碑刻,大部分是彝汉合璧,彝族土司安贵荣、安国享都有相当文化基础,还能题字写诗。彝族的余氏家族形成了一个诗人群,从乾隆年间的安吉士开始,出现了余家齁、余珍、余昭,到清末民初的余若泉,都有诗集传世。明代水东土司宋昂、宋昱的诗选入《明诗综》,清代锦屏苗族作家龙绍钠有《亮川集》传世,侗戏的鼻祖吴文彩吸收汉文化创造了侗戏。水书中大量引入汉字,或反写,或倒书,以汉字记录水语。
汉文化传入贵州后,出现了两个文化高峰,一个是“阳明文化”,另一个是“沙滩文化”。王阳明的学说是在贵州形成的,“龙场悟道”成为王学的起点,他的教育思想基本上是在龙岗书院形成,他的首批弟子是贵州人,最先在贵阳讲述“知行合一”学说,并形成一个“黔中学派”,在中国儒学发展上形成一座高峰,对
海内外有深远影响。清代中期以后,在遵义的沙滩出现了郑珍、莫友芝等文人群体,出现了黎庶昌这样的外交家,使沙滩成为儒学之乡、诗文之乡、书法之乡。贵州的多元文化当然也包括汉文化在贵州这块土地的发展与创造。“六千举人,七百进士”是贵州人才兴起的象征,这虽与文化发达地区比起来还有较大差距,但中原教育已有两千多年历史,而贵州仅用了五百年的时间,这不能不说是贵州文化教育昌盛的范例。
在贵州漫长的文化发展中,还有一些其他元素的注入:如元代蒙古族人的移入,明代回族的移入,清代蒙古族、回族、白族移入等。这些民族的到来,一方面带着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深入贵州,另一方面又受到后来逐渐强大汉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以及其他本土民族文化的碰撞和融合,在贵州各地形成了多元文化的组成元素。
总体上说,贵州文化的发展,是在各民族不断迁徙流动中形成的。如果用图形表示的话,贵州的多元文化应该是一个多维的网络空间。每两个民族之间会有一条由很多点组成的线,代表着两种民族文化互相影响下,所产生的不同文化单位。同时在每两种文化之间的线上那些点可能也会与别个民族或别两个民族之间的点,连接成许许多多其他的文化线。所有的线组成在一起,就构成了贵州多元文化网络状态。这个多维网不仅代表着文化本源的49个民族,而且还代表着每一个民族后面所可能拥有的是更丰富的文化细分。正是这些文化的“碰撞融合”,才造就了今天贵州文化的多元化。
贵州虽然不是民族自治区,但少数民族的总量超过1250万人。在众多的少数民族中,人口超过10万的有苗、布依、侗、土家、彝、仡佬、水、回、白等民族。此外还有仡佬、毛南、畲、蒙古、满等其他民族,民族成分之多,按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的比重排序,贵州居全国第五位。众多的民族与他们的细分构成了贵州文化的复杂多样,多元文化的特征极其明显而个性化,建筑、服饰、饮食、婚俗、祭祀、节庆、艺术等等方面,都异彩纷呈。许多民族文化不仅组成了贵州多元文化,而且是文化中的一个个闪亮点,如1992年,世界保护乡土文化基金会就把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苗族列入了该组织在全球的18个保护圈之列;1995年,由挪威政府援助,在六枝梭嘎苗族社区设立了中国的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其后,挪威政府又帮助贵州陆续建立了隆里、镇山、堂安三个“生态博物馆”。近年来,世界旅游组织又把贵州黔东南巴拉河流域的苗族村落和安顺屯堡文化,列入了发展乡村旅游的示范点。这些都说明了贵州多元文化的珍贵和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