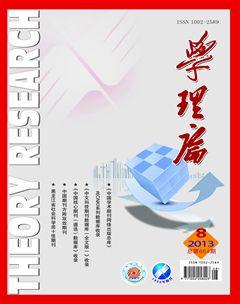贵州苗族生态观念及当代价值研究
谢仁生
摘 要:贵州境内的苗族大多生活在生态状况良好的山区,这主要得益于苗族人世世代代对生态的保护。从苗族先民到今天的苗族人一直都坚信着万物有灵论的原始宗教观念,同时也世世代代传承着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等原始的宗教习俗。这些都为苗族人赢得了青山绿水,另外,苗族通过制定各种形式的村规民约和习惯法对村民的日常行为加以引导和约束,从而为生态的保护筑起了最后一道保护墙。苗族人的生态保护理念和实践不愧是一个榜样,值得其他民族和地区学习借鉴。
关键词:苗族;万物有灵论;自然崇拜;动物崇拜;生态观念
中图分类号:B8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2-0078-02
“天人合一”是对自然与人之间最原始的关系的恰当的描述。在远古时期,“弱小”的人类对自然界一切满怀敬畏,打雷闪电,刮风下雨等自然现象和生老病死等生物的生理现象都被视作是“神灵”的作用。正是基于这种敬畏感和这种原始的万物有灵论,在人类的童年时代,自然与人关系极为和谐。但是,当人类理性逐渐成熟,并用来考察他周围的自然的一切时,人类不再相信万物有灵,对自然的敬畏感也随之消失了,最终导致自然与人的关系逐渐疏远,尤其是在近代科技革命之后,人们凭借着知识与技术,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甚至是“人定胜天”的雄心壮志之下,人类开始了肆无忌惮地向大自然索取,生态环境也因此而开始恶化。可喜的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贵州某些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依然坚信着万物有灵论,对许多自然之物充满了敬畏,也可以看到大自然回赠给这些少数民族地区青山绿水,生态和美景象。
一
生态危机应该是当今人类面临最紧迫、最棘手的问题之一。保护生态就是保护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园,这已经成了常识。世界各国早已尝试依靠法律、经济和行政等方式来解决生态危机,但是,若干年的努力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生态环境的恶化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遏制。究其原因,其症结之一在于当今主流意识中生态观念仍然是固守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人类自身生存环境”这一伪装了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并没有真正从植物、动物角度去考量,因此这种旧的生态观念已经不能应对当代的生态危机问题。其症结之二在于人类很难减少自身的欲望,减少消费,降低消耗。正如古人云:从俭入奢易,从奢入俭难。那些已经尝到了依靠现代科技革命和靠牺牲环境所带来的物质富足生活的甜头的人们,决不愿意回到物质相对贫乏的生活,而这恰恰是保护生态所必然的结果之一。于是一个可怕的局面出现了,富人希望保持奢华的生活,穷人也梦想过上富足的生活,这种合力必然致使任何国家和地区自始至终都不愿放缓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步伐,并且想当然地认为只有发展好了才能解决好生态问题。当我们仔细考察某些少数民族的生存理念和传统观念时,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其中蕴含了许多有助于解决上述症结的理念与经验。他们的许多观念和习俗有效保护生态环境,而且他们简单的生活也客观上降低了对自然的索取。
贵州境内生活着数百万的苗族,他们大多定居于偏远山区,这些地方往往是森林植被茂密,古树参天,自然环境非常优美。苗族居住地区之所以拥有这种美好的生态环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得益于苗族人的生态观念。这些观念大多数以神话传说、宗教习俗、村规民约等文化形式传承和保留至今。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他们至今仍然坚信万物有灵论这种观念。众所周知,万物有灵论最早产生于远古时期,其根本源于人的理性还未充分发展到足以解释自然力,于是人们普遍对自然万物赋予人格化、神秘化。同样,贵州苗族先民也很早就有了万物有灵论观念以及与之相应的自然崇拜。他们认为“树大有神,石大有鬼”。苗族把许多常见的自然物,如日月星辰、山川河流、花草树木等视为具有人类那样的灵性。“苗族的‘万物有灵还体现在周围自然界、动物、植物的关系是一种社会化的个体之间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人与自然可以结成良好的社会关系甚至亲密的血缘关系。苗族史诗中描述:人类的始祖姜央就与自然物雷公、牛、龙、蜈蚣等是亲兄弟,是蝴蝶妈妈所产的十二个蛋所生。
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枪手部落”的岜沙苗族热爱自然,亲近树木,崇敬树神,认为每一棵大树都具有一个灵魂,是他们祖先的化身,正因如此,大树成为了他们的保护神,庇护他们寨子人丁兴旺,平安无事。《苗族古歌·运金运银》对此现象有大量相关的描述,当地苗族人欲砍大树用以造船运输货物,但是,任凭人们如何使劲砍伐,大树就是不倒,于是人们就怀疑这大树不是一般的树,而认为“树子脚下有蚂蚁,树梢枝头有鬼怪,树子才会砍不倒”。于是,砍树的鲁猛“嘴里咬着芭茅草,头上反戴三脚架,斜眉怪眼来砍树”,最终才把大树砍倒[1]。正是这种万物有灵论观念,岜沙的苗族对自然爱护有加,在他们那里,肆意乱砍滥伐的行为是有罪的。在他们看来,“人来源于自然,归于自然;生不带来一根丝,死不带走一寸木”。也正是这种观念,使得苗家人寨子中往往都是古树参天,山上树木密布,景色秀美。
二
人与自然关系可以是物质的、经济关系;也可以是生态的、伦理的关系;还可以是审美的关系。中国文化中从一开始就崇尚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天人合一”的关系,从《易经》的天地人三才者的思想到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再到庄周的“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从《中庸》的“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再到汉儒董仲舒的“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等等,这些中国思想史代表性的人物的思想无不说明中国传统思想从来都是坚信:人是一个小宇宙,并且与自然这个大宇宙是相通相融的,因此,人应当顺应自然,合乎自然而生活。但是,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今天早已被奔走在现代化的征途中的人们所遗忘。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人们无所顾忌地向自然索取,并认为只有解开自然的秘密,进而改造自然,才能解决好人类所面临的许多问题。西方文化那种古老的“人类是大自然主人”的观念早已被《圣经》以故事的方式表述出来了:上帝创造亚当和夏娃之后,告诫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生,遍野大地,占领地球,统治大海中的鱼、天空中的鸟以及大地上的一切动物”,这种隐秘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接受,然而,这些观念却止步在贵州大山之外,在贵州某些山区,依然有许多少数民族坚信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他们世世代代都明白一个简单而又重要的道理,人不能离开自然,人类应该与自然和谐。
最有代表性的是贵州境内的世居的苗族,他们一般生活在山区,生活上依赖于大山,除了种植庄稼,打猎也是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是他们不是焚林而猎,涸泽而渔,而是合理利用环境,有节制地狩猎。在他们世世代代的生产与生活的实践中积累丰富的善待动植物经验,同时也折射出苗族人所拥有的宝贵的生态思想。
因为山区的可供耕作的土地有限,除了靠农业耕作维持生活之外,苗族人大多还兼有牧业和狩猎的习惯。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他们认识到自己与动物关系密不可分。苗族先民和其他以狩猎为业的民族的先民一样,一方面生活上依赖于动物,同时动物攻击力和危险性又让他们心生恐惧,因而,苗族和其他许多少数民族一样把动物神化,把某些动物尊为神圣之物予以崇拜。这种动物崇拜现象反映了苗族人对动物的思想和情感,这实际上是赋予了动物和人同等的“人格”,充分体现了苗族人对动物的尊重,也充分展露了苗族人的生态思想。例如,从苗族古歌《枫木歌·十二个蛋》中,我们也能窥见苗族人民对动物的尊重和爱护之情。在该古歌中,苗族的先民们认为人、神、兽拥有共同的祖先,当然,神、兽要比人低一点。他们还认为,像龙、蛇、虎、牛、象等动物,以及天上的雷公神,地面上的人类都是“同一个早上生”,都是由同一个母亲下的蛋,他们是由同一母亲孵出的亲兄弟,只是人要比龙、蛇、牛、象等动物以及雷公神要高明,而且更有心计。正是有这种生态观念,黔东南一带的苗族人在打猎之前,必要焚纸烧香,以求神灵护佑。捕获到手的猎物,通常要先让人折一把芭茅草从头向尾刷一遍,同时口中历数这个猎物的罪状,然后才做处理。因为在他们眼里,既然人、神、兽是同祖同宗,那么他们之间就应该亲如兄弟,而无缘无故地猎杀兄弟就显然是有悖道理的,有朝一日肯定会受到神灵的怪罪。当然,苗族人这种宗教习俗和观念在少数民族里不是个例,例如,同样生活在贵州的其他少数民族侗族同样拥有这种原始宗教习俗和观念,侗族古歌《人类的起源》也表现出类似的观念,侗族的先民认为,人和动物最初是兄弟,他们一起生活,但是后来人依靠自己的智慧走出森林,离开了动物群。
正是因为苗族人把动物视作兄弟,他们与动物、山山水水构成了一个和谐的生态环境。苗族的某些文学作品、歌词和史诗中都不乏这方面的描绘。例如《苗族史诗·打杀蜈蚣》中这样描写人类祖先姜央与众动物踩鼓跳舞的嬉闹场面:姜央丢开犁,把牛放在田当中,跑上田坎来踩鼓。鼓声咚咚响,往前跳三步;鼓声响咚咚,往后跳三步,他会跳不会转身,会转身不会转调,畅游的瓢虫来教他转身,飞舞的蜜蜂来教他转调。……啄木鸟敲鼓,咚咚又咚咚,姜央在田坎上跳,水牛在田里面跳,牛尾巴跳在两脚间,跳累了都不知道。牛鞭听见鼓响,它把牛背当舞场;蚊子一群群,围着牛头转,踩鼓踩得更欢[2]。
由此可见,苗族的先民早已经认识到人是大自然的产物,大自然与人的关系亲如母子,大自然是人类的母亲,人类是大自然的孩子,而且是她众多孩子之一。飞禽走兽,鱼虾虫卵,都是大自然的孩子,人类与它们都是亲如兄弟的关系。从起源上,人和其他所有的生命都是同根同源,因此地位上是平等的,彼此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苗族先民这种把人看成与动植物同源共祖的意识实际上就是一种“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
三
苗族人的自然崇拜、万物有灵论和动植物崇拜等宗教观念和宗教习俗也许被今天人们认为过于古老和陈旧,不合时宜。但是,正是这种宗教观念和宗教习俗在引导和约束人们的日常行为习惯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最终使得苗族人居住地的生态环境良性有序。然而,苗族人对生态的保护不只是依靠于宗教习俗、宗教戒律和神话故事的约束力,而且还有苗族各村寨历代制定下来的各种村规民约和习惯法。相比前者,村规民约和习惯法的约束力要更强,也更严格。这些传统的村规民约和习惯法除了保护生态环境之外,还为维护当地社会秩序,调解邻里纠纷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有的苗族的村规即“榔规”(苗族自己把寨子的公约叫“榔规”,商议并制定寨子里公约的组织叫“议榔”)中规定:所有村民必须要爱护集体的树木、土地上的财产。“烧山遇到风,玩狗雷声响。烧完山岭上的树干,死完谷里的树根。地方不依,寨子不满,金你郎来议榔,罗栋寨来议榔。封河才有鱼,封山才生树。”[3]有的苗族的“榔规”规定,“鼓山林”上的树木不能任意砍伐,必须按规定进行。所有公家的森林和牧场都有公约保护。他们相信,封山才有树,封河才有鱼,因此,他们实行封山育林,不准放火烧山。若是有人公然藐视“榔规”,恣意乱砍滥伐,则将被处以十二两银子的罚款;若不肯认错,不服处罚,则要加倍处罚,即处以二十四两到三十六两的银子罚款。
村规民约和习惯法与自然崇拜和动植物崇拜等宗教习俗产生的根源不一样,它是人们理性的产物,是人们有意识地制定出来的,是该民族精神和文化的反映。从内容上看,苗族人有关生态伦理的村规民约和习惯法反映了苗族人的宗教和道德观念,反映了苗族人世世代代的价值观念,它也是对本民族的人们日常行为的强制,目的在于使人们更自觉地保护生态。村规民约和习惯法虽然与宗教观念和宗教习俗形式不同,但是它们与后者一样都使苗族人周围的生态环境得到了保护。
由此可见,苗族人原始宗教信仰、禁忌反映了苗族人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热爱之情。从其对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文化中,我们不难发现苗族人对大自然动植物平等相待,尊重有加,尽管他们的生活也依赖于动植物,也要猎杀飞禽走兽,但是,他们并没有把动物当成可以任意宰杀的对象,而是对动物的生命同样充满了敬畏。苗族人在处理人与动植物的关系时,尤其懂得“适度”原则,他们不是肆意地向大自然索取、无节制地砍伐树木和猎杀动物,而是以“知足常乐”的心态掌握好分寸从而避免了竭泽而渔现象。由于懂得“知足”,因此他们过着相对简朴的生活,这使得他们不必过多地向自然索取。他们亲密地与周围的动植物接触,相对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从这个民族的村规民约和习惯法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苗族人民对大自然、大自然中的动植物的情感,也能窥见苗族人生态伦理智慧。尊重大自然,善待一切动植物这些生态观念经过苗族人代代相传,已经溶进了这个民族的血液之中,变成了苗族人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它深深地内化到这个民族的民族心理、民族精神之中。这种生态观念和生态文化已经成为了苗族传统文化璀璨的部分,在当今这个生态日益危机的时代,它显得尤为宝贵。
参考文献:
[1]贵州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苗族古歌[M].燕宝,整理译注.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