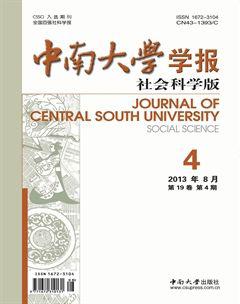熊大木书坊主身份的考证尚难动摇
收稿日期:2013?03?11;修回日期:2013?05?08
作者简介:苏亮(1980?),男,山西太原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太原大学教育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摘要:历来研究者认为,熊大木以小说编创者兼书坊主的特殊身份对明代小说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陈旭东先生《熊大木身份新考》一文,认为“熊大木作为书坊主的说法是不成立的”。遗憾的是,陈文立论并没有以过去的研究成果为基础,观点虽有新意,但无更有说服力的文献材料可以举证,熊大木书坊主的身份尚难动摇。
关键词:熊大木;书坊主;陈旭东;胡士莹;孙楷第;陈大康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4?0191?04
熊大木是明代通俗小说的编创者之一。他之所以引起关注,不在于其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而在于其本人另一个特殊的身份——书坊主。以小说传播者的身份介入小说生产领域,熊大木和以他为代表的群体在明清小说变迁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近见陈旭东先生发文《熊大木身份新考》(为方便论述,以下简称“陈文”)[1],否认“熊大木是书坊主”这个在学界几乎是定论的观点。那么,究竟是否如陈旭东先生所言,熊大木并非书坊主?重新审视以往关于熊大木身份的考证过程,笔者认为尚不能轻易下此结论。
一、熊大木身份考证的研究回顾
熊大木是书坊主的观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已被提出。胡士莹先生遗著《话本小说概论》第十三章《明代话本的著录和叙录》在谈到《熊龙峰刊四种小说》时,按语云:
嘉靖壬子(三十一年,1552)杨氏清白堂本《武穆王演义》和嘉靖癸丑(三十二年,1553)杨氏清江堂本《唐书志传通俗演义》都有建阳书林熊钟谷(大木)的题名,且版式与此四种极相类,钟谷又号鳌峰,似与龙峰为兄弟辈,知龙峰亦为书坊主人无疑。[2]
胡先生认为《熊龙峰刊四种小说》的编创者熊龙峰是建阳书坊主。判断依据之一便是熊大木的书坊主身份,并称熊大木“又号鳌峰”,至于“大木”和“钟谷”分别是熊大木的名、字,还是号,这里没有说明。胡先生之所以认定熊大木是书坊主,源于其所见之嘉靖三十一年(1552)杨氏清白堂本《武穆王演义》和嘉靖三十二年(1553)杨氏清江堂本《唐书志传通俗演义》上的题名信息。《武穆王演义》即《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又名《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陈文对此二作的版本信息有具体描述,此处不再赘述。另外,张秀民先生在《明代印书最多的建宁书坊》一文中[3],“据所见明建本牌子及各家公私目录所载”,注录“熊氏忠正堂(熊大木[钟谷]、熊龙峰)”。此条明确称熊大木是“忠正堂”书坊主,且将他与熊龙峰并提。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初,多位学者亲访建阳书坊乡,就熊氏刻书世家的谱系予以查考,对熊大木身份的研究也有了新成果。建阳当地学者方彦寿先生的论文《明代刻书家熊宗立述考》在“熊氏后人”一节[4],对熊大木身份略有考证:虽未见建阳熊氏宗谱有熊大木之名,但宗谱记述熊宗立的曾孙熊福镇号钟谷,此人恰与熊大木生活在同时同地。况且,熊大木多次在通俗小说中自称“鳌峰”或“鳌峰后人”。当初建阳熊氏始祖熊秘在鳌峰山下开设“鳌峰书院”,熊宗立也常自称“鳌峰熊宗立”。方先生认为“熊大木自称‘鳌峰后人即源于此”,熊大木就是熊福镇,号钟谷。九十年代初,陈大康先生《关于熊大木字、名的辨正及其他》一文对熊大木的身份作了更加缜密的文献考索和论证[5]。他认为,“大木”极可能是熊福镇的字。理由是“熊福镇兄弟数人以‘福字排行,而‘镇字据《玉篇》解释是‘重也压也,与‘大木有相通之义。在当时,书坊主刻书以字行世是常有的
事”。熊氏宗谱中虽没有记载熊福镇的生卒年代,但记载他的三哥熊福泰生于弘治九年(1496),卒于隆庆三年(1569)。陈先生的结论是:熊福镇,字大木,号钟谷,成年时期应在嘉靖朝。至此,后来学者对熊大木的身份认定,基本依循以上诸家之说。
关于熊大木身份的考证并没有到此结束。有两处疑点颇值得注意:一是既然张秀民先生提出熊大木是忠正堂书坊主,证据是什么?二是关于熊大木与熊龙峰的关系,是否真如胡士莹先生所推测的,他们是兄弟?一直以来,未见已公开的任何材料直接证明熊大木是忠正堂书坊主。反而文献一致指称熊龙峰才是忠正堂书坊主。孙楷第先生《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卷二《熊龙峰刊小说四种》题记云:
此明坊刊本小说四种,并中型,半叶七行,行十六字,行疏字大,显系同时同地所刻者,《张生彩鸾灯传》题云“熊龙峰刊行”。他本皆无此题,然因其形式全同,知皆熊龙峰一人所刻。余所见龙峰刊书,尚有余泸东校《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封面题“忠正堂熊龙峰锓”,书刻在万历十八年二十年顷。则此亦万历间所刊耳。[6]
如前文所言,胡士莹先生根据此条,同时比勘熊大木编创的两部小说的版本,认为熊龙峰是建阳书坊主,但当时尚无更充分的依据。直至1989年,黄永年先生在《<天妃娘妈传>校点前言》一文中[7],详细介绍了一部在国内早已失传,后发现为日本双红堂收藏的明刻孤本小说《天妃娘妈传》。该书上卷卷首题“南州散人吴还初编,昌江逸士余德孚校,潭邑书林熊龙峰梓”,下卷卷尾有“万历新春之岁忠正堂熊氏龙峰行”。建阳别称“潭阳”,建阳书林也称“潭阳书林”或“潭邑书林”。据此,熊龙峰是建阳书坊主,已经没有任何疑议。胡士莹先生称“钟谷又号鳌峰”,进一步推测熊龙峰和熊大木可能是兄弟关系。这个推测显然是不确切的。“鳌峰”本是地名,后来一度是熊氏书院名。熊宗立也自称“鳌峰熊宗立”,且熊大木还曾自称“鳌峰后人熊钟谷”。关于熊龙峰与熊大木关系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是黄冬柏先生的论文《日本内阁文库所藏<熊龙峰四种小说>考论》[8]。他根据明代书坊时常变换名号和书坊主使用别名的实际情况,大胆推测“熊大木”和“熊龙峰”可能是同一人物的不同署名,“为其他书坊编撰小说时用‘熊大木的笔名,而在自家‘忠正堂刻书时则称‘熊龙峰。但这种推测毕竟也不能排除第三种可能性,即熊大木和熊龙峰既不是兄弟也不是同一人”。笔者认为,黄先生的推论不无道理。既然“鳌峰”不是熊大木的名字或号,那么他和熊龙峰之间的所谓兄弟关系应该是不存在的。鳌在民间传说中是龙的一种,“鳌峰”与“龙峰”意义相近。在熊氏宗谱中,也没有关于熊龙峰的任何记载或与他相关的身份信息。因此,熊大木和熊龙峰极可能是同一人。如果是这样的话,熊大木是书坊主的论断便毋需质疑了。
综合以上关于熊大木身份考证的研究回顾,可以看到,学界前贤依据手中所掌握的文献材料,一步步靠近熊大木这个历史关键人物的原貌。到现在为止,绝大多数学者基本认同前人研究,将熊大木视为明代建阳熊氏刻书世家的家业承继者,甚至其堂号就是“忠正堂”。
二、《熊大木身份新考》的商榷
陈旭东先生的论文《熊大木身份新考》立意新颖,但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述之甚少,其描述的小说版本大多是前辈学者经眼之作,尚难拿出有力证据推翻“熊大木是书坊主”的观点。笔者于此就陈文中几处需要商榷的地方,提出个人的一点看法,以与陈旭东先生商榷。
第一,陈文对熊大木与熊福镇是同一人的观点持怀疑态度。其理由是《建阳余氏宗谱》有舛讹之处,且《(道光)建阳县志》在凡例中称“吾邑诸姓家谱,多不可凭”。笔者认为,这种怀疑可以有,但理由太过牵强。若依此推论,古代小说序跋作伪情况更严重,更不可用作考证材料。但陈文恰恰在后边论述中主要使用小说序文作为其立论依据。修编宗谱本身极其严肃,尽管宗谱中或有对先人功绩的夸大之辞,但大多基本事实还是可以凭信的。陈大康先生经过实地考察后,称《潭阳熊氏宗谱》几经劫难,很可能是世上仅存的孤本了。如方彦寿和陈大康两位先生的考证,熊大木与熊福镇是两个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们的考证依据绝不仅是陈文所说的单凭其号“钟谷”相同,就轻易下此论断。
第二,有研究者据题署“建邑书林熊大木钟谷”来判断熊大木是书坊主,陈文认为不妥。关于“书林”是地名还是书坊名,陈文只是提出肖东发先生的个人看法,认为“两个意思都讲得通,但主要还是讲地名”,并没有举出反例说明。其实在肖先生之前,张秀民先生就提出“明代建阳书坊均自称‘书林……建阳书林或简作‘建邑书林”。笔者认为,如果单独理解“书林”,肖先生的观点应当是成立的。若将诸如“建邑书林”、“潭阳书林”或“潭邑书林”之类的名称置于个人名字之前,则不应只理解为地名,它是有书坊经营者的职业特征包涵在内的。因而,之前研究者的判断,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第三,陈文用大量篇幅对与熊大木有直接联系的八种文献作了版本描述,其中三种藏于日本,陈旭东先生并未见到,其余五种也不是新发现的材料,在各家著述中多有提及。在此基础上,陈文以署名“熊大木”的两篇序文作为重点考查对象。这两篇序文分别为《大宋中兴通俗演义》而作的《序武穆王演义》和为《新刊大字分类校正日记大全》而作的《日记故事序》。鉴于明代小说翻刻盗版情况严重,笔者认为,陈旭东先生以小说序文为主要论证依据,缺乏足够的准确性。这些序文是否真实反映了成书过程,其信息的可信度与熊氏宗谱相较,更值得怀疑。连陈文本身也提供了一条有价值的材料,证明《序武穆王演义》存在熊大木抄袭情况:该文中有百余字内容与早其五年刊行的俞弁《逸老堂诗话》的部分语段相同。
第四,陈旭东先生从两篇序文出发,认为“倘若熊大木是书坊主,自己编纂、重校的畅销书籍却由其他书坊来承担初刻,是不可理解的。只有一种可能,熊氏如三台馆主人所描述的为‘建邑之博洽士,曾开馆授徒,为书坊所知名,屡应书坊主邀请,为书坊主编纂或校勘书籍”。这段论述有几处是不够确切的。首先,小说还未“初刻”,怎知已是畅销书籍?像《大宋中兴通俗演义》这样的章回体通俗小说在当时的出现,是书坊主解决小说稿荒问题的首次大胆尝试。明代书坊规模较小,基本是家族产业,采用“前店后坊”的经营模式,普遍使用雕版印刷技术。这导致刊刻大部头的作品周期长,成本高,有一定市场风险。对刊刻书籍的选择,书坊主有敢于冒险的一面,又有审慎的一面。特别是小说不同于蒙学读物,后者还有固定的消费人群,而小说的消费人群看似庞大,其实是不稳定的。《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在推向小说市场之前,书坊主也没有一定会畅销的绝对把握。其次,书坊主一定会对所谓的畅销书追加投入吗?陈文提到《日记故事》在熊大木重新校注之前,建阳书坊已屡次刊行。这的确可以看作是书籍畅销的表现。但市场是有限的,即使销量再好的书一旦达到饱和,也可能会给小本经营的书坊主带来沉重负担。所以,书坊主没有继续投资刊刻这种所谓的畅销书,并非“不可理解”。正如清末申报馆在《小五义》和《续小五义》的市场销售中价格占优,但当这两部小说售罄后,申报馆并没有加印,而是选择放弃。在继续投入无利可图,甚至可能造成书籍积压亏损的情况下,全身而退不失为明智之举。此外,明代书坊刊刻能力极为有限,在小说市场未达到饱和的情况下,同业竞争并没有那么激烈。熊大木受与自己有姻亲关系的书坊主杨涌泉所请,编创小说后交给杨涌泉刊刻,这也是符合常理的行为。最后,熊大木能称得上是“建邑之博洽士”吗?从目前所见文献来看,此评价完全是言过其实的溢美之辞。从序文的文体性质来看,对著者或编者极尽夸赞是一种惯常的叙述方式,也是对著作的一种宣传策略。如果熊大木学识广博的话,不至于一篇序文都要拾人牙慧,东抄西袭。从小说文本来看,熊大木的文学创作水平还是很低的。陈大康先生在《熊大木现象:古代通俗小说传播模式及其意义》一文中[9],详细分析了熊大木蹈袭前人,多少有点拙劣的小说编创能力。陈文结尾处提出“熊氏对旧本、成说的改编,究竟有怎样的价值,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这本身就是对“熊大木现象”的分析问题。该问题早已为学界研究,有过充分论述。从陈文看,陈旭东先生对“熊大木现象”的理解是狭义的。十多年前,陈大康先生对“熊大木现象”已作过全面的界定和解释:“狭义解释是指负责传播的书坊主越位,进入创作领域,自己编撰或雇佣下层文人代笔;广义内涵是指书坊主干预创作,他们对书稿的取舍甚至会影响创作格局变化.”进而归纳论证了“熊大木现象”出现的意义,此处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熊大木的书坊主身份是前辈学者通过挖掘建阳熊氏宗谱等一系列历史文献材料,比勘版本样式后得出的结论。若要否定这一观点,仅仅依靠小说序文是远远不够的,也是很难作为科学立论根据的。学界前贤既言之凿凿,称熊大木是忠正堂书坊主人,当务之急是要寻找材料,以弄清熊龙峰与熊大木之间的确切关系。这可能才是彻底解开熊大木身份之谜的突破口。在目前还没有更确凿的证据拿出来之前,熊大木是书坊主的观点应该还是成立的,而这本身也并不影响人们对“熊大木现象”的理解和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 陈旭东. 熊大木身份新考[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7): 98?102.
[2] 胡士莹. 话本小说概论[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3] 张秀民. 明代印书最多的建宁书坊[J]. 文物, 1979(6): 77.
[4] 方彦寿. 明代刻书家熊宗立述考[J]. 文献, 1987(1): 237?238.
[5] 陈大康. 关于熊大木字、名的辨正及其他[J]. 明清小说研究, 1991(3): 160?166.
[6] 孙楷第. 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7] 黄永年. <天妃娘妈传>校点前言[J].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1989(4): .
[8] 黄冬柏. 日本内阁文库所藏<熊龙峰四种小说>考论[J]. 中正大学中文学术年刊, 2011(1): .
[9] 陈大康. 熊大木现象: 古代通俗小说传播模式及其意义[J]. 文学遗产, 2000(2): 99?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