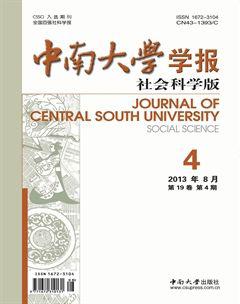民初至抗战后私营传统银行的公司化
收稿日期:2012?11?27;修回日期:2013?07?16
作者简介:孙建华(1966?), 男, 广西百色人, 经济学博士, 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货币金融理论与政策, 金融史.
摘要:抗战爆发后,私营传统银行的公司化已成为普遍现象,这对中小银行充实核心资本、维护信用以及政府稳定战时金融与经济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抗战爆发后私营传统银行的公司化,仍偏重资本的筹集而漠视银行的转机建制及内部治理结构的优化,因而存在经营非审慎、业务投机化、脆弱性高等问题。我国现有不少中小型银行类机构,包括信用合作社及股份合作制银行,公司化、合并及上市仍是这类金融机构提高资本充足率、抵御风险的有效途径。金融监管部门应以史为鉴,引导公司化的中小银行类机构着力改善内部治理结构和管理,审慎经营,而不能仅将公司化和上市作为募股集资或圈钱的手段之一。
关键词:私营;传统银行;公司化;资本
中图分类号:F83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4?0035?05
传统银行公司化不仅是近代中国银行业现代化的重要表征之一,而且是私营传统银行补充核心资本的主要途径。所谓传统银行是指采用独资或股份合伙组织形式、运用传统管理方法、经营存放款、汇兑、货币兑换、发行通用银钱票、贴现票据等信用业务但名称不叫“银行”的金融中介,包括官营的地方官银钱局行号及民营的账局、票号、银号、钱庄等金融中介。所谓新式银行是指采用公司组织、运用现代管理方法、经营存放汇等信用业务名称叫“银行”的金融中介。传统银行公司化即钱庄、票号、银号采用公司组织,在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上向新式银行的趋近。
一、民初至抗战前私营传统银行的
公司化
我国私营传统银行成功改制为银行公司是在民国成立后才出现的。1915年重庆的聚兴诚商号(实为票号)改组为股份两合公司组织的聚兴诚银行,1916年蔚丰厚票号增资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的蔚丰商业银行,此后又有镇江通惠银号(1917年)、上海豫园钱庄(1919年)、北京大成银号(1921年)、长春益发钱庄(1926年)、青岛中鲁钱庄(1926年)等传统银行增资改制为银行公司。
不过在北洋政府时期,传统银行的公司化还是此类金融中介基于业务竞争和发展需要而自发采取的行
动,官方并未强制其改组为公司组织,因而票号、钱庄或银号直接改组为公司、在经营方式上向新式银行靠拢、公开设立门市、存放款利率公开挂牌、改用西洋复式记账的尚不多见,市场力量主导的私营传统银行公司化的规模尚小。
20世纪30年代,钱庄的经营环境恶化,各地发生“钱业剧烈的崩溃”,政府对银钱业的监理也因此变化并加强。为稳固银钱机构的信用及经济金融,南京国民政府于1931年3月28日公布《银行法》,其中第二条规定银行类机构应采用公司组织,“并限合伙组织之银行,于本法施行后三年内变更为公司之组织”。1933年11月9日,伪满洲国政府颁布《银行法》,强制整顿银钱业,并要求所有经营金融业务者,务必在1934年6月末之前提出申请,经两次调查核实后,重新发给营业执照,而且不许独资经营,必须在一年内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对不符合条件者限令关闭。对新设银行,采取严格控制的原则,以其资产信用必须绝对真实可靠为条件,组织形式必须为股份制,资本金按城市规模大小分为4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上和10万元以上四个档次。受此影响,关内外银钱机构改组为公司的现象有所增加。
上海的益丰钱庄、泰和银号,四川的康泰祥银号、和成钱庄,东北的福顺德银号哈尔滨分号、功成玉钱庄等传统银行均在此时增资改制为银行公司。1929年及20世纪30年代,北平也有3~5家传统银钱组织先后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1]。1935年天津的启明银号也
由合伙组织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
此时私营传统银行公司化的数量虽有所增加,但由合伙组织的钱庄、银号改制而成的银行公司大多采用无限责任公司组织,采用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的还很少,这不利于降低投资人的风险并鼓励其扩大银行的投资规模;此外,私营传统银行合组银行公司的事例还很少见,由传统银钱组织独自公司化而成的银行公司资力依然薄弱,信用不稳固。
二、抗战期间私营传统银行的公司化
抗战期间,银钱业营业环境恶化,我国各地仍有部分传统银钱机构基于业务发展、应付挤兑和通胀的需要而主动改制并增资为公司组织。例如福州升和钱庄资本家罗勉候任福州商会会长期间,中南银行老板黄奕住等人即有意与罗氏家族合作,拟将该钱庄改组为公司组织。抗战后期,罗家按《公司法》的规定,以升和钱庄为基础,成立了升和钱庄股份有限公司。后来又计划吸收外股,将升和钱庄改组为福州海南实业银行,该计划已获得国民政府批准,但适值福州第二次沦陷,该钱庄银行化的计划流产。
不过,战时私营传统银行的公司化主要是官方强制推进的结果。在东北沦陷区,伪满当局于1938年3月1日颁布新的《银行法》,申明银行经营的主体应为股份有限公司,最低资本限额为50万元,再度对私营银行进行强制整顿及合并。哈尔滨的11家钱庄、银号因此被合并为公司组织的中泰银行、福德银行、天泰银行、天和银行、瑞祥银行[2]。
1938年12月24日,伪满政府公布新《银行法》,规定设立存款支付准备金制,新式银行资本金必须增至100万元。银行业准入门槛的不断提高,使长春的大多数钱庄纷纷倒闭,最后只剩下功成玉、福记钱、义和公、天和钱、益发钱等少数几家成立较早、实力雄厚的钱庄,并按规定改组成了新式银行。例如1938年5月,功成玉银行重新登记为功成银行;同年底,该银行依据伪满新《银行法》的要求,将其吉林、长春、哈尔滨三处房产作价抵押,同时采取高级职员集资的办法,再次增加资本金50万元,使其达到100万元,另有公积金50万元。功成银行由旧式钱庄改为新式银行后,资金实力增强,1940年在新京设立了吉林总管理处,其业务种类、范围和规模也不断扩大,尤其是汇兑业务剧增。仅1941年,功成银行的汇兑额就高达230余万元,而同年官办的伪中央银行吉林分行、伪中央银行吉林东关支店和伪兴业银行吉林支店的汇兑总额仅为13万元,是功成银行汇兑总额的5.6%。功成银行发展成为当时长春最大的两家民营银行之一。
在华北沦陷区如天津、北平、济南等地,部分私营传统银行也在日伪政权的强制下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
1937~1939年间,天津的振兴长、大德恒、华兴、益恒昌银号为厚集资本以应付抗战初期的信用收缩和存款挤提而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1941年12月11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财务公署公布《金融机关管理规则》,命令银钱业增资改组,规定“非实收股本50万元(联银券)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得经营”银钱业[3],经营银钱业者须一律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统称银号,资本不足50万元的部分限6个月交足,报经伪财务总署核准后再发给营业执照。1944年又实行第二次增资,规定银号资本最少须300万元。受此影响,天津有60多家钱庄因为股本达不到法定的最低资本限额而被迫停业,余下的振兴长、大德恒、华兴、益恒昌、广源、正丰裕、敦昌、鸿记、庆聚、广利、信记、老恒记、宝生、同生祥、义聚、谦丰、庆益、福康仁、瑞源永等银号和豫慎茂钱庄天津分庄,则按规定在战时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组织[3]。
北平在沦陷前有43家钱庄(当时称银号),沦陷期间,由于时局动荡和营业困难,加上日伪政权实施《金融机关管理规则》,强迫钱庄增资改制,所以有近一半的钱庄被迫歇业清理;而另外的22家钱庄按规定增资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并更名为银号后继续营业,其中的两家还直接更名为银行。例如山东梁姓商人于1906年创办的福顺德银号,注册资本银2万两,专营京饷汇兑业务,该银号在烟台设总庄,在北京、哈尔滨、长春、吉林、齐齐哈尔、大连、黑河、青岛、济南、天津、龙口、黄县及胶东各县设立分庄或寄庄。1942年12月,日伪政权强迫福顺德银号增资为伪联银券200万元,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并将北平分号改为总号;同年,日伪政权还迫令晋汇丰钱庄增资至伪联银券50万元,并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祥瑞兴银号、聚义银号、振大兑换所、永泰公银号也在该年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祁县乔氏独资创办的大德恒钱庄在1932年将总号迁至北平,1937年改组为股份合伙组织,以扩充资本。1943年日伪政权强制大德恒钱庄增资至伪币50万元,并采用股份有限公司组织,更名为银号;同年,合伙组织的义聚银号也被迫增资至伪币50万元并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
1944年12月,日伪政权再度对北京的金融业进行“编制整理”,要求银钱组织申请增资,又有部分银号因无法按规定增资改制而被迫歇业,而厚生银号等33家银号增资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后继续营业,其中6家银号还直接更名为银行公司,例如福顺德银号就被迫于1944年再次增资至伪联银券1 000万元并更名为福顺德银行,各分号改为分行。1945年6月,日伪政权再次令钱庄增资,晋汇丰等部分钱庄因未能满足日伪政权增资要求而被勒令停业整理。至此,北平共有公司组织的银号85家,除了上述公司化的银号之外,还有新设的63家公司组织的银号。
在山东,1941年末开始的银钱业首次增资改组期间,各地存续的银号还有67家,其中济南的银号由39家减为28家,烟台由48家减为15家,青岛剩下9家;在周村,除5家钱庄转为地下钱庄之外,其余钱庄因无力增资改制而全部垮台;潍县银号剩1家,济宁剩3家,德州剩3家,博山剩2家,威海剩1家。其实这些留存下来的山东银号都已是公司组织,只是其名号仍叫“银号”而不是“银行”罢了。在1944年开始的银钱业第二次增资改制期间,济南、烟台、青岛的几家银号不仅改组为公司,而且还直接更名为银行,其中烟台的福顺德银号在1942年改组为股份公司后,在账目上实行新式簿记账,优化业务人员的结构,吸收了从新式中学或商业专科学校毕业的管理人员。该银号的资力、信用、分支机构及信用业务均有扩充,个人存款也日益增多并得以营业至1950年6月才歇业,成为烟台市最后歇业的私人钱庄[4]。
在上海沦陷区,传统的银钱组织也在汪伪政权强制和市场压力下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组织。1939~1941年间上海的福利、光裕、同心钱庄由合伙组织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组织。1942年8月,汪伪政府财政部颁发《管理金融机关暂行办法》,规定凡是采用合伙组织的金融机构,一律要在1943年8月20日以前改组为公司。1943年7月1日汪伪政府财政部公布的《修正银行注册章程》第三条重申“银行应为公司组织”,股份有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两合公司组织的银行,其资本至少须达六百万元;无限公司组织的银行,其资本至少须达二百万元。1943年汪伪政权要求金融机构重新登记,并限令原来合伙组织的钱庄一律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允许投资人不再负无限责任,以使钱庄出资人的投资风险得以降低,从而鼓励其投资银行业。
为募集继续营业必需的法定资本金,不仅1942年以后上海新设立的钱庄纷纷采用股份有限公司组织形式,而且上海“硕果仅存的20余家著名汇划钱庄,也均次第改为股份有限公司组织”,例如1943年,上海著名的福源钱庄就在官府的要求下从无限责任公司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继之一般老庄为适应环境起见,也纷纷改组为有限公司”,谦泰、和泰、永泰、宝康等银行公司就是由钱庄改组而成的。
截至1944年初,上海尚未改制为公司的汇划钱庄只剩下元盛、均昌、义昌3家,1944年以后上海的汇划钱庄均为公司组织了,“于是资本额也随之扩大”[5]。
1942年上海有钱庄54家,资本总额达3 279.7万元伪中储券;而在1943—1945年分别增至193家、216家和229家,资本总额分别增至2亿5 517.6万元、8亿8 436万元、25亿9 810万元伪中储券,平均每家钱庄的资本额也从1942年的60.74元伪中储券增至1943—1945年的132.2万元、409.4万元、1 134.5万元伪中储券[6]。以上史实表明,在战时高通胀背景下,上海钱庄增资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对其充实资本金、稳固信用和服务经济社会,在客观上是有利的。
在后方地区,战时日趋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钱庄的资本大为缩水,以重庆为例,“战前渝市各钱庄最低资本五万元,最高亦不过七十万元,抗战以后各钱庄一再增高资本额,除已改组银行者不计外,最高资本额五百万元,最低五十万元;……三十四家钱庄之资本总合共计为五千一百三十万元。一般言之,其资力显见微弱”,不仅抵御风险的能力降低,而且难以满足经济建设内生的资金需要。为使钱庄出资人在法律上承担的债务责任从无限转为有限,投资风险降低而投资意愿得以增强,“三十三年春以后,各钱庄均纷纷酝酿增资改组……”,1938—1943年间,重庆有和成、开源、同心、永利、光裕、大夏、大同、泰裕、胜利、复华、复礼、福钰、聚康、永成、永美厚、谦泰豫等16家钱庄改组为公司或更名为银行。
由于采用股份有限公司组织之后,钱庄增募股本相对容易,加上战时通货膨胀严重,投资者创办钱庄所需的实际资本事实上并不高,所以独家钱庄改制而成以及新设的小型银行公司充斥银钱业。这些小银行信用不稳固,业务投机化,脆弱性高。“财政部鉴于一般钱庄资本薄弱,……经营稍一不慎,必致波及整个市场”,遂在1943年3月通令重庆以及各地的钱业公会:凡欲增资改组为银行者,须合并3家钱庄以上可予批准外,一概不得单独改组。考虑到恶性通货膨胀对银行资本的侵蚀,为充实改制钱庄的资本金,稳固银行信用,国民政府财政部“爰于三十三年春增订钱业改组银行办法四项,并规定渝市钱庄改组银行至少须实收资本一千万元,惟如合并钱庄三家以上改组银行者,得不受上述资本额之限制”。
虽然国民政府财政部遏制小钱庄独自改组为银行公司的目的未能完全奏效,但银号钱庄改组为银行公司的办法的出台本身就反映了战时后方地区银钱机构
纷纷公司化的史实。据统计,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仅重庆地区就有25家钱庄增资改组为银行公司[7];其他后方城镇也有传统银钱机构改组为银行公司的事例,例如成都的福川银号,昆明的兴文官银号、永丰银业公司、益华银号、光裕钱庄、云南矿业银号,衡阳的鸿兴银号等也在战时改组为银行公司[8]。
综上所述可知,战时各地钱庄公司化趋势的加强,既是战乱和高通胀时期银钱机构生存和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银行监管制度变迁及行政力量强制推进的结果。此时私营钱庄的公司化确实有助于这个时期银行信用及其业务的维持和发展。例如永利银行是由永利钱庄于1940在重庆改组成立的,该行成立后,资力和营业机构得以扩展,1943年7月15日在西安设立分行,同年11月在宝鸡设办事处。总部设于重庆的正和钱庄在1944年6月改组为正和银行之后,资本、分支机构和业务均有扩展,1947年该行在重庆设总管理处,而后在广州、重庆、上海、香港、昆明地设分行,业务规模及空间范围也随之扩大。
三、抗战后私营传统银行的公司化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传统银钱业组织进行了清理整顿,重新登记。1947年9月,国民政府公布新的《银行法》,其第一条强调银行要“依公司法及本法组织登记”为公司。而该银行法第七章第九十四条申明,凡按各地钱业习惯经营商业银行业务者,为钱庄,并为银行之一种。第九十八条规定,钱庄改组为银行时应按其业务及公司种类依第二十七条之规定为变更之登记。“与经营类似钱庄之银号票号及其它名称之银钱业准用之”。
1945年8月—1948年8月,法币发行增长1 191.7倍,物价上涨4 927 000倍,银钱机构资本缩水,资金短缺,业务和收入萎缩,经营风险加大,急需补充资本。由于股份有限公司比两合公司、无限公司和股份两合公司在募股集资上更有优势,所以在1946—1948年间,曾因华北沦陷而停业的传统银钱组织纷纷要求复业时,大多在复业后即自行依法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少数则在政府要求下按新银行法的规定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
以北平为例,1945—1948年间,在注明资本组织形态的46家银钱组织中,有45家为股份有限公司,占总数的98%;而在这45家股份有限公司中,又有43家是从传统的独资、合伙组织增资改制而成的。例如信成记银号,1929年成立时为合伙组织,资本为法币1.2万元,1947年复业后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增至法币1亿元。济兴兑换庄,1934年由沈鸿烈独资创办,资本为大洋3 000元;1935年,该庄更名为济兴银号,改由张凤鸣和耿希孟合伙经营,资本增至法币8万元;1947年4月,济兴银号北平总号又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并增资至法币1亿元[1]。
天津、上海等地复业的银钱机构也纷纷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天津至少有22家银号复业后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而上海至少有23家钱庄复业后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改制后,这些银钱机构的资本规模均有显著的增加,至少在1948年8月以前,公司化使得改制银行的账面资本得以增加,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银行实际资本因通胀的侵蚀而缩小的程度。
上述事实表明,各地私营传统银行组织制度的变革与其资本金的扩充是联系在一起的。不难看出,增资扩股、稳固信用、维持或扩大业务规模,仍是抗战胜利后及高通胀时期私营传统银行公司化的主要目标。
战后私营传统银行公司化的普及表明,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均已认可银行公司比独资或合伙组织的传统银行更有发展优势,社会已普遍接受有限责任的银钱机构的信用,均以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我国银钱机构组织制度变革的目标模式及增资扩股的有效途径,我国私营传统银行公司化的进程至此已基本完成。虽然该进程的完成是在市场压力下传统银钱机构自愿选择及行政力量推进的共同结果,但后者的作用显然更大。
1948年后的恶性通货膨胀使得私营传统银行公司化的资本补充效应化为乌有。1948年8月国民政府推行金圆券改革,规定1金圆券折合300万元法币;1949年7月国民政府恢复银本位制,推行银元券,规定1银元券折合5亿元金圆券。照此比价换算,1银元券折合1 500万亿元法币。至此,除少量金银、外汇形态的资本之外,诸多银行包括改制银行的货币资本的账面价值已荡然无存。
四、小结
民初至抗战后特别是抗战期间私营传统银行的公司化,虽在充实银行资本、维护银行信用、稳定金融与经济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过于偏重资本的募集而漠视银行的转机建制及公司治理结构的优化,因而在通胀恶化及政府对银行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就存在经营非审慎、业务投机化、脆弱性高等问题。我国现有大批中小型银行类机构,包括信用合作社及股份合
作制银行,在金融市场开放及竞争激化的背景下,公司化、上市及合并仍是这类金融机构提高资本充足率、抵御风险及稳固信用的有效途径。金融监管部门应以史为鉴,引导和规范中小银行类机构的公司化及合并重组,促其认真筛选和引进战略投资者、着力优化内部治理结构、改善管理、审慎经营,在此基础上改善银行公司的素质及其经营绩效,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而不能将公司化和上市仅仅作为其募股集资或圈钱的手段之一。
参考文献:
[1] 刘兰兮. 近代北京传统银钱组织的变迁[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6: 98.
[2] 哈尔滨市志编纂委员会. 清末、民国时期金融业[DB/OL]. [2012?04?22]. http://dqw.harbin.gov.cn/.
[3] 联合征信所平津分所调查组. 平津金融业概览[M]. 天津: 联合征信所平津分所, 1947: J1?J58.
[4] 山东省史志办. 日伪统治时期山东私营银钱号[DB/OL]. [2012?04?22]. http://sd.infobase.gov.cn/.
[5] 谢菊曾. 民元来上海之钱庄业[A]. 民国经济史(银行周报三十周纪念刊)[C]. 上海: 银行周报社, 1948: 53.
[6]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 上海钱庄史料[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0: 312?313.
[7] 交通银行总管理处. 金融市场论[M]. 上海: 交通银行总管理处, 1947: 100?107.
[8] 隗瀛涛. 近代重庆城市史[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1: 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