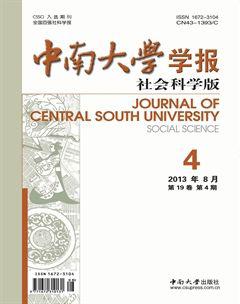论汤显祖“为情作使,劬于伎剧”思想的成因
收稿日期:2012?12?02;修回日期:2013?04?29
作者简介:储著炎(1975?),男,安徽岳西人,文学博士,安庆师范学院黄梅剧艺术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戏曲史及戏曲理论.
摘要:达观禅师之所以提出“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这一佛学论断,其用意在于劝说汤显祖以理破情,进而皈依佛法。在佛学层面上,汤显祖虽然认可达观的这一说法,但是两人在人生哲学、文艺观念等方面存在着的诸多差异,使得汤显祖对于情理问题有着不同于达观的独特思考。根植于内心深处的儒家救世情结,加之达观实践人格的实际影响等等因素的交互,最终坚定了汤显祖“为情作使,劬于伎剧”的人生道路。
关键词:汤显祖;达观;为情作使;劬于伎剧;禅学;儒家救世情结
中图分类号:I2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4?0187?04
达观禅师对汤显祖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在情理问题上。达观曾经向汤显祖提出“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的佛学主张,引起了汤显祖的共鸣。在《寄达观》中,汤显祖曾说:“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使我奉教以来,神气顿王。”[1](1351)楼宇烈先生认为:“汤显祖对达观‘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的论断还有其自己的理解,不一定完全符合达观的原意。但其中受到达观禅学思想的一定影响,这也是无疑的。”[2](162)楼宇烈先生的观点,是比较中肯的。在情、理问题上,汤显祖确实受到达观佛学思想的影响,但显然又有着他自己的理解。那么,达观所谓的“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这一论断的真实内涵是什么呢?汤显祖对于达观所提出的情理问题又有着怎样的看法?汤显祖的情理观在何种程度上受到达观佛学思想的影响?本文试图以汤显祖与达观之间的交往与信笺往来入手,以期探讨这样一些问题。
一
达观即真可禅师,晚号紫柏,明代四大高僧之一。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将他与李贽并列,推崇两人为当时思想界的“二大教主”。其云:“紫柏老人气盖一世,能于机峰笼罩豪杰。”“至辛丑,紫柏师入都,江左名公,既久持瓶钵,一时中禁大珰趋之,如真赴灵山佛会。”[3](691)达观与汤显祖交情很深,遇合甚奇。汤显祖在《答邹宾川》中云:“弟一生疏脱,然幼得于明德师,壮得于可上人。”[1](1449)“可上人”即达观。在《莲池坠簪题壁二首》诗前小序中,汤显祖说到他与达观的遇合奇缘:“予庚午(隆庆四年,1570)秋举,赴谢总裁参知余姚张公岳。晚过池上,照影搔首,坠一莲簪,题壁而去。庚寅(万历十八年,1590)达观禅师遇予于南比部邹南车郎舍中,曰:‘吾望子久矣。因诵前诗,三十年事也。师为作《馆壁君记》,甚 奇。”[1](577?578)万历十八年十二月,汤显祖任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时,在江西同乡南京刑部广东司署员外郎主事邹元标处正式结识达观。此前达观禅师游方偶见汤显祖的题壁诗,此次相晤,达观因诵前诗,二人神交既久,此后终身莫逆。
徐朔方先生曾说:“对汤显祖思想影响最深的人莫过于禅宗大师达观。”[1](4)情理问题是汤显祖思想的集中体现,是汤氏哲学观、人生观、文艺观的核心问题。考察汤显祖的情理观,应该联系汤氏与达观之间的交往,两人曾经针对情、理问题展开过一场探讨。万历戊戌(二十六年,1598)三月,汤显祖自遂昌知县任上弃官家居。是年秋,汤氏为《牡丹亭》撰写《题词》,《牡丹亭》创作完成。是年岁除,达观来到临川。达观在《礼石门圆明禅师文》中曰:“万历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予自庐山归宗寺,挈开先寿公,与吴门朗驱乌,来临川。”[4](885)汤氏《梦觉篇序》亦云:“戊戌岁除,达公过我江楼,吊石门禅,登从姑哭明德先生往反。己亥上元,别吴本如明府去栖罏峰,别予章 门。”[1](564)达观万历二十六年岁除来到临川,二十七年上元离开临川。他此次临川之行将汤氏法号寸虚改为广虚,并为是年殇逝的汤氏爱子西儿作《悼西儿名序》。其时《牡丹亭》已经完成。达观临川之行,应该
知道《牡丹亭》的创作,但他显然对汤氏“为情作使,劬于伎剧”不满[1](1221),所以他才在离开临川后寄来一封长信,即《与汤义仍》其一。达观在信中说:“真心本妙,情生即痴,痴则近死,近死而不觉,心几顽 矣。”[4](1039)他希望汤氏远情近理,明性诎情,因为“理明则情消,情消则性复,性复则奇男子能事毕矣,虽死何憾焉!”[4](1040)在情、理问题上,达观尊理诎情,主张以理破情。在他看来,汤氏给他的遗憾在于“昧性而恣情”[4](1039)。他认为汤显祖“受性高明,嗜欲浅而天机深,真求道利器” [4](1039),希望能够淡薄世缘,因为“世缘一浓,灵根必昧”。[4](1041)
针对达观的来信,汤显祖在回信《寄达观》中云:
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真是一刀两断语。使我奉教以来,神气顿王。谛视久之,并理亦无,世界身器,且奈之何。以达观而有痴人之疑,疟鬼之困,况在区区,大细都无别趣。时念达师不止,梦中一见师,突兀笠杖而来。忽忽某子至,知在云阳。东西南北,何必师在云阳也?迩来情事,达师应怜我。白太傅、苏长公终是为情使耳。[1](1351)
据徐朔方先生《寄达观》文后笺证,此文作于万历二十六年汤显祖自遂昌知县弃官以后。在《紫柏老人全集》中有《与汤义仍》信笺两则,《其一》所谈问题与汤氏《寄达观》内容相应,所以汤氏《寄达观》应是对达观《与汤义仍》(其一)的回复。汤氏弃官家居后的心情显然很是矛盾,他在《达公来自从姑过西山》诗中云:“厌逢人世懒生天,直为新参紫柏禅。”[1](563)在入出与出世的抉择中,汤氏的思想出现了危机。在此之前,即汤显祖在遂昌知县任上时,达观就历尽千难万险,来到遂昌。他之所以来到遂昌,其实就是劝说汤显祖了却尘缘,忘情人世。在遂昌,汤显祖陪达观游览唐山古寺,达观有诗云:“踏入千峰去复来,唐山古道足苍苔。红鱼早晚迟龙藏,须信汤休愿不灰。”[5](32)他将汤显祖比作唐末五代著名画僧贯休,希望他能精研佛学,了却人世情缘。达观的临川之行,二人更是“无情当作有情缘,几夜交芦话不眠” [1](580)。达观的临川之行,加之别后的信笺劝说,使汤显祖开始“新参紫柏禅”。夏写时先生认为:“达观以理破情实有之,汤显祖以情破理则未必。他只用‘谛视久之,并理亦无这种禅家习用的机锋轻轻一点,就把达观视情、理不两立的偏执性指点出来了。”[6](261)其实,从汤氏“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真是一刀两断语”之语来看,他并没有认为达观情、理不两立就是偏执。可以说,汤显祖也一直没有放弃对“理有情无”的追求。汤显祖曾说:“达观氏者,吾所敬爱学西方之道者也。”[1](1053)在《南柯梦记题词》中,汤显祖曾说:“梦了为觉,情了为佛。”[1](1157)在晚年所作《续栖贤莲社求友文》一文中,他曾经反省自己:“岁之与我甲寅者再矣。吾犹在此为情作使,劬于伎剧。为情转易,信于痎瘧。时自悲悯,而力不能去。想明斯聪,情幽斯钝。情多想少,流入非类。吾行于世,其于情也不为不多矣,其于想也则不可谓少矣。随顺而入,将何及乎?应须绝想人间,澄情觉路,非西方莲社莫吾与归矣。”[1](1221) 这种思想其实与达观的佛学思想是相一致的。
二
达观的情理思想虽然影响了汤显祖,但汤显祖对于情理问题显然有着自己的理解与阐释。在回信中,汤显祖有意提到了达观的“痴人之疑”与“疟鬼之困”,来为自己“为情作使,劬于伎剧”的行为辩解。所谓达观的“痴人之疑”,据德清《达观大师塔铭》言:“一日闻僧诵张拙《见道偈》,至‘断除妄想重增病,趋向真如亦是邪,师曰:‘错也。当云:‘方无病,‘不是邪。僧云:‘你错,他不错。师大疑之,每至处,书二语于壁间,疑至头面俱肿。”[4](627)所谓达观的“疟鬼之困”,据达观自述:“往年抱疟松云间,来慈偕其弟匡石,多方调治。予性不耐服药,复恣情所爽口者,故疟鬼得肆焉。”[4](879)在情理问题上,达观主张:“夫玄黄无咎,咎生于情。情若不生,触目皆道。故情有理无者,圣人空之;理有情无者,众人惑焉。”[4](708)“理之攻情,何情不破;情之攻理,谁当其攻。”[4](1008)在汤氏看来,“以理破情”很难,就是达观自己,“无情无尽恰情多[1](581),也不能做到无情无咎,可见“以理破情”何其难哉!所以他才以达观“有痴人之疑,疟鬼之困,况在区区”之语来为自己不能“忘情”辩解。
可以说,根源于儒家仁孝的入世情结使得汤显祖最终未能做到忘情尘世,逍遥世外。汤氏“情痴一种,固属天生”[7](34),在他的思想深处,始终没有放弃对有情尘世的执著。尽管他“平生只为认真,所以做官做家,都不起耳”[1](1519),难免“厌逢人世”,但他始终不以得失为念,“为邑吏有声,志操完洁,洗濯束缚,有用与行矣”。[1](2584)虽然他弃官家居后以“茧翁”、“义仍”自号,但他始终关注着有情人世,以情痴自许;虽然在汤氏晚年,确有向佛家皈依的倾向,如在汤氏逝世前二年,他倡建栖贤莲社,试图皈依佛门,但汤氏此举因母丧未果。汤显祖“先慈之哀,继之先严。创钜痛深”[1](1540)。蒋士铨《临川梦自序》谓汤显祖:“白首事亲,哀毁而卒,是忠孝完人也。”[8](209)晚年的汤氏,虽然有出世之想,但儒者的仁孝,使他终不能忘情尘世,超然物外。
达观在来信中告诫汤显祖“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其真实的用意还在于想让汤显祖斩断“情”的羁累,与世浮沉。达观所谓的理与情分指“无我”与“有我”,他说:“理无我而情有我故也。无我则自心寂然,有我则自心汩然。寂然则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汩然则自心先浑亦如水浑不见天影也,况能通天下之故哉?圣人知理之与情如此,故不以情通天下而以理通之也。”[4](1008)他向汤显祖宣扬“以理破情”,意在劝说汤显祖破除“情”的执著,做到“无情无我”以与世浮沉。其时汤氏官场的失意、爱子的殇逝,种种逆境,在达观看来,此是“年来世缘,逆多顺少,造物不忍精奇之物,沉霾欲海,暗相接引,必欲接引寸虚了此大事”。[4](1041)但汤显祖认为,真正做到“忘情”太难,况且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中,“与世浮沉”更难,所以他才屡次劝告达观披发入山,远离祸场。这从达观《与汤义仍》(其二)信中可以看出,其云:
屡承公不见则已,见则必劝仆,须披发入山始妙。仆虽感公教爱,然谓公知仆,则似未尽也。大抵仆辈,披发入山易,与世浮沉难。公以易者爱仆,不以难者爱仆,此公以姑息爱我,不以大德爱我。昔二祖与世浮沉,或有嘲之者,祖曰:“我自调心,非关汝事。”此等境界,卒难与世法中人道者,惟公体之,幸甚。……仆一祝发后,断发如断头,岂有断头之人怕人疑忌 耶?[4](1042)
其实,当时劝告达观披发入山、远离祸场的不止汤显祖一人。在万历三十一年达观因为 “妖书”事件死于狱中之前,“门弟子皆知都下侧目,师相继奉书劝出。开侍者刺血具书,隐去”。[5](146?147)可以说,汤显祖是理解达观所提出的“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思想的本意,但他不认可达观与世浮沉的说法,因为在当时那个世道,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据陆符《紫柏尊者传略》记载:“上以三殿工开矿税,中使辈出。有李道者初奏,南康守吴宝秀抗旨逮治,其夫人哀愤投缳死。师闻之曰:‘良二千石为民请命死,其妻自且不免,时事至此乎!遂入都门营救。”[5](146)面对旁人的百般劝告,达观辄云:“断发已如断头,今更有何头可断。”[5](147)他的这种不惜以身命弘法的救世精神,深深地震憾了汤显祖。万历三十九年,汤显祖在为友人汤宾尹《睡庵文集》所作的序中写道:“道心之人,必具智骨;具智骨者,必有深情。”[1](1074)这既是再次阐明真正做到“无情”太难,更是借作序这一机缘,对达观悲天悯人的智骨深情所作的一次凭吊。
三
正是因为达观“情有理无”的佛学启迪,加之达观与世浮沉、不惜断头的救世深情,让汤显祖对于情理问题有了更为透彻的了解,即世外之法虽然追求无情,但“人生而有情”[1](1188),世内之法重在有情,尤其是达观令人感伤的不幸遭遇,让汤显祖认识到“情”之于人世的弥足珍贵,更加坚定了“为情作使,劬于伎剧”的决心。汤显祖在《清莲阁记》中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话:
世有有情之天下,有有法之天下。唐人受陈、隋风流,君臣游幸,率以才情自胜,则可以共浴华清,从阶升,娭广寒。令白也生今之世,滔荡零落,尚不能得一中县而治。彼诚遇有情之天下也。今天下大致灭才情而尊吏法,故季宣低眉而在此。假生白时,其才气凌厉一世,倒骑驴,就巾拭面,岂足道哉。[1](1174)
达观的不幸遭遇,其实就是当时社会“灭才情而尊吏法”的真实写照。为了将“有法之天下”改造成“有情之天下”,汤氏“劬于伎剧”,努力从事戏曲创作。他生前创作的戏曲作品应该不止现存这些,据钱谦益《汤遂昌显祖传》记载,汤氏之子开远“好讲学,取义仍续成《紫箫》残本及词曲未行者,悉焚弃 之”。[1](2587)汤显祖之所以“为情作使,劬于伎剧”,原因在于他认为戏曲可以:
使天下之人无故而喜,无故而悲。或语或嘿,或鼓或疲,或端冕而听,或侧弁而咍,或窥观而笑,或市涌而排。乃至贵倨弛傲,贫啬争施。瞽者欲玩,聋者欲听,哑者欲叹,跛者欲起。无情者可使有情,无声者可使有声。寂可使喧,喧可使寂,饥可使饱,醉可使醒,行可以留,卧可以兴。鄙者欲艳,顽者欲灵。可以合君臣之节,可以浃父子之恩,可以增长幼之睦,可以动夫妇之欢,可以发宾友之仪,可以释怨毒之结,可以已愁愤之疾,可以浑庸鄙之好。然则斯道也,孝子以事其亲,敬长而娱死;仁人以此奉其尊,享帝而事鬼;老者以此终,少者以此长。外户可以不闭,嗜欲可以少营。人有此声,家有此道,疫疠不作,天下和平。岂非以人情之大窦,为名教之至乐也哉。[1](1188)
《礼记·乐礼》云:“礼乐之极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穷高极远而测深厚。”[9](1097)汤氏将戏曲功能描述得无以复加,其作用简直可以凌驾于儒家礼乐的教化功能之上,这使我们想起了他的“至情”思想。在《牡丹亭·题词》中,汤显祖曾对“至情”有过一番阐释:“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1](1153)在汤显祖那里,戏曲的教化功能之所以并驾乃至凌驾于儒家礼乐,原因就在于一个“情”字。“至情”既然可以使生者死、死者生,那么如果“因情作剧”,自然会使戏曲因为这“至情”的作用而实现它的功能最大化。晚明祁彪佳在《孟子塞五种曲序》中曾说:“盖诗以道性情,而能道性情者,莫如曲。……自古感人之深而动人之切,无过于曲者 也。”[10](621)在所有的文学体裁中,只有戏曲才是“情”的最好载体,所以汤显祖才从“情”的人世本体意义与形而下的社会功用出发,将戏曲的救世功能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
值得注意的是,在文艺观上,达观认为:“大概立言者,根于理不根于情,虽圣人复出恶能驳我!”[4](1008)但在汤显祖看来却是“无情师印有情文” [1](682)。在《耳伯麻姑游诗序》中,汤显祖说:“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天下之声音笑貌大小生死,不出乎是。因为憺荡人意,欢乐舞蹈,悲壮哀感鬼神风雨鸟兽,摇动草木,洞裂金石。其诗之传者,神情合至,或一至焉;一无所至,而必曰传者,亦世所不许也。”[1](1110?1111)左东岭先生认为汤显祖所说的“情”,“从文学思想上讲,此情是指文学产生的原动力以及感化人心的艺术力量,它是文学得以产生并传之久远的决定思想因素,同时也是它能够发挥教化百姓、和谐社会的根本原因。”[11]汤显祖以文艺为阵地,以戏曲为号角,充分利用戏曲教化人心的便利,努力实践他的救世决心。作为一代佛学大师的达观,自然不可不讲性、讲理;但是作为文学家、戏曲家的汤显祖,他的人生实践与艺术天地却少不了情的参与,也正是因为一个“情”字,成就了他的理想人格与艺术辉煌。
有学者认为:“汤显祖‘为情作使,劬于伎剧,为
情转易达到‘信于痎虐的程度,正说明他是极大地关注感性个性生命的本真存在状态的。这与他的道气论、贵生论、主动的认识论是一致的,也是明末重自然人性时代精神的反映。”[12](205)可以说,从社会文化思潮角度来看,汤显祖的“劬于伎剧”,是那个时代重自然人性精神的反映;从内在因素与深层视角来看,正是因为达观“情有理无”佛学思想的启迪,以及达观不惜以身命弘法这一实践人格的影响,加之根植于内心深处的儒家救世情结,等等因素的交互,最终坚定了汤显祖“为情作使,劬于伎剧”的人生道路。
参考文献:
[1] 汤显祖. 汤显祖全集[M]. 徐朔方笺校.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9.
[2] 楼宇烈. 汤显祖哲学思想初探[C]//汤显祖研究论文集.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4.
[3] 沈德符. 万历野获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4] 紫柏尊者全集[C]//藏经书院编. 卍续藏经: 第126册. 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994.
[5] 紫柏尊者全集[A]. 藏经书院编. 卍续藏经: 第127册[C]. 台北: 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994.
[6] 夏写时. 论中国戏剧批评[M]. 济南: 齐鲁书社, 1988.
[7] 吕天成. 曲品校注[M]. 吴书荫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8] 蒋士铨. 蒋士铨戏曲集[M]. 周妙中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93.
[9] 李学勤主编. 十三经注疏: 礼记正义[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10] 孟称舜. 孟称舜集[M]. 朱颖辉辑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11] 左东岭. 阳明心学与汤显祖的言情说[J]. 文艺研究, 2000(3): 98?105.
[12] 邹元江. 汤显祖的情至本体论[C]//汝信, 张道一, 主编. 美学与艺术学研究: 第二集. 南京: 江苏美术出版社,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