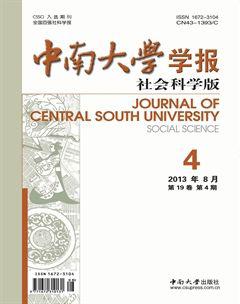略论唐人情恋小说中的寺庙意象
收稿日期:2013?02?19;修回日期:2013?04?25
基金项目:201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唐人小说与民俗意象研究”(11YJA751079)
作者简介:熊明(1970?),男,四川南充人,文学博士,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小说.
摘要:唐人的情恋小说,无论是人间普通男女的情恋故事,还是人与异类的情恋故事(即人神、人鬼、人妖情恋故事),其中多有寺庙意象,然历代研读唐人小说者几无有论及。细审之,唐人情恋小说中的寺庙意象,实与寺庙在唐人生活特别是士人生活中的特殊角色有关。寺庙意象是唐人情恋小说中独特的艺术构成,或者担负着暗示小说人物身份的作用,或者作为小说故事的主要空间场景,或者在小说故事的情节布设中承担联接功能,在叙事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寺庙意象的大量存在,也为唐人情恋小说增添了浓郁的民俗风情,形成其别样的审美意蕴。
关键词:唐人情恋小说;寺庙与寺庙意象;艺术呈现;小说功能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4?0165?07
在唐人小说中,如果就题材内容而论,情恋主题的表达无疑是最重要的题材类型之一,并因此造成了情恋小说的大量出现。唐人情恋小说中的情恋故事,不仅发生在人间普通男女之间,也发生在人与神仙鬼魅之间,且男主人公多为士子,女主人公则主要是妓女、女神、女鬼、女妖等。检读唐人小说中的这些情恋故事,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在许多情恋小说中都有寺庙出现,即在情恋故事中往往有寺庙意象存在,且在人神、人鬼、人妖情恋故事中尤其显著,这一现象值得注意。
一、寺庙:唐人情恋小说生产的
现实基础
寺即佛寺。汉末以来,随着佛教在中土的传播与流布,作为佛教僧侣与信众宗教活动中心的佛寺随之大量兴建。至唐代,由于统治集团三教并重,佛教在有唐三百年间十分昌隆,是上至公卿、下至庶民的普遍信仰。因而唐代的佛教文化十分发达,佛寺之创建遍及山川都邑。庙即神庙。自古以来,中国民间各地就供奉着许多神祗,他们被赋予执掌一事或护佑一方的职能,因而大大小小的神庙遍布各地,如岱庙、中岳庙、南岳庙、北岳庙等等。神庙与佛寺大略相类,故常统称之为寺庙。在唐代,随处可见的寺庙自然与普通民众的生活密切关联。
寺庙常常是唐人社群民俗活动的重要场所。在唐人的日常生活中,有许多习惯性的社群民俗活动,比如节庆。唐代节日众多,不仅有元日、立春、人日、上元、晦日、中和、寒食、清明、上巳、端午、七夕、中元、中秋、重阳、下元、冬至、腊日、岁除等普通节日,还有佛诞日、皇帝诞日及老子诞日等特殊节日。且每一个节日都有一些特殊的社群性民俗节庆活动,如上元赏灯、中元观灯、寒食秋千、清明斗鸡、七夕乞巧、中秋玩月,除岁舞傩等。而每到节日,寺庙常举办节庆活动,吸引大量民众游观。《传奇·颜濬》即云:“中元日,来游瓦官阁,士女阗咽。”[1](102)同时,寺庙为了吸引士人,常广植花木,善为景观。《剧谈录》即云:“京国花卉之晨,尤以牡丹为上,至于佛宇道观,游览者罕不经历。”又云会昌中,院主老僧将宝惜栽培近二十年的一窠殷红牡丹向众人展示,结果被强挖而去之事。[2](1481)《霍小玉传》亦言:“时已三月,人多春游,生与同辈五六人,诣崇敬寺玩牡丹花,步于西廊,递吟诗句。”[3](96)可见,在唐代寺庙之地常是举办各种社群民俗活动的公共场所。于此“士女阗咽”之地,当然是男女情恋发生的佳境,唐人情恋小说多有寺庙意象与此不无关系。
检读唐人情恋小说,不难发现,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多为士子,他们或因读书而寄居寺庙:如《纂异 记·杨祯》中的杨祯,“进士杨祯,家于渭桥,以居处繁杂,颇妨肄业,乃诣照应县,长借石瓮寺文殊
院”。[4](3962)《广异记·李元平》中的李元平,“李元平者,睦州刺史伯成之子。以大历五年客于东阳精舍读书”。[4](2689)《法苑珠林·王志》中的学士某,“寺中先有学士,停一房内”。[5](541)《集异记·光化寺客》中的习儒客,“兖州徂徕山寺曰光化,客有习儒业者,坚志栖焉”。或因行旅途中,暮夜投宿寺庙:如《莺莺传》中的张生,游于蒲,而寓居普救寺。如《感异记》中的沈警,“沈警,字玄机,吴兴武康人也……奉使秦陇,途过张女郎庙”。[4](2589)①《原化记·天宝选人》中的赴京选人,“天宝年中,有选人入京,路行日暮,投一村僧房求宿”。[4](3479)唐人情恋小说中男主人公的这种身份,反映了唐时读书人出于应举、求仕的原因,离家游学干谒、多栖止寺庙的现象。而唐人小说的作者,冯沅君先生对六十种四十八位唐人小说作者的考辨,指出其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唐传奇的杰作与杂俎中的知名者多出进士之手。[6]俞钢在其《唐代文言小说与科举制度》中专章考析了唐代文言小说的作者身份,得出唐代科举士子构成文言小说作者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结论。[7](24)正因为唐人小说的作者多为士子,而他们又往往有栖止寺庙的经历,故对寺庙环境十分熟悉,在这些寄托他们幽怀的情恋故事中多寺庙意象也就不难理解了。
唐人情恋故事特别是人与异类情恋故事中的女主人公——或神或鬼或妖,或者为神像、壁画所化,或为殡殓于此的女子亡魂所化,或为什物花木所化,亦往往与寺庙相关。《广异记·李湜》中的神女即华岳庙中 “三夫人院”中的三位夫人神像所化,“赵郡李湜,以开元中谒华岳庙,过三夫人院,忽见神女悉是生人”。《感异记》中的神女为张女郎庙神像所化:“沈警,……奉使秦陇,途过张女郎庙。履行多以酒肴祈祷,警独酌水具祝词曰:‘酌彼寒泉水,红芳掇岩谷。虽致之非遥,而荐之随俗。丹诚在此,神共感录。”[4](2589)《法苑珠林·王志》中的鬼女为暂时殡殓在寺院中的亡魂所化:“唐显庆三年,岐州岐山县王志……有在室女,面貎端正,未有婚娉,在道身亡,停在绵州,殡殓居棺寺,停累月。”[5](541)《纂异记·杨祯》中的妖女为佛寺中一盏长燃的烛灯所化:“母乃潜伏于佛榻,俟明以观之,果自隙而出,入西幢,澄澄一灯矣。”[4](3962)陆勋《集异记·光化寺客》中的花妖是寺前一株百合所化:“暮将回,草中见百合苗一枝,白花绝伟。”[4](3394)这些情恋故事中神女、鬼女与妖女身份的寺庙背景,实与唐时独特的寺庙规制风格与民间习俗信仰相关。
寺庙中多神像壁画,以为信众崇奉礼拜,这是寺庙的普遍的特点,但值得注意的是,唐时寺庙中的神佛造像与壁画,多表现出强烈的世俗化倾向。段成式《酉阳杂俎》云:“隋开皇三年置,本曰弘善寺,十八年改焉……西中三门里门南,吴生画龙,及刷天王须,笔迹如铁,有执炉天女,窃眸欲语。”又云:“净土院门外……寺西廊北隅,杨坦画近塔天女,明睇将 瞬。”[8](754, 764)佛教造像与壁画的原初目的与功能是要使人产生敬畏之心,从而皈依佛门,但是天女之像的“明睇将瞬”“窃眸欲语”,全然没有了庄严与凝重,有的只是夺人魂魄的异性魅力。《广异记·李湜》中李湜过三夫人院,“忽见神女悉是生人”恐正是这一现象的真实写照。不仅如此,有的寺庙造像与壁画中人物形象,甚至以妓女为摹本塑绘而成,段成式《酉阳杂俎》云:“韩幹,蓝田人,少时常为贳酒家送酒。王右丞兄弟未遇,每一贳酒漫游,幹常征债于王家,戏画地为人马,右丞精思丹青,奇其意趣,乃岁与钱二万,令学画十余年。今寺中释梵天女,悉齐公妓小小等写真也。”[8](756)寺院壁画中的天女以家妓为原型,这充分反映了寺院壁画世俗化的倾向,而这些具有强烈世俗风情的天女亦即神女形象,无疑会让那些栖止寺庙的士人生出种种幻想。
另外,唐人有死后葬于寺庙的风俗,据《唐代墓志汇编》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资料,[9]唐人终于寺院或葬于寺院者共35条,《墓志汇编》及《续集》中永久性葬于寺院中或寺院附近的共20条。而且,死者的灵枢因种种原因不能归葬,也可以暂时殡葬于寺院。《法苑珠林·王志》中王志之女归途中夭亡,“停在绵州,殡殓居棺寺”,即属这种情况。而这些早夭而葬于寺庙或者暂殓于寺庙的年轻女子,也让人易生翩翩之思。另外,中国自古就有物老成精的信仰,无生命的器物,有生命的动植物,这些非人的自然物秉赋灵性则可变化成人。寺庙多处深山幽僻之境,年代久远,其间各种什物以及周遭之花草树木,自然也会让人生出各种异想。
寓居在寺庙中的年轻士人,由于多值知慕少艾的年龄。寂寞长夜,相对荧荧一灯;或悠长白日,苦读倦怠之际,临窗一望,难免会有种种幻想。寺庙幽静神秘的环境、造像与壁画中美丽的天女以及寺院里的亡灵、周遭什物草木,也自然成为他们的幻想对象,人神、人妖、人鬼情恋故事的构设也就自然而然了。陆勋《集异记·光化寺客》就是这样一个颇具标本意义的故事:
兖州徂徕山寺曰光化,客有习儒业者,坚志栖焉。夏日凉天,因阅壁画于廊序,忽逢白衣美女,年十五六,姿貌绝异。客询其来,笑而应曰:“家在山前。”客心知山前无是,予亦未疑妖,但心以殊尤,贪其观视,且挑且悦。因诱致于室,交欢结义,情款甚密。白衣曰:“幸不以村野见鄙,誓当永奉恩顾,然今晚须去,复来则可以不别矣。”客因留连,百端徧尽,而终不可。素宝白玉指环,因以遗之曰:“幸视此,可以速还。”因送行,白衣曰:“恐家人接迎,愿且回去。”客即上寺门楼,隐身目送。白衣行计百歩许,奄然不见。客乃识其灭处,径寻究。寺前舒平数里,纤木细草,毫发无隐,履历详熟,曾无踪迹。暮将回,草中见百合苖一枝,白花绝伟。客因斸之,根本如拱,瑰异不类常者。及归,乃启其重付,百迭既尽,白玉指环,宛在其内。乃惊叹悔恨,恍惚成病,一旬而 毙。[4](3394)②
书生为了习儒,坚志栖于光化寺,“夏日凉天”,读书之余,“因阅壁画于廊序”,浮想联翩之际,而“忽逢白衣美女,年十五六,姿貌绝异”,因而“诱致于室,交欢结义”。后书生赠美女白玉指环而别,“白衣行计百歩许,奄然不见。客乃识其灭处,径寻究”,最终发现白衣美女实乃寺前草中百合所化。《集异记·光化寺客》艺术地再现了一个栖止于寺庙中的寂寞书生的白日美梦。而光化寺是作为故事情节展开的空间场景而存在的,于小说字里行间,如“夏日凉天,因阅壁画于廊序”、“客即上寺门楼,隐身目送”、“寺前舒平数里,纤木细草,毫发无隐”以及白衣美女“笑而应曰:‘家在山前”等语,光化寺绰约可见:隐于山中,山前几户人家;寺中清寂,是读书的好去处;廊庑曲折,壁画可观,引人遐思;门楼高峙,可以登临纵观;寺前舒平,纤木细草,可以流连。于此亦可知,寺庙意象也成为这一类小说中的典型构成而散发出独特的审美意趣。
二、寺庙意象:寺庙在唐人情恋
小说中的艺术呈现
寺庙对唐人情恋小说有着特殊的影响,也正因为如此,唐人小说中就多有对寺庙的描写,这些描写或详或略,或繁或简,均成为一种与小说故事情节密切相关的文学化的艺术存在——寺庙意象。比如《广异记·王太》[4](3499)王太避虎失道,在草中行十余里,见“有一神庙”,因宿于梁上,“寻而虎至庙庭,跳跃变成男子,衣冠甚丽”,继而虎神发现王太,言王太业当为其所食,并教其避难方法。小说主要表现脱离虎口的智慧和法术,而故事中的虎居然化为人形,居住在神庙中,且能在虎形与人形之间随意变化,其间蕴含着的佛道观念与民俗信仰成分值得玩味。又如袁郊《甘泽谣·圆观》[3](311),叙写李源与圆观的两世情谊,洛阳惠林寺是他们生活与交往的主要场所,李“脱粟布衣,止于恵林寺”,与圆观“促膝静话,自旦及昏”,“如此三十年”。而圆观转世时与李源相约十二年后再见,地点则是杭州天竺寺。小说中洛阳惠林寺与杭州天竺寺不仅是李源与圆观两世情谊的见证之地,无疑也为小说主题思想因缘轮回观念的表达提供了最为恰当的背景。再如薛用弱《集异记·徐智通》[4](3148),言徐智通偶于河桥听到两神相约来日于楚州龙兴寺前戏场斗技的对话,二神在交谈中各自炫其神技及效验,徐智通于一旁听得,是日前往观看。小说中龙兴寺作为神仙斗法的背景,自然而亲切。而在唐人的弘佛小说中,寺庙意象更是大量存在,此不赘述。相较而言,除去弘佛小说,在唐人情恋小说中亦存在大量的寺庙意象,这些寺庙意象在小说中构成一道独特的风景。
唐人情恋小说,以男女主人公身份的不同,大致可概括为两种主要类型:一是人间普通男女的情恋,一是人与异类之间的情恋。无论哪一类,其间均多有寺庙出现,这些寺庙在小说中往往呈现出独特的意蕴,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意象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