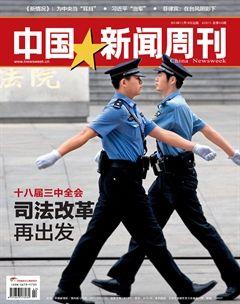野夫:写作是一种招魂的过程
吴子茹

“也许一个人老了,就爱怀旧。其实就是我辈,也不再是当年那种纯情男女了。正是因为与时俱老了,才恍觉当年之我的青春热血值得凭吊。这个时代,你看网上男女,大约真像王朔所云——一点正经没有。很多原本神圣庄严的东西,都被庸俗地消解了,都变成嘻哈疯癫了。”野夫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剖析自己的心理。这也是他对1980年代的眷恋与自省,在野夫写作《1980年代的爱情》的时候,他一直沉浸在这样的思绪中。
这位51岁、曾经纵情诗酒的鄂西土家族男人,也开始不无伤感地回望他的青春,属于1980年代的青春。在那个充满希望、理想与幻灭的年代里,野夫曾经是诗人、警察和罪犯。
真实与虚构中的故乡
在1980年代结束之后,野夫出狱、北上,成为北京小有成就的书商。此后又散尽家财栖居云南,专注写作,成为一名作家。现在他受邀在德国莱茵河畔写作,难得出国的他,借机在欧洲各处闲逛,“看看欧洲文明的积淀与成就。”同时在微博上点评时事。
但实际上,野夫从未离开过80年代,如同他从未离开过鄂西利川这片偏远的土地一样。1980年代与鄂西山野,构成野夫的精神江湖,让他得以抵御纷扰不堪的当下现实。
身在欧洲,野夫的微博发得频繁,言辞激烈地回应当下这个时代。同时,他也用伤感的文字,为过去作祭。
他把近年的一些散文收进了《身边的江湖》,同时还出版了小说《1980年代的爱情》。野夫以自己在80年代经历过的爱情故事为原型,尝试用小说的方式,记录自己经历过的爱情与时代。
《1980年代的爱情》虽然是小说,但其中“百分之六七十”的内容都是野夫的亲身经历。散文化的语言和第一人称的叙述,让这本书显得真切而柔软。
故事很简单,“我”是偏远中学里唯一考入大学的学生,毕业后被分配回老家的镇上任职,在这里与高中时一直暗恋的对象“雯”不期而遇。古朴偏远的小镇上,爱情终于生根发芽,但雯深情而隐忍,最终将“我”推向了外面更广阔的世界。野夫原本以为年轻人读这本书会“隔膜较大”,但出乎他的意料,年轻读者的反馈很积极,书出版后,他每天收到的微博反馈至少有几十条,而“百分之九十九都持赞扬的态度,”野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野夫老家鄂西利川,那里山重水隔,与湘西凤凰同属武陵山地区。鄂西地区和湘西一样,民风淳朴彪悍,构成了野夫写作和为人的精神世界。这个尚气豪侠的写作者经常在文章里不惜笔墨地回溯自己作为“巴人”的源头,书写自己对边民传统的认知。
对于武陵山区稍通文墨而又心怀抱负的年轻人来说,出走或者回归,成为永恒的纠结。入山,意味着放弃前程,而走出武陵山脉,进入外面的平原世界,才谓之“入世”。有抱负而又思乡心切的人,常在天平的两端徘徊。熊希龄、沈从文、黄永玉如此,1980年代时的野夫也如此。这种情绪也弥漫进《1980年代的爱情》一书之中,甚至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叙事主线。小说的故事,简单到只剩下欲说还休、欲走还留的情绪。没有大开大阖的故事结构。“我”想留,但“雯”一次又一次地把“我”推向大山外的世界。“我”出狱后,尽管有机会在一起,但雯的态度依然坚决。
关于鄂西利川的故乡情结,成为野夫最隐秘的内心一角。正如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野夫一步三回头,被爱情,也是被时代推着向前,离开了那个生养他的故乡。
1980年代
“看似还能拼酒约架,但内心是真的已经沧桑了。”现在的野夫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1978年,野夫16岁,上恩施师专,现在的湖北民族学院。他是班上最惹是生非的学生。爱读书,不爱上课,但考试成绩一般还好。流行喝酒打群架的时代,野夫是一群学弟们的孩子王,经常帮人出头担事儿。“性格比今天火爆,”野夫这样评价当年的自己。身上随时带着匕首,爱打抱不平,很受同学喜欢。
“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刘叉这首《偶书》,是野夫名字的由来。事实上,来自湘西和鄂西地区的人,自称“山野村夫”的人并不少。胸有文墨而自称山野村夫,既是自嘲,也是另一种方式的自傲。
1982年,恩施师专一群学生成立剥枣诗社,是湖北最大的诗歌社团,野夫是发起人之一。大家在一起油印诗刊,每月一期,写的是新诗,但野夫当时已经能娴熟地写旧体诗。
野夫的江湖习气,多少来自土家山民的彪悍作风。大家闺秀的外婆给他讲故事,教他习古文诗礼,成为野夫的启蒙教育。成年以后,剥枣诗社和武汉大学旁听的经历,为野夫打下了更深厚的文学功底。
野夫时常在文章中提起凤凰作家沈从文,他希望利川之于自己,就像凤凰之于沈从文,山水故乡的滋养是文学最好的养料。“《边城》这个故事比我的更简单,它为什么魅力十足?”野夫用沈从文打比方。他认为,文学的终极目的和意义,在乎语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不是别的。“好的纯文学,不是去拼虚构能力和复杂情节的。”
沈从文构建了他的神秘湘西。虽然同为武陵山区,但野夫的利川却并非如一个世纪前的纯净、完美。“文革”开始时,野夫四岁,刚刚开始有记忆。最清晰的一幕就是父亲被戴高帽子押着游行的场景。此后的漫长十年,他亲眼目睹了社会的天翻地覆。野夫甚至认为,自己骨子里好斗的性子,“也许就是在这时种下的”。
但在《1980年代的爱情》中,野夫却又写出了单纯而美好的味道。“十年”喧嚣后的鄂西山野,只剩下重创后的死寂。两个年轻人的爱情就在这样静谧的环境里展开。在野夫心中,写爱情的目的依然在于写时代,“写史”。他将这样的写作称为“招魂的过程”。
以小说纪史
2003年,野夫在做自己的影视公司,他忽然想寫自己的故事,甚至想自己投资、自己导演,“就想做一个纯粹自己的影视作品”。野夫善于尝试,他认为中国的文艺片“缺乏经典”,但搁了十年后,野夫不再想做电影了,但舍不得想写的那个故事,于是改写成了小说——就是今天的《1980年代的爱情》。“就当是对自己青春和那个年代的一个祭奠吧。”野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藉由这本小说,更重要的是,野夫梳理了那个纯真、充满理想的时代。
野夫并不认为《1980年代的爱情》是自己的代表作。他更愿意将之描述为关于文体的实验。虽然也写过小说《父亲的战争》,但他将《1980年代的爱情》描述为自己“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对于野夫来说,散文是最见长的文体。在《尘世挽歌》《江上的母亲》《乡关何处》收录的文章里,他以“史记”的笔法,每篇文章寥寥几千字,写尽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悲欢故事。为身边人“作传”,记录家族的历史。
野夫的散文里,处处可见对故乡、故人的留恋。写得最多的是鄂西利川的家族史。被打成右派、性格倔强最后投河,“至今不知曝尸在哪一片月光下”的母亲,至死也隐忍不提家人一个字的父亲,被投监二十多年、回家后都忘了自己罪名的“伯父”,一根绳子上吊死的大伯母二伯母。野夫用笔如刀,将自己的伤口割得鲜血淋淋,是为“纪史”,而纪史,是为了拒绝遗忘。这是野夫的理想。
野夫逐渐认识到,散文由于完全真实,“因而会影响一部分想象力的发挥”。而小说一样是自己经验世界的一部分,但因为是虚构,“可以更加逼真地表现一些残酷的生活”。因而跟他的散文一样,“也是一种招魂的过程”。 现在,身在欧洲的野夫正在写作新的长篇小说。
“我们本人也与时代同流合污着,但这似乎又不是我们的真我,就像垮掉派的诗歌所说——我们并不是我们污脏的外表,我们的内心也盛开着一朵圣洁的向日葵。基于这样的一些伤悼,所以开始写一点这些忆旧。”野夫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剖析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