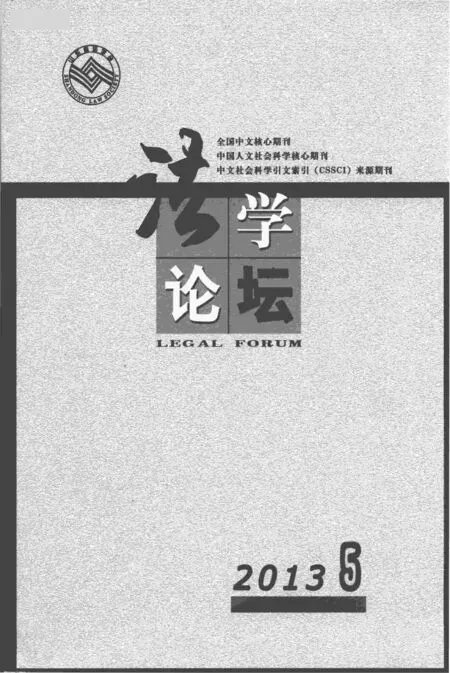外商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退出路径探析——从国际板证券发行上市准入监管切入
马其家,范晓娟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29)
一、引言
盛行当下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以下简称“私募基金”)业已从其设立伊始的单纯并购工具发展为仅次于银行贷款和首次发行并上市的重要融资方式。随着当今世界经济中心向以我国为中心的新兴经济国家的转移,加之国内银行贷款政策的缩紧,国内市场对于多样化融资的需求进一步增大,国际私募基金纷纷进入中国,国内绝大多数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背后都具有外资背景。私募股权投资者的目的是为了获取高额收益,在基金“募集资本——投资——退出——再投资”的循环资本运作中,退出环节为投资者实现了由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的顺利转化,而被寄予厚望的首次公开上市发行更是有助于投资方和被投资方的合作博弈实现双方利益最大化。外商投资股权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外资基金”)本身,以及其作为战略投资者投资的境外企业,都很可能进军中国拟构建的证券国际板市场,在中国境内实现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的新一轮融资。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要加快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建设,探索建立国际板市场。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处于新兴加转轨时期,人民币国际化尚在进程中,此时推出的国际板带有特定历史阶段的过渡性制度色彩。一方面,在特定历史时期,尤其是世界金融危机并未消散之际推动国际板的建立是一种机遇,有助于为将来资本项目全面开放后的全球化竞争积累经验,增加我国在国际资本金融市场的发言权,在传统西方经济标杆疲惫之际加速建立新兴经济中心;另一方面,经济形势差异明显之际推出国际板也是对监管机构的一种巨大挑战。从历次金融危机来看,整个监管的历史往往是以危机作为起点,以危机作为结束,风险和回报的追求会不断出现新的金融创新产品来催生新一轮的监管要求。2008年金融危机暴发后的几个月,一份长达1279页的金融改革法案(《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被提出,美国政府期望以强化监管的方式恢复对美国金融体系的信心。而此时,我国在建立国际板时更应避免因不同强度的监管环境而成为投机者首选的监管洼地。这就要求我国政府在处理与市场的关系时,应慎重设计一种体现规制与确权有效博弈的准入机制,在效率和稳定之间寻求一个最优的平衡。
二、私募基金的退出机制探讨
私募基金的投资运作过程一般包括募集资金、项目选择、投资管理和资本退出四个阶段,由于私募股权投资的根本目的并非旨在掌握公司的控制权或者长期经营权,而是在投资目标公司后,随着所投资企业的发展而获得增值,并在合适的退出渠道中将该增值转化为实际收益获取高额收益,资本退出便成为基金资本运作过程中的核心环节。私募基金退出是指在其所投资的企业发展到一定成熟的阶段之后,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将其持有的权益资本在市场上出售,以收回投资成本并实现投资回报的行为。[1]这里的企业股权出售包括选择适当时机和方式在市场上出售变现或转换为可流通证券。无论是出售变现或转换为可流通证券,均与私募基金个人最优这一根本目的相吻合。私募基金的退出在优化资源配置性效率的同时有利于实现帕累托最优,对实现社会福利也具有重要意义。投资不同的产业对于私募基金而言是基于对未来市场绩效预测而进行的权利选择。典型的私募基金一般约在10年后实现最终清算,因此,私募基金集中投资于未来上市概率较高的行业和公司,即计算机、生物技术、多媒体、互联网等“热门”产业,而非不具有高成长性和社会进步性的高耗能、低技术等没落产业,而对这些竞争行业的首轮选择本身就是一种完全竞争行业的均衡。
私募基金本质上是一系列协议与金钱的组合。投资者通过出资或提供劳务的形式,以投资协议、管理协议等契约性质的文件进行组合,实现一定期限,往往是7—10年的股权或其他权益合作关系。实际上,从私募基金的募集设立到项目投资,再到项目退出,这一过程反映了股权或其他权益关系与债权关系的循环转化。由于私募基金组织形式的不同,在基金内部,各投资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略有差异。根据国际惯例,私募基金的组织形式主要有合伙型、公司型、契约型三种,[2]目前运用最为普遍的形式是有限责任公司型和有限合伙型。在有限责任公司型私募基金中,基金管理人股东和投资者股东与公司的关系基本等同于一般股东与公司的关系,而在有限合伙型私募基金中,普通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之间的共有关系也类似于在公司章程下的内部股东关系。在基金外部法律关系中,私募基金投资新的合伙企业或公司企业后,与该企业形成新的股权或类似权益关系,一旦在该被投资企业上市后,则通过转让所持有被投资公司的股权从而转化为与第三人之间的债权关系,最终实现以金钱为对价的债权权益。
有关私募基金的退出应重视对“私募”和“股权投资”或称“权益投资”的理解。私募是相对于公募而言的,[3]在私募基金产生之前,原本是就证券发行方法之差异,以是否向社会特定或不特定公众公开发行证券为区别,从而界定为公募和私募;而股权投资则相对于证券投资而言,以一、二级市场的投资方向和对象的不同而界定,私募基金是投资者通过投资未上市目标企业参与入股并进行管理的方式实现利益资本化;而证券投资基金则是指通过投资已上市公司的证券等金融产品以实现利益资本化。在此提出两者的区别极为必要,因为两者经常被混淆。中国国内的相关市场主体为寻求法律的保护,纷纷呼吁将私募基金的监管纳入《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近期修订中,甚至有监管层力量力推此事。正是混淆了两者的属性,有可能造成监管权力的错位及对不同金融产品衔接监管的冲突。证券投资基金的退出类似于股票市场的退市机制,主要指基金的中止及退市;而私募、基金的退出由于市场风险、被投资企业违约等因素的存在,被投资企业的股权增值具有不可预测性,一般包括常态退出和非常态退出,具体而言,前者指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产权出售,后者指资产清算。
三、外资基金的退出路径选择
私募基金的退出方式有多种,国内有的学者认为退出方式有首次公开招股、将所持股份转让给战略投资者或其他风险投资家、借助于被整体收购实现投资退出、所投资企业回购、清算等五种;[4]有的学者认为分为主板上市、二板上市或OTC 柜台交易、协议转让退出、股权回购、破产清算等五种;[5]有的学者认为有公开上市、股权回购、企业兼并收购、企业清算等四种;[6]有的学者认为主要有股票市场上市、企业并购、股权回购等三种;[7]有的学者认为有首次公开上市、出售、清算等三种。[8]国外有学者认为有首次公开上市、购并、回购、二级出售、清算等五种。①参见Douglas J.Cumming,Jeffery G.Macintosh,Venture Capital Exits i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3 University.of Toronto Law Journal,Vol.53,p101.具体分析可知,上述学者的看法具有内在一致性,据此,私募基金的退出方式可以分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产权出售、资产清算三大类。关于三类退出方式的比对如表1。
需要指出的是,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实际涉及发行和上市交易两个环节。仅仅是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而不上市流动,私募基金所持被投资企业的股票无法高价变现,因而无法实现收益最大化退出。②从目前多数国家的法律实践看来,发行公司在股票发行前便取得证券交易所的上市承诺,在股票首次发行之后立即在证交所上市,发行和上市出现了一体化趋势。参见吴国基:《证券发行审核制度研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第76页。我国实行发行和上市的分离制。目前产权出售在私募基金中应用最多的形式是从美国引入的管理层收购方式,在国内演化为对赌协议的广泛应用。对赌协议即估值调整机制(Valuation Adjustment Mechanism,简称VAM),是一种基于公司业绩而在私募基金和创始股东(或管理层股东)之间进行股权调整双向约定。私募基金之所以与创始人股东签订对赌协议,其主要目的是通过一种直接跟利益挂钩的激励与惩罚机制,刺激创始股东或管理层为公司创造出更好的业绩,从而也为私募基金带来更大的回报,同时还是防范投资风险的一种手段。国外的对赌协议通常涉及财务绩效、非财务绩效、赎回补偿、企业行为、股票发行和管理层去向六个方面的内容,但国内的对赌协议较为单一,通常采用财务绩效(如收入、利润、增长率)为单一指标,以股权作为确定对赌双方的权利和责任。我国法律目前并未对赌协议的合法性予以明文规定,但从契约自由角度考虑,私募基金与被投资公司作为独立民事行为主体,在意思自治的前提下订立协议,在未来满足一定条件下实现部门股权或资金的赠与,也有理由认定为有条件的民事赠与行为。但最近首例对赌协议案例——苏州工业园区海富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海富投资”)和被投公司甘肃世恒有色资源再利用有限公司(下称“甘肃世恒”)的对赌条款最终被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为相对有效,其有效性仍值得商榷。此外,目前产权交易市场在我国开始建立,为私募基金提供了另一渠道,但这种退出方式在我国刚开始萌芽,相关的法律配套体系未开始建立。

表1 国内三类退出方式的对比表
综上,首次上市并公开发行是私募基金最主要的常态退出方式。从经济角度来看,首次上市并公开发行能够产生高流动性和高市盈率,从而使得企业获得更高的股票定价。据清科研究中心③清科集团清科研究中心2001年创立,致力于为众多的有限合伙人、VC/PE 投资机构、战略投资者,以及政府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投资银行、研究机构等提供专业的信息、数据、研究和咨询服务。范围涉及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新股上市、兼并收购以及TMT、传统行业、清洁技术、生技健康等行业市场研究。目前,清科研究中心已成为中国最专业权威的研究机构之一。统计,自2004年以来,私募基金共有743 笔IPO 退出,占退出总数的62%;共有162 笔并购退出,占退出总数的13%。[9]从法律角度来看,首次上市并公开发行作为一种常态的退出方式,相对于产权出售而言,能够充分发挥私募基金与被投资基金在私法中的意思自治;相对于资产清算而言,遵守证券首次上市并公开发行的法律监管成本较小。
四、外资基金通过国际板上市退出的准入性监管分析
外资基金通过国际板上市退出往往涉及跨国民商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或法律关系的事实发生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①参见M.Benddettelli,loc.Cit.,p.720;A.Licht,op.cit.footnote 8,pp.616-620;M.Roe,loc.,p.599.根据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 于1998年9月发布的《外国发行人跨国证券发行与首次上市国际披露准则》,对于跨境发行定义为:不管公司是否在东道国同时发行或上市证券,只要直接在东道国之外的一个或多个国家发行或上市,就是跨国发行或上市。国际板证券发行在不同国家存在跨境②既包括跨越国界或边界,也包括跨越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法域。发行(Cross-border issuing)、国际发售(International issuing)、跨国证券融资(Multinational securities financing)的不同称谓,但均指经营主体在注册设立地以外的国家或地区的证券市场发行证券并筹集资金的行为。我国对于建立国际板的设想是,在我国证券市场建立一个让外国公司证券可在境内交易所挂牌交易并接受集中监管的特殊证券交易平台,符合条件的境外公司,或称离岸公司到我国境内A 股板块上市,国内投资者以人民币来直接投资该公司的股票。该类境外企业在A 股上市后,因其“境外”(Offshore)性质③区别于海外性质,境外性质包括我国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台湾地区。而将被划分为“国际板”。这就要求在我国当前A 股市场相关制度的基础上建立独立的境外公司证券的上市发行制度、交易制度、持续信息披露制度以及退市制度等,将境外公司证券集中置于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的统一监管之下,此时,上市发行这一市场准入性的监管最先进入制度设计的范畴。
(一)准入条件——外资基金的上市主体资质
对于外国公司在本国发行证券的能力问题,各国规定不一,但大多数实行资本项下外币自由流动的国家对于外国公司在本国发行证券采取的均是一般认可,即只需符合国内发行证券的主体条件、履行国内证券法所要求的程序,如《1933年美国证券法》、《德国有价证券交易法》。根据美国证券交易法的一般规则,外国发行人指的是“发行人是外国政府、外国国民、或根据外国法律成立的公司或其他组织。”④参见General Rules and Regulations promulgated under the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Rule 3b-4 (b):The term foreign issuer means any issuer which is a foreign government,a national of any foreign country or a corporation or other organization incorporated or organized under the laws of any foreign country.我国目前尚未完全实现资本项下外币自由流动,《证券法》作为规范证券发行、上市与交易的专门法,在第2条第1 款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股票、公司债券和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的发行和交易,适用本法……”,并在部门规章《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8条中明确规定:“发行人应当是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未来在我国证券国际板上市的外资基金涉及海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ualified Foreign Limited Partner,简称QFLP)、外资人民币基金,其中可以作为上市的主体包括:符合一定条件的海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本身和其所投资的境外企业,以及外资人民币基金所投资的境外企业。在外资基金中,基于对税务、法律监管等成本考虑,基金的法律架构往往相当复杂,基金本身所采用的法律组织体也较为多样,并且通常选择开曼、维尔京等避税港设立基金,以筹划税务成本;通过夹层商事组织体(特殊目的公司)作为中间结构实现跨国法律监管成本的最小化,典型法律结构如图1 所示。
此时需要探讨的问题是跨境拟上市发行人的组织结构和公司治理问题。由于《1933年美国证券法》对于“证券”的界定范围相当宽泛,包含各种债务工具、石油及天然气或其他矿产权、投资合同、股票、保险产品、银行产品、雇员鼓励计划、有表决权之信托证书、存托凭证和凭证、设备信托证、但保证书、认股权证、期权和期货等。⑤参见Louis Loss,Joel Seligman:Fundamentals of Securities regulation,at 194.私募基金中有关合伙权益的投资协议安排类似于该证券范围内的“投资合同”,而有限合伙企业这种组织形式在美国被认定具备合法的上市资格。在1980年S.E.C.v.Murphy 一 案中,法院就支持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将不参与经营的有限合伙人的出资视为证券的裁决。①参见SEC v.Murphy,626 F.2d 633,649-52 (9th Cir.1980).有限合伙基金在美国上市后被称为“公开上市有限合伙企业”(Publicly Traded Partnerships,简称PTPs),或称“业主有限合伙企业”(Master Limited Partnerships,简称MLPs),其公开发行的权益凭证为普通单位(common units)。在特拉华州注册的基金典范——黑石集团有限合伙企业于2007年6月22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然而,有限合伙企业在我国却并未被纳入能够直接上市的合格商事组织体中,我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所认可的上市公司的组织形式只能是股份有限公司。是否能够接纳以有限合伙企业为代表的其他组织形式关系监管成本与监管能力,在上市审查程序的短时间内很难穿透该境外复杂法律结构并追溯至最终合伙人的权益结构,此时,与发行人所在国家之间的监管合作协议有助于该问题的求解。此外,对于发行主体的认可还涉及依据外国公司法所设立的外国公司与国内公司在治理结构差异中的“容忍”问题。公司制境外私募基金在我国证券国际板上市,将面临两大法系中关于单层治理模式与双层治理模式的选择性困境。按照伯利和米恩斯的观点,公司治理问题的产生源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公司治理的焦点在于使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相一致。[10]市场知道怎么做最好(Market knows best)的思想是当前公司治理理论的基础。法国推行允许公司在单层与双层两种治理模式之间选择的单双层选择模式,或称混合型治理模式正日益受到大陆法系各国普遍的青睐。有理由相信,多元化公司治理模式的并存符合公司治理监管的根本理念。合伙制境外私募基金在我国证券国际板上市将对公司治理提出更大挑战。科斯在20 世纪30年代提出了“企业契约理论”,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公司视为一个由物资资本所有者、人力资本所有者以及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的一系列契约的组合。[11]在这种将公司视为利益相关者集合体的主张之下,公司与契约之间具备了更大的契合性。合伙制境外私募基金本身作为一系列契约的组合,并且有限合伙人不具备投票权,普通合伙人掌握控制权,该种治理结构符合现代契约理论。此外,目前的发展趋势之一就是在组织上建立起类似于公司治理的结构,②参见IFSL(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ervices London)Research,Private Equity 2008,http://www.ifsl org.uk,最后访问日期:2012年7月26日。由此,合伙制境外私募基金本身的治理结构与公司的治理结构具有内在一致性。

(图1)
(二)准入程序——组织法冲突
国际板上市中的准入程序涉及法律的适用问题,而证券国际板法律的适用中则体现为组织法的冲突。这种法律冲突在国际板证券中,主要体现在证券的发行和交易领域,涉及的法律关系主要是民商事私法冲突,主体包括证券发行人、各类中介服务机构、投资者等。由于证券的发行人——外商投资股权投资基金及其所投资的企业和投资者分属于不同国家;证券的发行地不在发行人所在国境内;上市并发行跨越两个或多个法域,受两个或多个法域的管辖和监管机构的监管,因而所产生的法律冲突主要将发生在公司本国法和目标市场之间。拟上市企业作为境外企业,受到设立地即属人法的强制管辖,同时在我国境内上市,其交易、发行行为受到行为地法即我国法律的管辖。由于证券本身是一种具有财产属性的民事权利,而跨境发行具有多重空间属性,证券权利所在地的确定有助于确定调整证券交易的冲突法规则。法律实践中,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依据属人法,即法人的国籍或住所之所属国法律的规定,但各国对于法人的国籍或住所的确定一直存在较大分歧。而对于跨国证券发行,由于目标资本市场所在国家是公开上市并发行的主要场所,目标市场基于保护境内公共利益的考量,一般会通过立法机构来设定进入市场的条件。美国作为代表国家,根据《1933年美国证券法》第5条规定,当一家公司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同时上市发行时,应在美国向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简称SEC)进行登记,并适用该法及S条例等相应规定。此外,美国于2002年通过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这一法案取消了对境外公司的通融性豁免,对境内发行人和境外发行人实行一视同仁的政策,并加强了对境外公司证券的监管。[12]相比之下,欧盟统一体内部的协调性规定则较宽松。欧盟委员会于1999年5月出台了《金融服务行动计划》(the EU Commission's Financial Services Action Plan,简 称FSAP),在FSAP 出台前,调整欧盟证券规则的冲突规则是传统的“受影响市场”规则,即每个参与证券交易的当事人都可适用其本国的证券法。但这会导致证券市场的多重管辖,各发行人国家的法律都竞相要求适用于一个跨多个欧盟成员国的发行人的多重挂牌交易。因此,传统的法律适用规则对于欧盟协调整个欧洲的证券市场来说是一个障碍。在FSAP 出台后,欧盟境内证券发行交易适用的一般规则是:不论股票发行交易发生于何地,公开招股和证券交易适用证券发行人的登记注册的办公室所在地国家(母国)的法律。[13]由此可见,在应对证券国际板的构建初期,我国首先需要进一步完善《证券法》中关于域外性的适用规则,可以从市场准入的必要性出发,对于在我国拟上市的公司同时一般准入程序和特殊准入程序,并可以考虑效仿欧盟,在与法律体系相近并且长期参与的稳定区域经济体中实行与一般准入程序相关的组织法。
(三)准入范围——信息披露延伸及监管权扩张
各国基于对于本国公共政策的考量,东道国的证券监管者由于对其领域内的证券交易行为具有排他性的监管权也将被本国法律授予对境外企业的相应的“垄断监管权”。[14]这种“垄断监管权”在市场成熟度不同的国家中表现为监管的严苛程度不一。一方面,由于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持续性影响,以金融创新为代表的美国将新一轮的危机为起点,推出了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加强了对金融业的监管,随着欧债危机蔓延,欧盟国家也势必会跟进出台监管政策,由此可能形成一种监管权的竞争态势;而另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由于金融市场的单一化、原始化,可能将本次危机作为起点,在构建新的金融中心中寻求在全球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发言权,提高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的能力,由此推出的监管性政策相对则较为宽松。在这种对比鲜明的监管趋势中,向来以追逐利益最大化、成本最低化目标的外商投资股权投资基金发行人,希望避开其本国证券法而去寻求国外证券法的适用,寻求单一证券法调整的市场,并且选择信息披露较为宽松的法律环境,这将会导致选择证券市场环境的结果。在目标市场的法律监管成为跨境证券发行人可选择的一种权利时,则会产生类似国际私法中的法律规避行为,跨境证券发行人利用监管的不同层次选择监管洼地,进而实现监管套利。①“监管套利”作为官方的表述最初见于G20 华盛顿峰会的声明当中。“金融监管套利”一般是指各种金融市场参与主体通过注册地转换、金融产品异地销售等途径,从监管要求较高的市场转移到监管要求较低的市场,从而全部或部分地规避监管、牟取超额利益的行为。参见杨柏国:《避免“监管套利”——合作而非竞争》,载2009年2月12日《第一财经日报》。
外资基金及其所投资公司在我国国际板上市,是一种从私密性自由商业操作到强制信息披露的重大转折。而对于所有拟上市公司,都存在着强制性信息披露要求与保守商业秘密之间的矛盾和协调问题。美国对于在国内进行发售的证券实行国外综合披露制度,但为降低外国私人发行人的报告负担,对外国私人发行提出了与国内企业相当的披露要求。而澳大利亚实行连带披露规则,反映在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中:境外企业必须立即以英文语言将提供给母国证券交易所的所有对投资者公开或可能对投资者公开的信息向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作相同披露。②参见Listing Rules of ASX,Art.No.1.15.2,Available at http://www.asx.com.au/supervision/rules_guidance/listing_rules1.htm.这种信息披露监管原则能够保证跨境发行领域信息披露监管的完整性,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保障东道国证券投资者对境外企业的知情权。所以,在国际板市场监管中,各国对于信息披露的延伸性,以及监管的扩张性、涉外性一般持认可态度。我国在这种认同中可以借此进一步完善我国监管规则的细则。
五、国际板构建的前车之鉴与准入监管设想
各国证券市场中一般均设置了国际板上市板块,以美国为代表的成功范例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以日本为代表发展国际板的经验教训更值得我们深刻反思与借鉴。日本于20 世纪80年代开设国际板,鼎盛时期的1991年,曾经有127 家外国公司在东京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而到2009年6月,东京证券交易挂牌的外国上市司仅有15家。[15]究其失败的根源,市场准入方面的监管导向值得研究。整体而言,日本对于证券国际板的监管过于严苛、复杂。对于境外拟上市公司,在市场准入主体方面实行排外的歧视性规制,过于重视保护境内企业;准入程序中增加了事前报告和认可制度,并对赴东京交易所上市的境外企业,设置了近年税前利润额、国内股东人数等诸多条件,超过了世界绝大多数交易所的严格程度和繁杂条件,并且审查严格,对于中介机构的责任过于强化,超出了中介专业的职责范围,审核批准周期冗长。市场准入的背后体现的是政府规制市场、公权干预私权,但前提是认清政府与市场的合理边界。市场准入机制最初定位为政府克服市场失灵而提供的一种公共物品,其本质上应体现正外部效应,即意味着它的使用至少不会给其他人带来利益受损的结果。[16]日本的教训之一在于政府的规制几乎无处不在,使得境外上市主体几乎没有任何私权利行使的空间。一方面要最大化实现本国公共利益,一方面又以歧视性规制对待他国上市主体,实质是一种负外部性的监管导向。事实上,市场准入在不同层级的设置以及所体现的价值目标上会存在一定的差别,政府规制层次有所不同。因而,在构建我国证券国际板的国内层面立法层面,应从上市主体、准入程序和准入范围中纳入一般准入与特殊准入机制设置。对于维护社会安全、市场行业秩序的规制超出一般准入范畴之外的风险,应过渡到特殊准入机制范围内,适用较高准入的核准条件,才得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有效维护。如有限合伙企业等非公司法法人性质企业作为上市主体,需要穿透多层法律结构背后的股权结构,这就需要更高的准入要求披露才能够实现投资者保护目的。在行业选择领域,对于我国处于需求危机的能源行业,则不宜设置较高准入条件,此时降低公权力规制也是应有效维护公共利益目的。
从根本上而言,监管实际上是在效率和稳定之间寻求一个最优的平衡。这种平衡作为各国所追求的监管目标,在市场环境类似的国家中可能存在重叠的监管领域和方式,在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中也可以达成在原则性的一致监管。因此,在对于国际板证券监管的国际层面,
跨境监管合作便成为当前协调跨境证券发行的共赢选择。国际证券会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简称IOSCO)作为目前国际社会国际证券业的组织仅将自身描述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证券监管机构国际合作论坛”,③参见IOSCO 官方网址,[2012-07-27]https://www.iosco.org/about/ index.cfm?section=history.演进到今日,更多的具有一种行业属性,其正在努力推进的统一性标准和监管规则也缺乏约束力。此时,诸如世界贸易组织般的跨国金融监管权力的政府间组织正为又一历史需求的产物,在这种国际金融性组织尘埃落定之前,双边及多边合作备忘录的协议成为跨境监管合作最为便利、有效的方式,不论在相似或相近抑或差异较大的法域均得以适用。中国证监会目前已与49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53 个监管合作备忘录,但该类备忘录一般原则性较强,仍需要更多细则性指引予以明确,尤其是在跨国证券所涉及的金融问题更为复杂和深远的情况下。
[1]罗玉中,李程富,徐娜.关于私募股权基金退出机制的研究[J].经济视角,2011,(6).
[2]李晓峰.中国私募股权投资案例教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6.
[3]王苏生,陈玉罡,向静.私募股权基金理论与实务[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2.
[4]刘健钧.创业投资原理与方略——对“风险投资”范式的反思与超越[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302-306.
[5]高正平.政府在风险投资中作用的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203-215.
[6]孔淑红.风险投资与融资[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4.
[7]徐水前,李字龙.风险投资法律实务[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1:176-178.
[8]李月平,王增业.风险投资的机制和运作[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126-142.
[9]姚轩杰.新三板将成PE/VC 退出新选择[N].中国证券报,2012-07-16.
[10]Adolph A.Jr.Brle,Gardiner C.Means,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M].New York :New York:MacMillan,1932.
[11]刘黎明,张松海.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模式探析[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5,(2).
[12]贺显南.从利益均衡的角度看股市国际板的推进[J].金融与投资,2010,(6).
[13]Luca Enriques,Tobias H.Troger,Issuer choice in Europe[J].Cambridge Law Journal,2008,(67).
[14]Frederick Tung,From Monopolists to Markets?:A Political Economy of Issuer Choice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Regulation[J].Wisconsin Law Review,2002,(1367).
[15]陆岷峰,高攀.国际板市场发展的境内外经验借鉴及策略研究[J].天津商业大学学报,2011,(6).
[16][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第二版)[M].梁小民,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4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