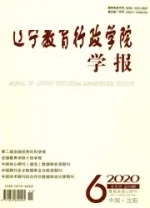20世纪生活丑向艺术美转化的动力机制
史健男
辽东学院,辽宁 丹东 118003
1853年,罗森克兰兹的《丑的美学》出版,丑作为一个独立的审美形态登上美学发展的历史舞台,“仿佛是一只五彩的画笔,先是在美的图画上勾勾点点,继而画出了美女身边丑陋的老太婆,可它的画兴一起便无法抑制,继而又涂上了荒诞和滑稽的颜料在画布上肆意地涂抹起来”。[1]20世纪,后工业社会的危机,两次世界大战的伤害,自然环境的恶化,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物、人与自我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畸形关系,生活丑更是在文学艺术中得到了创造性表现,成为现代、后现代等各种“主义”广泛关注和着力追捧的对象。
一、实践的解构功能推动着生活丑向艺术美转化
“美向着低处走,愈走愈低微卑贱,以至人的本质力量受到窒息和排斥,而非人的本质力量却以堂皇的外观闯进了我们审美的领域,这时,它在对象中显现出来的就不是美,而是丑”。[2]古典的、和谐的美在现代艺术中似乎消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畸形的、怪异的、非规则的、反自然的、反理性的、孤独的、厌恶的、非对称的和阴森恐怖的东西。有人甚至认为,20世纪的艺术是丑的艺术,20世纪的美学是丑的美学(丑学)。如果以注重艺术实践的建构和转化功能的传统美学为立足点,这种说法毫无疑问;但从20世纪艺术家们更加注重在艺术创作中扭曲和否定现实世界来看,丑获得空前的美学价值却是实践的解构功能的必然要求。
广义的实践一般指人的现实活动,与人的意识过程、理论活动相对应。从功能的角度来看,实践有肯定性的建构功能,转换性的转化功能,否定性的解构功能。它们对应着实践的自由,准自由和不自由,反自由,在审美领域对应产生柔美(优美)、刚美(崇高)和幽默、滑稽,丑。张玉能教授在《新实践美学论》中指出,实践不仅可以建构、创造出一个新世界,使现实朝着肯定性方面转换或发展,而且也能解构、破坏世界的某些部分,并使现实朝着否定性方面转换或发展。简单地说,实践的解构功能就是实践破坏、扭曲、否定现实世界及其存在事物的功能。实践的解构功能,在物质实践来看,就是对象世界及其事物的被破坏、扭曲、否定;在精神实践来看,就是科学、伦理、艺术等意识形态及其精神产品的被破坏、扭曲、否定;在话语实践来看,就是主体间行动和语言交往及其意义的被破坏、扭曲、否定。[3]
对比安格尔和杜尚的同名作品《泉》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实践的解构功能对生活丑向艺术美转化的要求。安格尔用少女柔美的身体曲线与瓦罐中泻下的清澈水流这样优美和谐的形式来表现一种青春无邪的气息和况味,而杜尚却将一个从商店买来的男用小便池起名为《泉》,匿名送到美国独立艺术家展览要求作为艺术品展出。如果说安格尔在追求并创造着美,那么杜尚就是用水淋淋的小便池破坏、否定、扭曲着安格尔眼中和笔下的美,进而诠释出丑在现代艺术中的地位。2004年,在英国艺术界举行的一项评选中,杜尚的《泉》击败了毕加索的《亚威农少女》和安迪·沃霍尔的《金色玛丽莲》,被推选为现代艺术中影响力最大的作品。在小便器摇身一变成为艺术品的过程中,由于人们审视物体的角度发生了改变,原有的精神实践遭到了解构,使得原本不登大雅之堂的小便器变成了格调高雅的艺术品。
二、审美理想的颠覆推动着生活丑向艺术美转化
审美理想也称美的理想,是指审美主体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和审美活动中形成的、由个人审美经验和人格境界所肯定的、融合了特定历史文化传统的关于美的理想观念或范型。[4]审美理想是艺术家和接受者进行审美评价的最高标准。艺术作品中的一切美或丑、崇高或卑下、悲或喜,都需要接受审美理想的观照;也不管是否自觉,艺术家的创作和接受者的鉴赏总离不开审美理想的引导和调节。审美理想是引导艺术家创造艺术美和接受者欣赏艺术美的重要内部动因和力量。生活丑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在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实践过程中不断地生成和转化着。面对生活丑的流变,艺术家和接受者也不会无动于衷,他们关于美的观念或范型,对审美活动的观照方式和评价功能也都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古典主义美学认为丑的作品,在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美学那里却被认为是美的;现实主义美学认为丑的作品,在现代主义美学那里又成了美的。
20世纪以来,伴随着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和全球化浪潮的强劲冲击,商品经济以其巨大的诱惑和无坚不摧的威力攻城略地,使一直以神圣、高尚自居的审美也不得不放下自己的矜持,卖身投靠于商品经济的门下,成为商品经济的一部分。审美感性已经成为经济活动的载体,生活的审美化也以服务经济为目的,审美理想的背后更是隐藏着资本运作的规律。随着文化传统、社会语境、阶级身份等各种影响审美理想形成因素的消解,审美理想试图通过自身的照耀和穿透来否定丑以确证美成为一种谵妄。
审美理想的颠覆和迷失让更多的艺术家把注意力转移到对丑作自然主义的、不偏不倚的、纯客观的描写上,通过对丑的展览、玩味,甚至是维护来显示个体差异,博取人们的关注,既发泄了对传统审美理想的挑战和质疑,又获得了名誉地位和经济利益。“在现代社会里,艺术标准迅速堕落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人们追求地位和炫耀财富的心理所造成的趣味所致。艺术不再需要去发挥它们难于把握的审美功能,而是作为社会地位的标志被人们创造、购买和消费”。[5]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弥补艺术与现实、艺术与非艺术、艺术与大众之间的鸿沟。
三、艺术形式的异变推动着生活丑向艺术美转化
艺术内容与形式之间是相互规定的:一方面,一定的材料和内容要求并规定着相应的艺术形式;另一方面,艺术材料和内容又必须达到充分的形式化,融入艺术形式之中。在艺术美的创造过程中,形式对材料和内容的表现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朱光潜对此作过具体分析:“一般诗歌虽不必尽能催眠,至少也可以把所写的意境和尘俗间许多实用的联想隔开,使它成为独立自主的世界,诗所用的语言不全是日常生活的语言,所以读者也不至以日常生活的实用态度去应付它,它可以聚精会神地观照纯意象。……许多悲惨、淫秽或丑陋的材料,用散文写,仍不失其为悲惨、淫秽或丑陋,披上诗的形式,就多少可以把它美化。比如母杀子,妻杀夫,女逐父,子娶母之类的故事在实际生活中很容易引起痛恨与嫌恶,但是在希腊悲剧和莎士比亚的悲剧中,它们居然成为极庄严灿烂的艺术意象,就因为它们表现为诗,与日常语言隔着一层,不致使人看成现实,以实用的态度去对付它们,我们的注意力被吸收于美妙的意象与和谐的声音方面去了。”[6]
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20世纪的艺术形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在机械复制作品盛行的时代,传统艺术的“光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审美的泛化或者说是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当日常生活中的吃、喝、住、用、行堂而皇之地走进艺术圣殿之后,生活丑也堂而皇之地走进了美的范畴,并且受到现代艺术家们的礼遇。在现代艺术与传统艺术分庭抗礼、各展其能的过程中,现代艺术以其重新组合、复杂多变的形式敲击出时代的旋律,并凭借着对生活丑全面艺术呈现所带来的视觉冲击和感官快感确立了自身的存在。以20世纪最后20年的中国小说为例,有从叙述技巧到叙述策略都发生变化的“现代派”、寻根文学、先锋小说和新写实小说;有注重语言调侃和个体经验的“王朔”、“王小波”和新生代小说;更有全面冲击情节设置、叙事风格和审美价值的影视剧本和网络文学。不断革新的文学形式让作家们更多地关注区别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的异常丑陋、病态的人物形象,更多地关注给当下这个世界带来矛盾、困惑、生存危机的生活丑。
雨果说过,“美只有一种类型,丑却可以千变万化”。丑是美学发展史上的催化剂,审丑能力的提高标志着人们审美能力的健全。20世纪,丑不再仅仅是美的陪衬或美的对立面,它成为在美学史上与优美、崇高、悲剧、喜剧、荒诞等并驾齐驱的审美范畴。需要明确的是,我们关注丑在美学中的意义,并非鼓励对丑的病态追求和嗜痂成癖。我们思考生活丑进入艺术表现领域并转化为艺术美的动力机制是为了进一步丰富自己的审美视野,理解现代文学艺术的深刻内涵,从而建构起辩证的、发展的美学范畴体系,让美的世界看起来炫彩纷呈。
[1]周纪文.论丑在美学发展中的意义[J].文史哲,1995(4).
[2]蒋孔阳.美学新论[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3]张玉能.新实践美学论[M].人民出版社,2007.
[4]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第四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5][美]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2.
[6]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3卷)[M].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