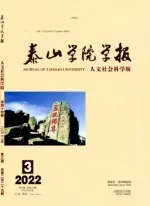论遗体捐献自我决定权与近亲属决定权的冲突与协调
刘 欢,张 宏
(1.福建师范大学 法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2.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河南 洛阳 471000)
现代医学技术以及医学理念的发展让普通人可以在其死后通过捐献遗体和器官来继续完成其造福他人及社会的愿望,他们的这一愿望是高尚的义举,是无私奉献的利他主义和互帮互助的集体主义的集中体现。然而我国目前遗体捐献概率较低,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传统“身体发肤,授之父母”思想的禁锢,即便有思想开明的捐献者,其捐献意愿很容易变成一纸空文,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为捐献者死者处理遗体近亲属的阻挠或者反对。死者的遗愿与近亲属对遗体权利产生了冲突从而阻碍了遗体捐献的执行。我国将来的遗体捐献立法必须对这一问题予以重视。
一、遗体捐献自我决定权
遗体捐献的自我决定权指的是自然人自由的决定是否捐献自己的遗体,不受干涉的权利。由于遗体的基本处分权来自死者本人,自然人对于自己死后的尸体有权作出处分,可以通过协议或者遗嘱,处分自己死后的尸体。台湾学者史尚宽先生认为:“死亡者生前关于其遗骸处分之契约或遗嘱,如不反于公共之秩序或善良风俗,为有效。”日本学者石原明提出,死者本人对自己死后遗体可以处理,其渴望自己生前的意思得到尊重,这属于生前人格权派生出的自我决定权。可以说,该权利是由自然人身体权派生出来的权利,是民法意思自治原则在遗体捐献领域的体现,是充分尊重公民行为自由的表现。目前,包括美国、德国、加拿大、比利时、新加坡等在内的世界大多数国家都通过立法对自然人遗体捐献自我决定权予以明确,例如《魁北克民法典》第一编“人”第42 条规定:“成年人可以决定其葬礼的性质和尸体的处置方式。”我国目前虽然没有统一的遗体捐献立法,但是部分地方立法有所规定。
二、近亲属决定捐献权
近亲属决定捐献权,是指在自然人生前未有捐献与否的意思表示的时候,在其死后近亲属得以决定是否捐献死者遗体的权利。我国《侵权责任法》以法的形式明确了近亲属对自然人本人身体享有的权利。该法第55 条规定了近亲属有决定是否在罹患疾病的亲属身上进行医疗措施的权利。其实,在遗体捐献领域,近亲属基于与死者的身份关系,取得对尸体的所有权。死者对尸体的处分权,就是来自于对尸体的所有权。有的学者认为,根据社会一般观念以及我国民事习惯,近亲属是与死者关系最为密切的人,死者是否有捐献遗体的意愿,与其共同生活的近亲属最为了解。赋予近亲属捐献与否遗体的权利同样是尊重死者意愿的表现,是符合民法构造的。史尚宽先生区分地认为,在(台湾地区)“解剖尸体条例”允许范围内,亲属之同意可以捐献遗体加以解剖。然对于移植,在法律未设有规定前,继承人不得为允许供移植之处分。可见,史尚宽先生并不反对近亲属作为捐献主体的,只是出于对传统伦理的尊重,认为在法律未明确规定前遗体不得为移植所用。
世界多数有遗体捐献立法的国家都规定了近亲属的遗体捐献决定权,如美国《统一组织捐献法》(UAGA)规定,除死者生前反对外,如果死者生前未做捐献的意思表示,死者亲属可以代为捐献;《越南民法典》第32 条第5 款规定,在没有死者意见的情况下,死者的父母,监护人,亲属同意,也可以进行解剖。我国《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第12 条第2 款规定:“生前未办理遗体捐献登记手续的自然人死亡后,其近亲属可以持身份证件办理遗体捐献登记手续。”
三、自我决定权与近亲属决定权冲突及表现
事实上,在自然人死后,其遗体捐献权的最终实现主要依赖于近亲属的积极履行。但是实践表明,大量的遗体捐献意愿得不到最终实现,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死者近亲属的阻挠,有些近亲属虽然为遗体捐献执行人,但是由于各种因素,拒绝执行的情况时有发生。
上文所述,遗体捐献自我决定权是公民行使支配自己身体权利在死后的延伸,而近亲属决定权来源于我国民事习惯,即近亲属对遗体所有权中的有限的处分权能。二者权利构造并不相同,但是二者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支配权能,并且支配权能指向的对象同为自然人遗体。支配权属于绝对权,是排他性的权利。笔者认为,权利冲突在所支配的内容相矛盾情形时才会出现。因此,遗体捐献自我决定权与近亲属决定权如果只有在内容上表现为不一致的话,才会发生此类冲突。冲突的表现主要有以下两种:
1.死者生前书面或者口头表示同意捐献,而在其去世后近亲属拒绝捐献而直接将遗体按照一般方式处理。这种情形较为常见。
2.死者生前书面或者口头表示反对捐献,死后其近亲属捐献其遗体。这一冲突实践上较少发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器官移植十大基本原则第一条,以及《赫尔辛基宣言》,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有立法明确规定了死者生前表示反对的,任何人都不得捐献其遗体或器官。
四、国外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关于权利冲突的立法
解决自我决定捐献权与近亲属决定捐献权冲突的实质就是发生意思表示冲突时,二者谁更优先的问题。
日本。1997年《器官移植法》第6 条第1 款规定,从尸体上摘除供移植的器官,必须有死者在生前以书面的形式表明同意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家属没有拒绝该摘除的意思表示时,医师方可为之,但没有家属的除外。因而按照日本国内这种规定,遗体器官捐献前提是,死者生前表明捐献遗体器官的意愿以及近亲属不反对的意思表示,二者缺一不可。可见,日本采取的是自我决定权与近亲属决定权等同的模式。
德国。《关于器官的捐献、摘取和移植的法律》第4 条规定:“如果被判定死亡的人反对摘取器官,则不允许摘取器官。当死者未作出捐献与否的意思表示时,经过亲属允许的可以摘取。”该条第2 款规定,亲属在决定前必须重视可能的死者的推测性的意志。德国立法以死者意思表示为优先的模式,只有死者生前未做说明的时候,近亲属才可以决定捐献,可见,近亲属意志是次要的,而且必须谨慎行使,以便准确地把握死者捐献与否的真实的意思表示。
美国。《统一组织捐献法》(UAGA)规定,死者生前表达的捐献意愿,其近亲属不得取消。美国很多州的法律都规定了本人同意捐献无需考虑家属意见。但在实际施行中,医疗机构仍然会征求家属意见,争取家属支持摘取。
罗马尼亚。1978年《器官移植法令》规定:死者生前由书面意见表示反对的,任何人不得为移植;对器官移植必须尊重死者亲属的意见,如从尸体中移植器官的,需要年满18 岁的亲属同意。根据这一规定,死者生前拒绝捐献意愿效力具有绝对性,除此之外都需经过死者成年家属的同意。即罗马尼亚采用的是自我决定权与近亲属决定权等同的模式。
我国台湾地区《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7 条规定摘取尸体器官可以:“(一)死者生前书面或者遗嘱同意;(二)死者最近亲属以书面同意者。”《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实施细则》第4 条规定了死者本人与最近亲属意思表示不一致时的处理,即死者最近亲属的书面同意,不得与死者生前明示之意思相反。我国台湾地区采用的是自我决定权优先的模式。
可见,国外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对于解决自我决定权与近亲属决定权问题有着两种模式,即一,自我决定权优先的模式,如美国、德国、我国台湾地区等;二,自我决定权与近亲属决定权等同模式,如日本、罗马尼亚、瑞典等。所有的共同点集中起来就是,只要死者本人生前明确表示反对,包括近亲属在内任何人都不得捐献,这是尊重与保障人权的精神要求。
五、解决冲突国内立法模式的选择
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8 条第2 款规定了公民生前表示拒绝捐献意愿的,任何人不得捐献器官。生前未作出表示的,其近亲属可以一致作出捐献的意思表示。可见,我国立法并没有明确死者生前表示捐献意愿,其近亲属表示反对时解决冲突的模式,即自我决定权和近亲属决定权谁更优先的问题。
笔者认为,无论是死者本人对遗体处分的自我决定权还是近亲属的决定权,两种决定权都是重要的,不能说哪一种更为优越。因为二者都有救助他人的善意,都应予以尊重。无论采取哪种立法模式,其目的必须是鼓励遗体捐献以及保障捐献各方主体的合法权益。“死者自我决定权优先的模式”并不能很好地解决权利冲突。因为自我决定权优先模式建立的基础是,死者处理自己未来遗体的意思表示在先,优先于在其后近亲属的决定权,其实质是排斥近亲属捐献决定权,这一模式未能看到近亲属对遗体享有的处分权,也未能考虑到实际的效果,因为遗体大多数是死者近亲属占有,未有近亲属的同意,捐献很难顺利执行。故将来立法可以参照国外“死者决定权与近亲属决定权等同”模式,以解决上述权利冲突,具体理由如下:
伦理方面。在遗体捐献未被大多数人接受之前,立法必须尊重民事习惯。在我国传统上,一般是死者近亲属为死者料理身后事,而且这料理过程必须符合当地的风俗习惯,否则这些亲属会被社会认为是对死者的不孝、不敬。近年来,虽然很多人认可了遗体捐献,但是不能排斥那些反对遗体捐献的观点。即使某个思想开明的人同意死后捐献其遗体,但也并不意味着法律必须强迫死者近亲属也必须“思想开明”地“公然”违背当地的丧葬风俗去捐献死者的遗体。何况近亲属本身就享有对遗体捐献与否的决定权。换个角度来说,试想在遗体捐献这一严肃的话题面前,将生者意愿都置于不顾而一味地遵守死者的遗愿的立法,显然未能达到“良法”的要求。
执行方面。实践上,死者近亲属如果表示反对,遗体捐献是无法执行的。遗体是承载近亲属的精神寄托,死者的逝去必定给生者沉重的心理打击。强制脱离近亲属对遗体的占有必然导致强烈的反抗,其导致的后果不堪设想。我国《行政强制法》第5 条同样也规定:“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应当适当。采用非强制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设定和实施行政强制。”行政强制执行必须合理性原则。实践上大多数接受机构所用的方法是耐心的安慰、劝说与教育死者近亲属后才得以顺利接受遗体,也免去了接受机构的后顾之忧。故遗体捐献必须尊重死者近亲属的意愿才可以顺利进行,不得强制执行。
有学者认为,目前能够有自愿捐献遗体的人已经为数不多,如果又需要其近亲属的同意,那么必然大大降低遗体捐献的概率。对此笔者不予认同。第一,如果死者生前登记表明捐献意愿得到了近亲属的认可,在死者百年之后接收遗体工作将会比较顺利的进行;第二,即便捐献人生前其近亲属对其遗体捐献不予认可,但由于捐献人更了解其近亲属的心态与思维方式,可以更好地与其沟通取得其同意。这一效果当然优于接收机构在死后与死者近亲属进行沟通的效果,也可减少沟通的难度与阻力,从而提高捐献的概率。第三,假如近亲属在死者身后表示拒绝捐献的,依据“等同模式”观点,接收机构无权仅仅依照死者意愿摘取尸体器官,只能通过耐心劝说、教育、鼓励其近亲属捐献死者遗体器官,并且接受近亲属的监督,不得任意处置遗体,这本质是对近亲属决定捐献权的保护,免去了捐献人生前担心自己遗体可能被捐献机构任意处置以及其近亲属反对的忧虑,也免去了其近亲属的后顾之忧,同样也可以减少沟通中的阻力,提高遗体捐献概率。其实施效果远远优于自我决定权优先模式。
其实,国内大多数地区的遗体捐献接收机构采取的是近亲属与死者共同表示同意捐献的做法。如《广州市志愿捐献管理暂行办法》第8 条规定,捐赠人生前填写捐献申请表时,应征得直系亲属的书面同意。广州市规定近亲属与死者本人共同的意思表示才产生遗体捐献的法律后果。广州市是目前我国遗体捐献接受机构最多的城市,也是我国遗体捐献概率较高的城市之一。
“等同”模式的实质是死者与近亲属意思表示没有优劣之分。二者“等同”是意思表达上的效力,即二者意愿一经合法表达即发生法律效力,谁也无法取代谁,只有权利内容一致时,才可以进行遗体捐献,这样既尊重了死者的遗愿,又照顾了近亲属的意愿。当二者意思表示内容相冲突时,遗体捐献不可执行,当然也无法执行。此时只能按照传统习惯处理遗体。
[1]杨立新,曹艳春.论尸体的法律属性及其处置规则[J].法学家,2005,(4).
[2]史尚宽.民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3][日]石原明.医疗、法与生命伦理[M].东京:日本评论社,1997.
[4]熊永明.尸体器官或者遗体捐献涉及的法律问题[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4).
[5]刘长秋.器官移植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6]周君华,李明月,李慧瑜,潘晶鑫,林泽怀.广州市民遗体捐献意愿及影响因素调查与分析[J].中国医学伦理,2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