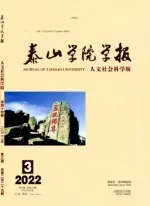荒野——人类最后的伊甸园——爱德华·艾比散文集《荒野独居》的生态解读
苏 冰
(泰山学院 外国语学院,山东 泰安 271021)
生态文学(eco-literature)也称“自然写作”(nature writing)或“环境文学”(environmental literature),是20 世纪下半叶在美国文坛上兴起的一种新的文学流派,包括虚构文本和非虚构文本两大类。诸如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约翰·穆尔(John Muir)、约瑟夫·伍德·克鲁奇(Joseph Wood Krutch)、阿尔多· 利奥波德(Aldo Leopold)、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安妮·迪拉德(Annie Dillard)等作家立足于以“伊甸园”与“新大陆”闻名于世的美国土地上,以自然为主题,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展现出描写自然与人类心灵的一道亮丽的风景。著名的美国当代环境文学批评家斯科特·斯拉维克(Scott Slovic)[1]指出,美国生态文学包括以表现人与自然关系为基本内容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该类作品反映的是个人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对人类和自然所表现的责任意识。具体地说,人们今天广泛使用的“环境文学”这一术语涵盖了以表现人与自然关系为内容的所有文学形式(口头文学、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生态文学家和生态文学研究者要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人类在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出了什么问题,才导致了如此严重的生态危机?自然与人的关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人类到底应当怎样对待自然?人类如何才能力挽狂澜?美国生态文学作家爱德华·艾比在他的成名作《荒野独居》中对这些问题给予了回答。在该部作品中,艾比对惟发展主义批判和对世界生态文学和西方环保运动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他独居沙漠的生存方式和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一直是读者和评论家热衷于讨论和争议的话题。
爱德华·艾比(Edward Abbey 1927—1989),被称为“当代的梭罗”①,自称独居于犹他州沙漠里的“仙人掌爱德”②。他以梭罗为偶像,继承并发展了爱默生、惠特曼、缪尔等美国近现代生态作家的生态思想,承袭利奥伯德关于“土地伦理”的观点,高举生态保护的大旗,提出了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模式,即对立——妥协——平衡,并将自己的大半生都奉献给了美国西部的荒漠。《荒野独居》③(Desert Solitaire)于1968年出版,作为艾比最著名的散文集,该书因毫不妥协地为西部地区的荒野存在而大声疾呼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并使爱德华·艾比一举成名,标志着他真正成为一个生态文学作家。全书共分19 章,描写了艾比独居于荒漠的见闻感受,展示了伊甸园一般美丽的荒野生活,表现了作者与荒野中的自然万物的和谐关系,抒发了他对大自然的热爱,表达了他对工业和旅游给自然带来的危害、现代化的弊病、惟发展主义等问题的深刻思考。
这部散文集以美国西部犹他州阿切斯国家公园④里的沙漠为背景写就,作为一部生态文学的经典之作,成为美国新文艺复兴的标志。此书经久不衰,多次再版,并被译成德﹑法﹑日等多种语言。文学评论家哈里·米德尔顿说:“每当被问及我们是怎样了解荒野时,当然我们要首推艾比留给我们的那些永恒而珍贵的荒野影像。虽然它们是纸上的字,但却像碑文一样永存。”[1]美国自然文学作家及评论家唐·谢斯(Don Scheese)视《荒野独居》为“美国对世界文学的最大贡献之一”,并追随艾比大量时间也居住在荒野,把研究自然文学作为自己的职业。在他眼中,艾比居住的沙漠是“一个与荒野更贴近的自然环境”;而艾比成了他眼中“一个言论更激进、更无视偶像的人物”[2]。这部散文集中既有作者在沙漠和荒野中探险的经历,也有他对现代文明的批判性思考;既有他对自然万物和谐生存的观察与赞美,也有他在沙漠中的生存体验;既是一位观察者和探险者的手记,也是一位公园管理员和生态主义者的思考日志。
一、荒野,人类诗意的栖居地
艾比大半生在美国西南部犹他州阿切斯国家公园的荒漠地区度过。《荒野独居》描绘并赞颂了该地区植被极为稀少的沙漠戈壁。在他的笔下,他所独居的阿切斯国家公园“是地球上最美丽的地方”,“是世界的中心,上帝的殿堂”,是“伊甸园”。他喜欢荒野,因为“荒野比高山和大海更具吸引力,更为变幻莫测,也更具有想象力”;“它看起来纯洁简单,但同时却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沉默静止的荒野引起我们内心难以捉摸的感觉,就像一个我们不知道也不可知的谜底即将被揭开一样”[3]。在《峭壁玫瑰和刀》、《午间炎热:岩石、树和云》等篇章中,艾比细腻地描绘荒野中观察到的事物:荒野不是常人想象中的荒凉与贫瘠,而是神圣的,富有独特的魅力的风景,这种美好是神秘的,与任何世俗的物质的实用主义无关。荒野令作者如此倾心,不仅仅因为其景象的壮丽,还因为其中氛围的和谐与安宁。所有的生物都按照自然的法则生老病死,接受“物竞天择”的考验。人类与动物也可以按照生命的原始状态和谐相处。在《乐园中的蛇》中,艾比就以其亲身经历描绘了他与牛蛇的和谐共处:
牛蛇和我相处得很融洽。……我把他拿起来搭在胳膊或脖子上,他毫不抗拒。带他到户外的寒风和阳光里,他却更喜欢躲在我的衬衫里面,盘在我腰上,歇息在我腰带上。有时他也会从我的衬衣纽扣中间探出头来,观察一下天气,这情景让那些碰巧看到的游客惊讶和欣喜不已。他的蛇皮干爽而光滑,摸起来很舒服。当然,作为冷血动物,他的体温是从周围环境获取的——在我身上时就从我身体获取。我们就这样和谐相处。我认为,我们互为朋友。[3]
他抚摸“干爽而光滑”的蛇皮,牛蛇从他身上获取体温,牛蛇不是他的宠物,而是“互为朋友”,平等共处。这幅场景是许多生态主义者理想的境界。美国著名的生态哲学家纳什指出:“爱德华使一代人认识到,荒野不是一片空寂、荒芜之地,相反,恰巧因为是荒原它才富有价值。《荒野独居》出版后,美国年轻人不再热衷于塞拉(Sierras)风景区⑤,而纷纷涌向布满平滑石的大峡谷地区,在新的地方发现了美景和野趣。”[4]可见,《荒野独居》改变了人们对荒野的看法,拓展了荒野自然美的内涵,使人们认识到自然本身的存在就是意义,她并非人类宣称的那样,是作为人类的工具而存在,也不需要依赖于人类的存在而存在。在自然世界中,万物自觉地遵循着其中既定的法则和秩序。自然不仅不必依赖人类观念而存在,而且她与人类本应是和谐相融的。现代社会物质文明给人类带来的精神上的空虚和极度的不自由感更是有赖于自然的抚慰和弥补。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保留一片纯净的荒野之地也是对人类文明和精神的呵护。
艾比进一步提醒人们:人类应该摒弃那种高高在上的对待自然的态度,以一种平等、真诚的态度去直接地接触、感受并参与自然。这种对自然的认识和接触并非超验主义和浪漫主义所倡导的那种脱离了自然的观察和想象,而是地质学意义上的、真真切切的接触,[1]艾比终其一生的荒野独居正是对这种观念的实践。只有那些实实在在地踏入科罗拉多高原的人,才能欣赏到那美妙的风景。一位作家,惟有拥有了真切的经验,才能够对风景尤其是美国西南部的风景进行判断。在荒野这个远离现代科技文明和物质追求的地方,没有现代人早已习惯了的一切舒适、优越、便利的生活条件,但是,生存条件的艰苦并没有让艾比退却,相反,在野外独居的所有时间里,他始终都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去接受荒野中凶险的挑战,自足自乐地独处思考,沉醉而忘我地享受荒野乐趣,让精神与灵魂得到充实和完善。正是因为对自然这种极度真诚的接近和感受,在艾比的这部作品中,才随处都可读到他对荒野饶有情趣的描写:
在瀑布下面的水塘边做了几天梦,像亚当一样在棉白杨树下裸体漫步,巡视我的仙人掌园。日子变得原始、奇特和费解——一种原罪的因素弥漫在流动的时间中。在似醉似幻的时光里,像道家的庄子梦蝶一样,我也挂念着蝴蝶。那里也有一条蛇,一条红蛇,住在泉溪的岩石间,我总在那里灌满我的水壶,每次去的时候它都在那儿,或是在石间滑来滑去,或是停下来用它充满暗示的舌头和朦胧、不安、原始的眼神迷惑我。[3]
这是伊甸园一般的荒野生活,匪夷所思而又梦寐以求,人与自然生物密切接触、和谐共生。艾比作为一位自然之子完全没有文明人对自然的俯视姿态,而是以一种极高的神圣感去感受自然的本真,这是一个孩子对母亲出于本能的尊重与爱戴。
正如教堂是人们精神活动的场所,荒野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失去了荒野就失去了精神家园;“荒野绝不是人类精神的奢侈享受,而是必不可少的东西,它对于我们的生命就好像水和好面包一样至关重要。文明毁灭了荒野中剩余的那点空间和原始性,从文明自身的根源中剥离出来,背离了文明本身的原则”;如果工业社会的人继续扩大工业化导致荒野消失,“他最终会感到一无所有的痛苦和苦恼,会理解那些背井离乡的印第安人为怀念家乡所作的歌曲的含义。”[3]
荒野也是人类文明的根基,失去了荒野的文明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失去了荒野的人,无法过上真正意义上的人的生活。一切与现代文明为一体的喧嚣和躁动,一切因盲目追求却又因追求不到而导致的压抑与不平,在自然世界里都会渐渐消褪,随之而来的是灵魂的安宁,是思想的空灵,是对生命真谛的感悟。因此,荒野是日益精进的人类文明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也是人类诗意的栖息地。
二、荒野,人类曾经的家园
阿切斯国家公园及其周边这一极度缺水的沙漠地区,是由包括人在内的动物、植物及其生存环境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命运攸关的生态共同体。在这一共同体中,动物和植物之间既存在着弱肉强食的关系,又存在着“典型的互利互惠的”共生关系:丝兰的授粉过程“是在一种飞蛾的帮助下完成的”;“飞蛾适时地将卵产在丝兰花的子房中,其幼虫在生长过程中一直以丝兰籽为食,但它会留下足够的籽,供丝兰繁殖用;为报答养育之恩,飞蛾产卵时会把另一棵丝兰的花粉传递给雌蕊”。动物之间既有吃与被吃的食物链关系,又有和平共处的关系:沙漠中隐藏着几个清澈的水塘边,“晚上,哺乳动物也来光顾,鹿、山猫、美洲狮、狼、狐狸、长耳大野兔、大角羊、野马,还有野驴,每种动物都依照同样顺序先后轮流,相互间还宣告休战;它们是来饮水的,不是来杀戮或被杀戮的”。艾比认识到,自然生态中的生命体既要生存,又允许他者生存,否则生命体自己的生存就成了问题;而且,人只不过是生态共同体中的普通一员。因而,他以管理员的身份在阿切斯国家公园独居时,就努力使自己融入该地区的生态共同体,并竭力维护其原生生态。他写道:“我已经融入这个世界。这里的所有生命都息息相关,杀手与受害者,掠食者与被掠食者,我和狡猾的草原狼,高飞的秃鹰,优雅的牛蛇,胆小的棉尾兔,以及我们体内的寄生虫,等等,所有这些生命都将永存。物种多样性万岁!地球万岁!”[3]
艾比的笔下,荒野是矛盾的集合体,它不仅是壮美的景观,亦不仅是可怕的死亡之地。荒野这个伊甸园“不仅意味着苹果树和美貌女人,也意味着蝎子、鸟蛛和苍蝇,响尾蛇和希拉毒蜥,沙尘暴、火山爆发和地震,细菌和熊,树形仙人掌、丝兰、木槿、蔓仙人掌和牧豆树,暴洪和流沙,当然,还有疾病、死亡和腐肉。伊甸园并不是一个永远完美的极乐园,狮子不会像绵羊那样躺着(不然它们吃什么?)”[3]。自然是复杂多样的,艾比并不像传统作家那样,把欣赏自然景观当作获得感官愉悦的途径,或者把自然当作寄托思想情感的载体,而是要真实地感受和传达复杂与神秘的生态之美,把自然万物的生存权利看成自然天赋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他把万物都当作他的兄弟姐妹,当作大自然家庭中的一员。艾比眼中的自然是一个与万物共存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无论是人类还是非人类,是动物还是植物,都有思想、有意识、有情感、有爱憎、有喜恶:
拒绝对所有的动物(除了人和狗) 给予任何形式的感情是一种愚蠢、鲁钝的理性主义……我甚至认为,许多非人类的、未受驯化的动物有着我们所不知道的情感体验。郊狼望月长啸是什么意思? 海豚如此真诚地在向我们倾诉什么呢? 当那两只狂喜的牛蛇穿过沙岩溜进我的视线时,它们是怀着怎样的一种想法呢? 如果当时我能克服极易恐惧的本能,尽量给予它们信任,那我就一定能够明白一些从未知道的道理,或者说真理。这些真理其实非常古老,却早已被我们忘怀。[3]
既然所有的生物都拥有生存权,而人类和其它生物都是自然这个大家庭平等的成员,那么人类自身的利益就不是衡量一切的惟一标准,也不是最高标准。艾比认为,人类应该学会以生态系统这个整体的利益为终极尺度来反思、约束自己的行为。当人类的利益与非人类的利益产生冲突的时候,人类可以也应当牺牲一些自我的利益来成全生态整体的利益,因为只有生态系统的至高利益得到维护,人类和其它生物的利益才可能实现。生态系统不仅包括整个人类,还包括所有的动植物甚至树林﹑山川﹑河流和土壤中的微生物等等。[5]艾比不仅认为动物和植物与人一样有着生存的权利,而且还把无生命的自然物也视为富有生命的有机体。他极力反对现代社会仅仅从发展经济出发,无视自然,肆意改造自然的行为。在《顺河飘流》一章的开篇他便写到:“海狸们不得不另觅去处了,(人类)又要在科罗拉多河上修建另一座该死的大坝。”他指出:政府修筑大坝主要是为了经济收入而几乎没有考虑大坝的生态环境问题。例如多少动物会无家可归甚至濒临死亡;被大坝截断的河流将永远消失以致那美不胜收的沿河风景也随之化为乌有;峡谷里的古代文明遗址也会被无情的大水永远埋葬……他不禁发出感叹“格兰峡谷⑥是有生命的,它的地位无可取代,人类对它造成的破坏(在峡谷修筑大坝)也是无法恢复的”,“虽然我只是看见格兰峡谷的一部分,但也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它是一个伊甸园,是地球上最早的一片天堂”[3]。
荒野是人类曾经的家园。在漫长的文明进程中,人类遗忘了我们与自然万物本是一家的事实,丧失了与它们相互信任并进行交流的能力。人类已远离了曾经的家园。
三、荒野,没有主宰者的家园
艾比生活的时代,是美国工业化突飞猛进的时代,是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是社会商品化的时代。缪尔笔下的“森林的教堂”⑦,已成为Ts.艾略特的长诗《荒原》中那“空荡荡的教堂,仅是风的故乡”[5]。人们精神的空虚、信仰的丧失以及与自然界的隔离,仿佛预示着世界末日的来临。这时候,艾比从美国西部的沙漠,向惶惶不安的现代人传送了一则信息:“在那里(荒野)有一个比我们人类更古老、更伟大、更深沉的世界,正像海和天围绕与支撑着一艘船那样,它正围绕和支撑着我们的世界。”[3]作为一个现代人,艾比最逼真地展现了美国之梦。当美国人面对与日俱增的消费主义和都市化的威胁而愤愤发问:“是谁给了你们权力来夺走我天空中的蓝色”时,艾比成了荒野以及人类自由的代言人。艾比的一生都在为荒野辩护,他曾经激动地宣称:“保护野生动物是一个道德问题。所有的生物都是生来平等的……为没有声音的生物代言是人类的责任。”[3]
作为“当代的梭罗”,艾比在继承梭罗等人的自然文学传统基础上,提出了关于自然与人类和谐共处的对立——妥协——平衡的理论,他把19世纪自然文学中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然观,发展为以生态为中心的自然观[5]。他把以随意破坏自然为代价的盲目增长,视为对现代文明本身的背叛。艾比看到了野性的沙漠对人类及其文化的重要性。他认为“为发展而发展是癌细胞的疯狂裂变和扩散”,盲目的增长与发展就像癌细胞一样威胁着人类社会。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人们进入了一种近似疯狂的地步,使人类与其生存的根基相脱离。“那种以摧毁仅存不多的野性的、原始的自然为代价的文明,实际上是切断了文明与其根基的联系,背叛了文明本身的基本原则。”继而他以人们在海上、山中、以及沙漠里的不同的感受和追求,说明沙漠对人类文明的特殊意义。“航行大海上,我们可以到达彼岸;攀登高山,我们可以到达山顶;但在荒野中我们难以找到类似的感觉,我们感到的只是无边无际的黄沙的‘漠然’”[3]。正是荒野这种不带任何目的性的“漠然”吸引了人们,这是一片独特的风景,一片人们可以从中获取对人类及宇宙的洞察力的特殊地带,一片人们用以对抗经济发展等疯狂行为的缓冲地带。荒野以其理智,引导现代人走出自相矛盾的山谷,以其广漠给急躁的人们以精神上的平衡,以其博大宽容给现代文明以新的启示。
艾比之所以能够如此深刻地认识到自然的内在价值,能够站到生态整体主义的高度去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完全是因为他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质疑和超越。他以一个非常简单的比喻批判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将自然界视为我们的财产、我们的领地、我们的管理对象,这种观念无异于一个儿童视自己为世界的核心,仿佛别人活着的目的仅仅是为他服务。[3]
艾比以坚决的态度否定了人类的中心地位,颠覆了传统的人为主体,自然为客体的观念。他坚持认为:人类不能以主宰者的优越感去审视自然;自然不需要人类的确证而自得地存在,但是人类却必须以自然为参照物和学习的对象创造自己的文化和社会。自然本来就是万物所共有的,在荒野中,那些安然自得地生活着的动植物才是真正的主人,人类不过一个外来的侵略者:
走进冰川公园,你就像是走进了灰熊的家里。我们是不速之客,是侵略者,熊才是我们不愿认可的主人。只要他愿意,随时都可以把某人赶到树上去,或送往去医院的路上,这乃是它天赋的特权。而那些想变得更文明的灰熊,因为没有利用这种特权就注定要被抓到迪斯尼乐园,被训练出五花八门的扮相和模样。[3]
艾比将荒野与人类自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告诫人们,一旦荒野失去了,人们的自由也将受到威胁。艾比认为:“真正的人类自由、政治、经济和社会自由,从根本上来讲是与人身自由紧密相联的。它需要足够的空间和土地。”对艾比而言,除非人们走近沙漠与河流,除非他们行走在荒野这幅古老、原始辽阔而民主的远景之中,否则,他们将“永远无法理解‘自由’这个词的真谛”。所以,艾比视保护美国最后一片荒野中的“伊甸园”为自己义不容辞的使命。他把对荒野和自然的破坏提高到了宗教的高度:“所谓原罪,真正的原罪,是那种对围绕着我们的自然天堂(假如我们还配拥有它的话)的贪婪与盲目的破坏。”[3]
艾比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向世人传达这样一则消息:“人有生有死,城市有起有落,文明有兴有衰,惟有大地永存”,培养人们“对我们星球的最基本的忠诚,对所有生物……甚至对我们脚下的岩石,对支撑并使我们存活的空气的热爱和忠诚。”[3]在生态现实危机重重的今天,在严重污染的环境里,我们听到艾比向人类吹响了号角:
如果一个人在饮用自己国家的河水和溪水时都会担心害怕,那么,那个国家无论如何都不适合它的国民生活了。移民的时刻到来了,去找另一个国家吧,或者——以杰弗逊的名义——去创造另一个国家吧。[3]
四、结语
艾比及其创作深刻地改变了许多美国和其他国家民众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唤醒了人们的生态意识,激发起许多人为保护地球家园而行动。他的作品直接推动了著名的环保组织“地球优先”⑧的诞生和发展。在艾比看来,行动尤为重要,“荒野的观念并不需要保护,它惟一需要的是荒野保护者”[3]。艾比提醒我们,自然对于人类生存的重要性,如果人类继续不计后果地破坏自然,让人类心灵的家园不复存在,那么,人类的精神将无处寄托。
[注 释]
①在犹他利的绿河漂流多日写下了生态文学散文集《漂流而下》(1991 发表),书中的一章题为‘与梭罗一起漂流而下’,因为作者是手持一本第33 版的《瓦尔登湖》进入这次旅途的。对他而言,这也是一次与前辈梭罗进行心灵对话的旅程,也有人称他为“西部的梭罗”。
②爱德华·艾比把自己比喻为仙人掌,自称独居于沙漠的“仙人掌爱德”(cactus Ed)。仙人掌全身长满刺,暗喻他激烈地批判美国和整个西方的反生态文化,毫不留情地挖掘出导致人类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
③Desert Solitaire 的汉译,2003年海南出版社的译本是《孤独的沙漠》,程虹在其《寻归荒野》里译为《大漠孤行》,台湾译者唐勤译为《沙漠隐士》,厦门大学王诺教授建议译成《沙漠独居者》或《荒漠独居者》,笔者倾向于译成《荒野独居》。
④阿切斯国家公园坐落在科罗拉多高原之巅,这片高原沙漠一直延伸,从西科罗拉多穿过南部的犹他州、北部的新墨西哥州直到亚利桑那州。这里是美国本土48 个州中人口密度最低的地区,但却拥有美国最重要的国家公园。这里遍布超乎想象的丰富自然景观:山脉、峡谷、奔流的大河、巨大的山谷、悬崖、山丘、尖顶、山峰和延绵不绝的沙漠景观。
⑤塞拉冈景区是内华达州境内的齿状山系风景区。
⑥格兰峡谷(Glen Canyon)位于举世闻名的科罗拉多大峡谷(Grand Canyon)上游约100 英里处,格兰峡谷大坝兴建于1956年,1966年大坝及其电站工程竣工,拦截科罗拉多河上游建成的水库,即鲍威尔湖。
⑦美國早期环保运动的领袖。他写的大自然探险,包括随笔、专著,特别是关于加利福尼亚的内华达山脉的描述,被广为流传。缪尔帮助保护了优胜美地山谷等荒原,并创建了美国最重要的环保组织塞拉俱乐部。他的著作以及思想,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现代环保运动的形成。1868年3月,缪尔抵达旧金山的优胜美地,他被优胜美地山谷深深地吸引住了,他写道:“没有哪个人造的殿堂可以跟优胜美地相比,“优胜美地是大自然最壮丽的神殿”。
⑧是1979年在美国西南部兴起的激进环境主义组织,简称EF。受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奥尔多·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和爱德华·阿比的启示,一群行动主义者发誓:“保卫地球母亲,决不妥协!”
[1]程虹.寻归荒野[M].北京:三联书店,2001.
[2]Don Scheese,“Desert Solitaire:Counter-friction to 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The Ecocriticism Reader,eds.,Cheryll Glotfelty &Harold Fromm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6),pp.303.
[3]Edward Abbey.Desert Solitaire:A Season in the Wideness[M].New York:Ballantine Book,1971.
[4]Arne Naess,“Simple in Means.Rich in Ends”[A].in M.Zimmerman (ed.),Environmental Philosophy:From Animal Rights to Deep Ecology[C].Englewood Cliffs:Prentice-Hall,1993.
[5]王诺.欧美生态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