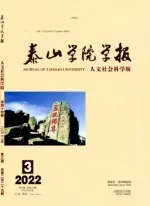生态批评空间的翻译生产
鹿 彬
(洛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河南洛阳 471022)
在现代中国,自从向现代化进军的号角吹响以来,我们就一直沉溺于一种焦躁急切的心态中,急欲改变民族以及自身的生存状态,“无所畏惧”地追求经济利益。正是在这样“贪多求快”的飞速发展过程中,由于过度强调“人定胜天”以及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使资源匮乏和环境污染成为我们都不得不面对的残酷现实。同时,“物化的时代”将一些非本真的东西制作得如此的炫丽和令人迷恋,致使追求物质的理想成为当下国人的生活目标和攀比的核心内容,这种追求物欲的不满足,严重影响了国民素质的提高。更为严峻的是,在网络媒介的推波助澜下,社会的公德意识正在淡漠,人与自然的不和谐现象层出不穷,人性扭曲的极端事件也频频爆发,血腥残忍的虐待动物、虐待他人、甚至自杀的过程在网络上现场直播,这样的现实,对于成年人尚且是巨大的精神刺激,更不用说尚处于青少年时期的未成年孩子们。青少年的成长需要一个和谐健康友爱的环境,在他们树立人生观、世界观的时候,整个社会给予他们的,不是最温馨的关爱和最轻松的氛围,而是“随处可见的危险”以及最大化的“追求物欲”的价值观潮流。如果说生态不和谐、人性扭曲以及经济利益最大化对教育、对学生的冲击仅仅是表现在大学开学大一新生必备的“苹果电子三件套”,那就是在原先的资源浪费和破坏环境的罪责上更加深了一重罪过——在教育的问题上只看和社会贡献价值最接近的大学生,而忽视了国家和社会未来稳固的根本,那就是现阶段正处于祖国花朵时期的青少年健康培育问题,即如何帮助新一代孩子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如何帮助他们避免成人后犯下我们此刻正在犯的错误,如何让他们具备让自己幸福生活的能力。
生态批评学者关注一切被边缘化的群体,包括一直处于“失语”状态的孩子们。面对主流文化,孩子们是“失语”的,面对校园文化,孩子们是沉重的,超负荷的课业,近视眼成片,小胖子成堆,自主学习的能力下降,为国家昌盛而读书的志向淡漠,取代的是孩子们之间趋于“成人化”的金钱、地位攀比以及德育的缺失,这样的社会现象,是我们学者,特别是生态批评学者必须在它成为社会洪潮席卷孩子们纯洁心灵之前,预先关注并思考该如何有限防御的重要课题。生态批评批判粗暴的工具主义和贪婪的功利主义不仅将物质的追求达到极限,还是精神的腐蚀剂,一种由“人工制造的思想化学毒剂”[1]。本文从生态批评的空间出发,探讨生态批评中的空间生产模式即通过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将国学养生文化译介到生态批评的空间中,把历经时空考验的国学文化译介成当代人能够理解和实践的行动指南,构建出一个健康和谐的空间出来,至少在生态批评的空间中,先给孩子们构建一个美好的心灵源泉,同时将中国养生文化译介到国外,和世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产生碰撞和共鸣,创造和生产出属于我国生态批评贡献的重要文化内容,这不仅是社会、文化、人类生生不息的重要举措,也是比较文学学者和翻译学者义不容辞的使命和责任。
一、生态批评的空间模式
生态批评自诞生之日起,就已注定要超越文学批评的藩篱,与社会批评、文化批评相互辉映,互相渗透。众多学者和批评家在现实使命感和理想主义的推动下,不断发展并努力完善生态批评理论,使之愈来愈成为当代文学批评和社会生活中一项重要的思想资源。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学者们在残酷的社会现实中不禁发出这样的疑惑——“科学”真的像我们“以为”的那样“科学”吗?特别是在当今,“科学”已成为少数人操纵多数人的工具,科学的化身也经常以主流人群为主,以强势为主,以男性为主,那么当代的文化反思,在我们生态批评的推动下,引发了一个关于将人文主义的分配和整合做出一个重新的分配和整合诉求。这就是本文探讨的关于生态批评空间及其空间模式、生产等相关的问题。
(一)生态批评的空间
生态批评的空间,是多元共存和社会秩序的空间。不管是探讨建设多元共存的和谐空间,还是探索稳固社会秩序的空间,都得将关注的视线放到“空间”这个概念上来。那么对于空间提出精辟解读的人,则是在扭转人们对空间的传统认识、重新界定(社会)空间概念的法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列斐伏尔,他的空间生产理念为生态批评学者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也是本文的理论基础。列斐伏尔不仅纠正了一百多年间关于空间是“容器”,是“空洞”的错误认识,提出“社会秩序的空间化”[2]。为了弥补由传统的二元论的不足以及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之间的对立带来的不足,列斐伏尔引入了社会空间的概念,并利用黑格尔关于“生产”的思想,形成了将物质空间、精神空间以及社会空间集为一体的三元化空间理论。按照列斐伏尔建构的社会空间类型,资本主义社会对应的空间是“抽象空间”,资本主义依靠不断占有新的空间,并在新生成的空间中生产出新的空间来维持自己的扩张并延续自己的生命[3];他指出,(社会)空间是一种社会的产品,每一个社会和每一种生产模式都会生产出自己的空间。而随着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发展,格局的划分愈发复杂,我们对空间的知识的了解有望复制这个空间的生产过程。如果说空间是一种产物,那么,我们对空间的了解和认识就是生产过程的复制和展示[4]。
生态批评是一种结合了社会历史语境的外部研究,而且随着女性主义批评和后殖民批评的兴起,批评家越发意识到自己有权利有责任以自己的研究为人类、社会,乃至地球负责[5]。因此,在生态批评的探索道路上,也必然存在着研究方向的修正和转向。例如,不管是在欧美,还是在我国国内,都出现了文学理论中主流阵营为文学研究者介入环境问题提出严厉的质疑,对于生态批评的立场,既说是环境保护主义的变形,又担心文学介入环境,是否会带来人文学科的滞后,比如说历史学、生态学、伦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基础都是以“人”学科为核心的,倘若消解“人”对自然的干预和影响,这些学科的建设将面临着怎样的考验和困境。而为了凸显自己的独特视角和批评方式,生态批评在最开始的时候,也总是借助关注环境问题的外衣,走着反理论的道路,将自己的这种批评视为一场声称文学具有用文字来表现或占领自然界潜力的思潮。但是,随着国内外兴起了大量的自然写作、自然诗以及绿色文学,涌现了解读经典作品中作者深深的渴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蕴涵的研究以后,时间告诉我们,仅仅用文字来解读和书写是不够的,我们必须面对的是一个亟待解决关乎人类生存的严峻问题。正是基于解决问题的共同心愿,生态批评学者们,在90年代的社会发展现实基础上,终于实现了一个认同,那就是现代化的进程已经不可恢复得改变了自然环境,环境日益技术化,这个事实已经不可改变和逆转,因此,现代的生态批评需要将自己定位于一种在后现代状况之中并对之加以针砭的干预力量。也就是说,生态批评需要为自己建构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实现生态的和谐的文化构建,实现对人类生存问题的反思和修正,对现在的社会问题能够给予精神层面的缓解和疗养。生态批评的空间,不一定必须做到带领全人类找到既支持现代化发展又有效解决环境、能源危机的终极目标,但是,生态批评的空间,一定是为了保护人类生生不息而努力探索的空间,通过启迪和干预作用构建出生态和谐文化空间,为了下一代的和谐健康成长,提供一个健康的、生态的、安全的理想空间。
(二)生态批评的空间模式
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生态批评有着显示本体特征和独特价值的主要任务,那就是通过文学来重审人类文化,来进行一种旨向修正的文化批判。这种批判的对象,由原来的探索人类文化与社会发展模式是如何产生危机形成目前的整体失衡状态的,明确到在一个生态批评的空间中,肩负人类生生不息重任的思考和干预作用。因此,生态批评的空间模式应该是开放式的、多元共存的、和谐健康的文化模式。在生态批评空间模式中,批评的视角投向不分国别不分种族的孩子们身上,在现在成人世界中从来就没有话语权的孩子们身上,探索影响他们走向恶性循环的根源;在孩子们早期教育中提前做到预警和指导,从而将当下我们这一代人可能还做不到、或者不够完善的修正工作,交付给可以担当重任的下一代手中去改造和创新。我们这一代的生态批评学者,将生态批评面对的种种问题,在现在的时空内设立一个空间模式,并在这个模式空间内,以是否有利于孩子们的身心健康为衡量标准,来生产、构建出新的生态空间。所有的生态的,和谐的,健康的存在方式,必定以人类物种绵延为衡量标准。在一个生态的空间中,在空间的整体性存在中,外在存在和内在存在并不是并列的两种存在,而是同一种存在的展开。当前的社会现实和环境危机是外在的存在,人类的和谐存在观是内在的存在;当前社会现实中的种种人类群体,不分国别不分种族,都是一个外在的存在,都是脆弱的表象,这个脆弱的表象的内在核心价值在于各自群体的子孙后代的健康繁衍。人的存在,在生态的空间视野下,以成人世界和孩子世界两种不同存在形式展开的。如果,不能保护和爱护好自己的子孙后代,又怎么能寄期望于这个群落会对其它的群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和谐共存呢?
福柯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焦虑主要是和空间有着根本的关系[6],而和时间关系不大。物理性的空间,凭着自身的构造可以构成一种隐秘的权力机制,这种权力机制能够持续不断地进行监视和规训。这种监视和规训,可以控制个体的身体,并将其生产成一个新的主体形式。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比较了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的规训与惩罚,发现它们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古代社会的规训与惩罚不可能达到全面操纵的极致效果,而现代社会则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机制,这些机制普遍地表现出一种密闭的空间特征——正是这种密闭的空间特性使得规训和惩罚成为可能,而现代监狱则是这种密闭的空间的极端性代表[7]。
现代化的发展的空间,正是按照所谓“科学”“理性”的结构建筑而成的,在这样的一个空间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控制主体,这种主体对空间中的所有个体形成约束和惩戒。这样的格局,对成年人来说,人性扭曲痛苦挣扎地生活,极端者则以虐待他人、虐待动物甚至虐待自己,从别人的或者自身的疼痛获得暂时的快感和释放。这样的空间格局,最终会形成福柯所描述的“密闭的、单调的、剥夺自由的‘监狱’”形式,那么,生活在这样“监狱”空间格局的孩子们,长期处于这种压抑扭曲的空间,能否做到我们所期望的“具备和谐生活的能力”和“保持乐观宁静的心态”呢。因此,为了避免恶性循环,生态批评的重任,不仅仅是研究文学文本中的生态哲思,更是要追寻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格局状态,从而引导人类正确的生活、生存方式。关注空间,关注空间中最重要也是最弱势的群体——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及其审美教育,是生态批评空间的重要内容。
二、生态批评空间的翻译生产
审美价值的生态尺度的生成性,使人类总是面对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终极关怀”[8]。生态批评的价值追求在不同的学术流派那里有不同的阐释,但是对于生态环境的关注,对于人类生存方式的反思,对于绿色家园的建设,却是高度一致的。尤其是绿色,对于生态批评来说,“具有永不衰败的魅力,它可能有益于人类的健康,因而它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一系列活泼的或低沉的、单一的或复杂的色调将由枝叶的绿色中分出,而在一种不可理解的奇迹之下,它们从来也不互相冲突或互相损害”[9]。人类破坏绿色的行为始终没有停止过,为了保护我们生命中珍贵绿色的呼吁也从未终止过。生态批评的空间中,更是一个绿色的园地,强调了人的心态、文学的形态与自然生态的关联性及其在空间的存在。因此,生态批评是一种独特的文学、文化批评,将文学文本以及多物种的审美平衡、生态平衡放在一个共同关注的平台上,那么翻译即是生态批评必不可少的解读形式,也是生态批评空间中重要的生产工具。
(一)生态批评空间的翻译模式
在《生态批评读本: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1996)的导论中,格罗特费尔蒂给生态批评下了一个流传甚广的定义:“生态批评研究文学与物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正如女性主义批评从性别意识的视角考察语言和文学,马克思主义批评把生产方式和经济阶级的自觉带进文本阅读,生态批评用一种以地球为中心的方法研究文学。”[10]对此,格罗特费尔蒂的解释是:生态批评的角度是这样的一些问题:这首十四行诗是如何再现自然的?物理环境在这篇小说的情节里起什么作用?这部戏剧所表达的价值观和生态智慧是否一致?我们关于大地的隐喻是如何影响到我们对待大地的方式的?我们如何能够把自然写作当成一种文类?除了种族、阶级、性别、场所应否成为一个新的批评范畴?男人的自然书写有别与女人的吗?文学经验本身以何种的方式影响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荒野的概念是如何随时间而改变的?环境危机以何种方式、何种程度上渗透到当代文学和流行文化中来?何种自然观充斥着美国政府报告、企业广告和电视自然纪录片,产生什么样的修辞效果?生态科学和文学研究有什么样的关系?科学本身如何对文学分析开放?文学研究与历史、哲学、心理学、艺术史、伦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环境话语如何可能相得益彰。”[5]
生态批评从科学研究、人文地理、发展心理学、社会人类学、哲学(伦理学、认识论、现象学)、史学、宗教以及性别、种族研究中吸取阐释模型。而在重读、挖掘和阐释文本过程中,翻译是跨学科、跨语言、跨文化的桥梁,也是实现人类统一视角思考问题的必要条件。同时,作为生态理念的呼应,生态批评不可能消极等待生态文本的完整出现,也不可能以某种精确、具体的尺度鉴别出所有的生态文本,它更倾向于一种生态主义的创作,即以生态主义阅读视角对经典作品的重构性创作。这种创作以生态主义的立场阅读、翻译甚至改写,并在这种阅读和创作形式中,发现、确认、建构和丰富自身的生态主义视野。生态批评视域的拓展需要翻译来解读和阐释,建立科学对生命终极关怀的目标,更需要翻译作为桥梁来实现生态批评理论的多元融合和自我超越。
(二)生态批评空间的语内翻译
生态批评的视域下,翻译活动无处不在。在弘扬中国国学经典中医养生文化的过程中,不仅仅是将中国文化译介出去,即实现文化的“走出去”需要翻译,从我国古老典籍中读出适合现代时代发展需要的生态哲思来指导现代人的生活品质,也需要翻译来实现,生态批评推动了语内翻译的新热潮。中国社会由于漫长的农业社会历史,使得传统的生态文化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在人与自然亲密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发达而又原始的文化心理。这就是中国的生态美学从人与万物和谐共存的关照中获得身心的诗意存在。而传统的中国养生文化和思维方式都大量保存在中医典籍之中。
以中医为例,作为一门系统的学科,中医具有自己的语言以及一套意义确切而且恒久不变的词汇。由于中医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中国古代哲学、心理学、天文学、气象学、逻辑学、养生学以及文化、宗教的影响,包括了这些学科的内容,产生了许多抽象的概念。把国学经典的中医文化介绍给当下的民众作为实践纲领,从而获得身心的和谐健康,介绍到国外,和世界生态文化形成一个系统的交流资源和宝贵文库,就涉及到两种的翻译形式,即美国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的“语际翻译”和“语内翻译”[11]。语际翻译就是两种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如英汉翻译;而语内翻译则是指同一语言中用一些语言符号解释另一些语言符号,如古文翻译成现代文。国学生态文化就是一种单向的翻译活动,即把我国传统的中医药知识及相关科研成果推广到世界范围之内,让更多的人了解、学习和研究中医养生生态文化,从而造福全人类之前,必须面对的一个严峻的问题,那就是语言自身的文化缺失。中医理论是建立在中国古代哲学,尤其是道家理论的基础上,大量的哲学用语进入了中医语言,而且很多的中医典籍都是用医古文写成的,深深地打上了中华民族的烙印,展示出了中医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样也给中医文化的传播带来了重大的障碍和繁琐。学习、研究中国特色的生态养生文化,不仅仅得具有“语际”之间翻译的能力,即使是同一个语种以汉语为交流方式,也得具备极为扎实的医古文、文言文的语内翻译功底。因此生态批评视域下,需要新的翻译研究领域为生态文化做出贡献,而翻译的结果,即是翻译的生产。通过翻译在生态批评空间中建构的新空间,就是翻译生产的空间。
三、结语
正如比较文学不仅仅只是“比较”和“文学”二者的简单相加。生态批评也不仅仅是“生态”和“批评”的简单杂糅。生态批评不仅需要多学科的交流和评析,需要吸取自然科学的具体研究成果,更需要立足生态哲学,对人类的文化模式、价值模式、社会模式等进行批判,为新型的人类生存模式探索出路。因此,翻译在生态批评的跨学科交流中,实现的语际之间的转换和交流,作用显著,同时,作为中国生态批评学者,还有一个重要的语内翻译重任,即,将中国古代哲学的生态思想,进行必要的语内翻译,把古文言翻译成现代人能够学习和领悟的现代思想,把散落的思想火花,以“片段”的方式进入当代生态批评的建构。而这个过程,就是在空间生产——生态批评空间中的翻译生产。
美并不是一个可推出伦理标准的范畴,而是人类对美的直觉产生能激发起伦理行为的某种关系。自然审美的体验为环境伦理的发展提供了有意义的支撑,从而可能纠正我们这个时代的文明偏颇。少年强则国强,且不说现在以追求分数的“量化”排序对孩子们身心的摧残,但说整个社会的发展潮流,价值观、世界观的导向,也不利于青少年发展健康的体魄,感悟前辈“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精神品质,从这个层面来看,青少年缺乏一个属于他们独立呼吸、自由发展的空间,因此,生态批评学者借助翻译的语内、语际翻译,将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带进现代人的思考中来,让自然界万物,无论是动物、植物等有生命的物体,还是山川、岩石等无生命的物体,都具有各自自身的“内在价值”和“审美价值”,我们在实现了对机械论自然观、人与自然对立的“人定胜天”盲目崇拜理念的批判之后,在生态批评空间格局内部,建立人与物种之间的生态公平、当代人之间的生态正义和生态文明,从而实现生态批评、生态美学的奋斗目标,实现人类“审美的生存”、“诗意的栖居”生存境界。
[1]鲁枢元.生态文艺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2]Rob Shields,Love and struggle:Spatial Dialectics.London& New York:Rutledge,1999.
[3]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生产[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4]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 - Smith.Oxford(UK),Cambridge,Massachusetts(USA):Blackwell,1991.
[5]张艳梅,等.生态批评[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6]MichelFoucault, “Texts/Contexts ofOther Space”,Diacritics,1986,16(1)(Spring).
[7]福柯.词与物[M].莫伟民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
[8]曾永成.文艺的绿色之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9][比]P.迪维诺.生态学概论[M].李耶波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
[10]Cheryll Glotfelty & Harold Fromm(ed.),The Ecocriticism Reader: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Athens: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66.
[11]申雨平.西方翻译理论精选[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