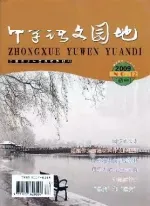亦真亦幻话人生——莫言小小说《奇遇》品读
柳 青
公元2012年底,莫言成了一个最热的词汇。莫言背后所代表的文化现象,引起了众多媒体的追捧。有人开始兴奋了。中国人的诺奖情结终于可以释怀了。各大书店网站开始大张旗鼓地宣传莫言的书籍了。文学终于开始扬眉吐气了。净化文学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当文化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喜剧已经散场了。文坛,依旧只有少数人坚守着热爱着。大众,其实并没有耐心去阅读莫言的那些动辄几十万的小说。他们需要的还是一种快餐文化。如今的读者太忙了。
对莫言的喜欢,并不是因为他的那些大奖,而是在他得奖之后的诸多言论:
“当代文坛没有出现大作家,才使我这样的人得以成名。”面对媒体大张旗鼓的宣传与造势,莫言保持了难得的清醒。有这样心态的莫言,是一定可以挣脱“诺奖魔咒”的。
“感谢那些支持我的朋友,也感谢那些批评我的朋友。我终于得到了一个把自己放在众声喧哗之中的机会。”面对众多网友的调侃甚至质疑,莫言表现出了文章大家的风范。在缺少大师却又到处自称大师的时代,莫言甚至说自己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而并不能说是作家。
莫言确实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他可以将故事讲的很长,几十万字,也可以将故事讲的很短,不到 2000字。 比如《奇遇》、《马语》、《放鸭》、《女人》、《井台》、《小说九段》,即使是这些小小说中,也可以见出他那一贯的叙述风格。信手拈来营建的氛围,不着痕迹勾勒的民风,曲径通幽描摹的传奇,魔幻现实主义的叙述,直达人性深处的拷问,倾诉着莫言浓浓的乡情,那清秀的乡野、善良的乡民、淳朴的民风,化为他作品中生动的场景、魔幻的风俗、变异的景致。这一切,成就了莫言所有小说的艺术魅力。
“1982年秋天,我从保定府回高密东北乡探亲。”因为莫言确乎有过这样的人生经历,所以,我以为,这篇小说所讲的故事很真实。
“路两边全是庄稼地,有高粱地、玉米地、红薯地等,月光照在庄稼的枝叶上,闪烁着微弱的银光。”这是作者熟悉的生活场景,熟悉的故土风物。这些场景的描写,进一步增添了故事的真实性。
“我感觉到路两边的庄稼地里有无数秘密,有无数只眼睛在监视着我,并且感觉到背后有什么东西尾随着我,月光也突然朦胧起来。”“儿时在家乡时听说过的鬼故事‘连篇累牍’地涌进脑海”,这样的生活体验,对于有过夜晚赶路的人来说,是那么的真切与真实。就如同在说自己的某一次生活体验一般。此时,读者会产生一种错觉,这不是一篇小说,就是一次亲身经历。叙述者、讲述者、读者,在这样的心理流程中,似乎是三位一体。真实与虚幻的界限消弭了。
人死之后,是否有灵魂,我以为这是一个无法解说的谜语。记得鲁迅先生在《祝福》中,借祥林嫂之口,讨论过关于灵魂有无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真的是一个说不清的问题。
《奇遇》之奇,不在于“我”一路上最怕碰见鬼的时候没有碰见,而在于以为没事了,曙光初现了,却碰见鬼了。小小说的精巧在于开篇的单刀直入,在于结尾的出人意料,这样的出人意料出于写作的需要,却又是水到渠成,天衣无缝。
《奇遇》之奇,在于作者将自己的善良愿望寄托在一个已经离世的赵三大爷身上。如今社会,我们看到太多欠债故意不还的情况。而死去的人借助灵魂偿还债务,而且唯恐惊扰乡亲,请不知情的“我”来代劳,这是何等的用心良苦?通过传奇化的叙事曲径通幽,把人情纯朴、民风乡约不着痕迹、不动声色还原出来。
《奇遇》之奇,在于前面的许多铺叙,都是在强调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读完两遍以后,依旧还是相信,这不是虚构的小说,而是一次真实的人生经历。我总是以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是两回事。不能将一些神秘现象都定义为迷信。因为,即使是自然科学,也有许多未解之谜,而人文科学的未解之谜带来了思想的交锋与学术的繁荣。
《奇遇》之奇,在于故事情节看似虚幻实则真实,看似真实实则充满神秘;在于作者用真实的手法写虚幻的故事,用虚幻的手法表达真实的情感。
《奇遇》之奇,在于读完这个故事,本不相信灵魂之说开始怀疑了,本是唯物者开始相信神秘。我不知道是因为作者的高明还是读者的思维混乱,但我想,这样的思维混乱也是因为作者叙事的高明。或许,这真是作者的本意呢。
“这么说来,我在无意中见了鬼,见了鬼还不知道,原来鬼并不如传说中那般可怕,他和蔼可亲,他死不赖账,鬼并不害人,真正害人的还是人,人比鬼要厉害得多啦!”
结尾的这段议论,似有狗尾续貂之嫌。留有余地,可令小说更有韵味。不需要作者帮读者思考,读者自会掩卷思考,开悟作者的良苦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