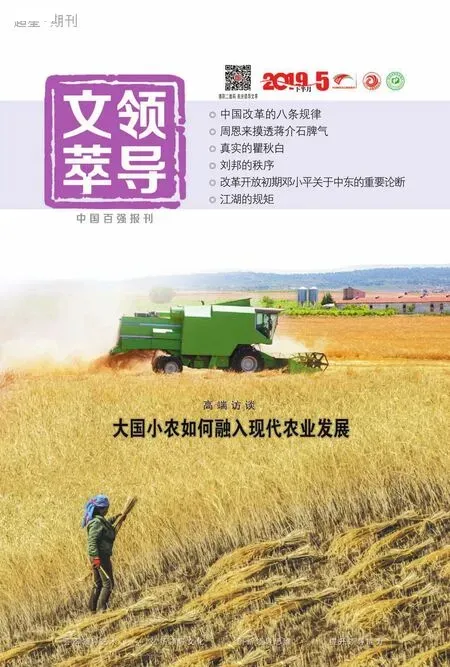唐太宗也无权看《起居注》
□邓忠强
古代的皇帝和大臣,他们对待历史的态度是怎样的呢?史书记载的唐太宗想看个人“档案”一事,让人颇觉意味深长。唐贞观十六年(公元639年)四月,某一天,唐太宗对谏议大夫褚遂良问道:“你近来又主持《起居注》,里面记了些什么呢,我可以拿来看看么?”
“起居注”是史官中的一种官职,其职能是专门负责记录本朝皇帝言行。这些载有“帝王言行”的史书,也叫《起居注》,堪称皇帝的“绝密”档案,连皇帝本人也是不能看的。正因为不能看,皇帝大都放心不下,生怕将来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所以对自己的行动就有所顾忌。如今唐太宗虽说创建了号称 “贞观之治”的盛世大业,但他还是担心自己有什么不良言行被载入史册,坏了一世英名。所以,他很想看看这本《起居注》,但又不好硬性地以 “皇命”行事,于是不惜向兼任起居注的褚大夫屈尊以求。
可褚遂良不给这个面子,婉言劝阻说:“现在的《起居注》,就像古代史官记录君主的言行一样,就是希望君主不做非法的事。还没听说过君主可以自己随便拿去看的!”褚大夫不卑不亢,话语柔中有刚。唐太宗听出这人正气凛然,禁不住又问道:“朕有不善,卿亦记之邪?”意思是说,我有不好的言行,你也要记下来吗?话中隐隐透出自己的担忧和不安,同时又似乎是在以君临天下的皇权来考验对方。
这无异于给褚遂良出了道难题,可他不假思索地答道:“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言下之意是,臣下不是不忠于皇上,但尽忠不如守职,职责所系,焉敢因为是皇上就可以一笔抹掉?他的应答从容而又干脆,可谓掷地有声,一点也不含糊。
这时,黄门侍郎刘洎插进一句话:“借使(即使)遂良不记,天下亦皆记之。”皇帝有过失,就像日食月食一样,每个人都看得见,即使史官不记,天下的人也都记下来了。以君主权威,如果硬要看《起居注》,甚至要篡改,那是容易办到的,但历史是篡改不了的。在“民心公论”和“历史道义”面前,即使贵如帝王者,又岂奈之何?唐太宗终于幡然醒悟,立刻打消了看《起居注》的念头,不得不承认:事实的确如此啊。
据吴兢《贞观政要·文史第二十八》记载,这件事之后,唐太宗有一次看本朝国史“太宗实录”,看到武德末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发生的“玄武门”事件,史官记载“语多微文”,文辞很多隐晦不明,就对负责编修国史的大臣房玄龄说:“从前,周公讨平了管叔、蔡叔的叛乱,使周朝得以安定,季友毒死了叔牙而鲁国太平。我做的事,大义与这些事相同,是为了安定国家,以利万民。史官执笔,何须隐晦?应当立即删除虚饰多余的文字,直截了当地把这件事的真相写出来。”
“玄武门之变”,是王朝内部兄弟间为争夺中央领导权的一次军事政变,在这场权力博弈中李世民虽然是胜者,但毕竟对兄弟开了杀戒(杀掉了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使龙椅宝座染上了腥红的血色。对这个最关键最敏感的事实,对自己以往的所作所为,唐太宗毫不回避,而是坦然面对,开诚布公,要求史臣以公正严谨的态度,“改削浮词,直书其事”,不能不说,他的责任心与道德,他的胸襟气度和求实精神,远远超过了常人的见识,不愧为真正的勇者、智者和强者。
看《起居注》,看国史“实录”这两件事,都表现了唐太宗对历史的尊重和敬畏。然而,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算得上一个明君,却认为司徒崔浩主持编写的《国史》,“暴扬”了“国恶”,使皇家面子很不光彩,一怒之下,竟然冤杀了崔浩。东晋中叶,史官孙盛作晋代史书《晋阳秋》,如实记下了桓温北伐前燕,在枋头遭到惨败的经过,大司马恒温看了后恼羞成怒,竟以“灭门之祸”相威胁,要他删改这段史实,但孙盛始终不为所屈。唐中宗时的史官吴兢撰写了《则天实录》,其中涉及到宰相张说的不光彩事,张说暗地里祈求吴兢改动几个字,吴兢就是不肯,说:“若徇公请,则此史不为直笔,何以取信于后!”
能否善待历史,实事求是,鉴往知今,是检验人们有没有正确历史观的一个重要标志。仅仅对历史“有所畏”,远远不够,这只是被动的一面;还必须对现实“有所为”,这才是主动的一面。惟恐自己在历史上留下人生的败笔,又能按美好的道德做人做事,因怕恶而向善,才是对历史最好的敬畏和忠诚?
毫无疑义,任何权力强势、投机取巧,都遮不住正义的光芒。看看树立了“盛唐丰碑”的唐太宗和他的臣属,他们对待历史的态度,难道不该作为今人的一面镜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