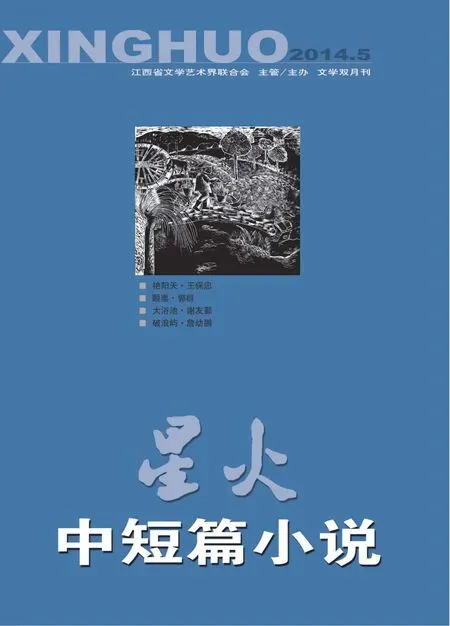何处是归宿
□常 君
天气好得出奇,阳光洒在身上暖洋洋的。德昌老汉敞着怀靠在一丘隆起的土堆上,惬意地眯着眼睛。旁边卧着与他形影不离的看家狗大黄。
身后的土堆高大结实,像一座小金字塔。躺在里面的是他的老婆子。老婆子撇下他走了整整四年了。这个地方是老婆子和他一起定下的。有一年的秋天,地里的庄稼都收完了,闲来无事他和老婆子一起到盘龙岭上来搂树叶。老婆子打量了一下四周,说,这个地方挺眼亮,有朝一日咱俩就到这儿来吧。老婆子走了,德昌老汉遵照老婆子的遗愿,把她葬在了这里。
这个地方有个规矩,新坟三年之内不许动土,也就是说三年之内不能添坟。今年是老婆子故去的第四个年头,清明节的前两天,德昌老汉率领儿子孙子上了山来,为老婆子添坟。添坟取土也是有讲究的,不能就近取土,添坟的土要到一百步之外去取,否则不吉利。儿子大顺没表现出什么,孙子志强听了却是一咧嘴。要知道,这可是个不小的工程,没个三十担五十担的土别想把坟添得像模像样。德昌老汉到百步之外选了一块土质肥沃的地儿,儿子孙子轮番挑了担子取来了土,德昌老汉一锹一锹把土添在坟上,然后用铁锹背儿一下一下把松散的土拍严实。开始德昌老汉上身还穿着他的灰色外衣,后来,灰色外衣从他的身上移到了树枝上。最后一项是挖“坟茔头”。这挖“坟茔头”可是项技术活儿,首先必须选草根密实的土,其次挖的时候还要注意锹的角度和力度,否则就散搂儿。德昌老汉走了好几处地方,才挑了一处比较理想的,先在四周散开一个盘儿,然后才一点一点转圈挖起来。那两块挖好的“坟茔头”是儿子和孙子搬走的。脸盆大小足有二三十斤的两块土盘儿,德昌老汉搬起来实在有些吃力。
坟茔的后面是一行槐树。西边的几棵是普通的洋槐,开白色的花;东边的是新品种,开的是粉色的花,一串串,一挂挂,白的像雪,粉的像霞。风儿吹拂过来一阵阵甜丝丝的清香,直往德昌老汉的鼻孔里钻。
老婆子活着的时候喜欢花,房前屋后巴掌大的地方也要见缝插针种上一棵花。到了这里后,德昌老汉怕老婆子嫌冷清,就从别处刨来了几棵槐树苗,又从山脚下的小河里担来了几挑水,栽了下去。几年下来,竟然枝繁叶茂,挂了满树的花。
清明节那天,德昌老汉在这儿遇到了北沟给人看风水的宗先生。一家人家要给父母立碑,请宗先生过来给度方向。宗先生忙完走了过来,巡视了一番,捻着胡须说,两山夹一岗,辈辈出皇上。后代子孙大富贵,科甲连登及第来。龙脉啊!不错!不错!德昌老汉没想到老婆子只是随口那么一说的地方,竟是块风水宝地。忙向宗先生问周详。宗先生便向德昌老汉细细道来。左右一边一道山梁,像椅子两边的扶手,后面横一道山梁,状如龙椅靠背。这样的风水宝地,日后定会荫及后代子孙,大福大贵。德昌老汉在心里盘算,这龙脉的福祉恐怕没荫及到儿子。他快三十了才得了大顺,以后老婆子就再没开怀儿。如今大顺已人到中年,和自己一样,老实巴交的一个农民,土里刨食,哪来的富贵当官命?倒是孙子志强那小子挺争气,今年大学毕业后刚考上了县里环保局的公务员,难不成日后会有发展,当个一官半职的?
听宗先生这么一说后,德昌老汉重新打量起这个地方。背靠青山,面临小河,山清水秀,视野开阔,倒是个眼亮的地方。没想到老婆子还有看风水的本事呢。他把宗先生的一番话对老婆子学了一遍。
俗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德昌老汉今年七十有三了,有人问起高寿,和他同龄的老哥们不是说自己七十二,就是说七十四,都忌讳说那个七十三,只有德昌老汉坦坦然然地承认。德昌老汉来这里的次数增加了,隔个十天半月的就会背着手弓着腰走上一趟。村里和他年纪相仿的几个老哥们都忌讳这种地方,更别提到这种地方来了。德昌老汉不在乎,人这一辈子最后的归宿都是这种地方,你忌讳,难不成那个期限就停住了脚步,不向你迈近了?
德昌老汉对这个以后的“家”满意的原因还有一条,那就是这儿的邻居。左前方不远的地方葬着德泰,比他小了两岁,去年快入冬的时候走的,坟上的花圈还没褪色呢。德泰的性格和他差不多,闷葫芦一个。但是闷葫芦归闷葫芦,那要看对什么人。两个人到了一起,春种秋收,家长里短,拉起家常来就是大半天。西北角是大翠他妈,活着的时候和老婆子好得恨不得两个人穿一条裤子,包个菜饺子也要颠颠给对方端过去一碗。不用说,在那边一定还和活着的时候一样你来我往,走动得热热闹闹的。他和老婆子在这儿都有各自对事说话的,以后串个门唠个嗑也方便。
今天上了山来,德昌老汉把“院子”平整了一下。春天来了,新发出来不少的野山枣刺儿,这东西没脸没皮的,今年刨了明年又发了出来。德昌挥起尖镐,把它们连根刨了出来,然后把坑洼的都填平踩实了。老婆子活着的时候爱干净,院子里经常扫得光溜溜的,一点戈能(东北方言:垃圾的意思)草刺儿也看不见。这里和自家的院子一样。不让动土的三年间,德昌老汉遵奉着不填土的原则,却每年都挥着镰刀,把坟上收拾得利利整整的,不像别的人家,坟上的草齐腰深。
不服老不行喽!德昌老汉扔下尖镐在心里慨叹。这才多少活儿,就腰酸腿乏,出了一身的汗。搁在年轻的时候,还不像玩似的。
德昌老汉靠在了老婆子的坟前,从怀里掏出一个豆腐块大小的铁盒,上面的漆已经掉得斑斑驳驳的了。德昌老汉打开盒盖,里面是一行排列整齐的烟卷,不过不是市面上卖的那种带过滤嘴的香烟,而是农村常见的那种手卷的喇叭筒。每年的春天,老婆子都要在房前屋后安排种两垄烟,移栽、浇水、打叉、晒烟,都由老婆子一手打理。收了烟后,老婆子把金黄的烟叶放在纸糊的笸箩里一点点揉碎,再把平时攒的孙子志强上学时的作业本裁成两指宽的长方形纸条,捏一点烟末放在上面,然后一点一点在一端用手卷成喇叭筒状,最后伸出舌头在喇叭筒的边缘舔舔,把纸条捻紧实了,一支喇叭筒就算卷好了。老婆子边卷边对他说,下地干活现卷费事,事先卷好了带着,掏出来就抽,方便。后期,老婆子的身子骨越来越差了,地里的活儿不能帮着忙活了,就坐在炕上给他卷烟。德昌老汉不知道老婆子为他卷了多少喇叭筒,老婆子过世后收拾东西时,在北地的纸盒箱内,德昌老汉发现了满满一塑料袋的喇叭筒烟。德昌老汉颤抖着伸出手,在那些粗细一致的喇叭筒上抚摸着。
德昌老汉从铁盒里拿出一颗喇叭筒,揪掉前端的拧着的纸阄儿,掏出火柴点燃,深吸一口,微眯着眼睛,表情显得很是舒服受用。
老婆子,我有个打算,说来你听听?我想在咱这院子的四个角各栽上一棵松树,宗先生说松树一年到头长青,能绵延子孙多福多寿;再一个我还想在四周栽上一圈矮棵的灌木,修剪成篱笆当做围墙,居家过日子没个围墙算怎么回事;通往山下的土台阶被山水冲得有些平了,我想重新修出一级一级的,上山下山走起来也方便……
德昌老汉靠在那儿,絮絮叨叨说着心中的规划。大黄好像听懂了似的,趴在旁边嘴里哼哼唧唧地应着。
老婆子你看怎么样?不错吧?到时候咱这地方要多美气有多美气!让那些老哥们眼热去吧!
德昌老汉筋骨舒泰地沐浴在阳光下,下垂的嘴角向上牵扯出一道陶醉的弧线。
阳光温热,岁月静好。德昌老汉眯着眼睛畅想着,竟然睡着了。
德昌老汉寻遍了盘龙岭的沟沟岔岔坡坡岭岭,千挑万选才选中了四棵松树苗。这四棵松树苗高矮适中,冠形周正,最主要的是根系发达,须子都有小手指头粗,一尺多长。德昌老汉很是满意,翻山越岭把四棵松树苗背了回来。挖树坑时,德昌老汉把树坑挖得很大,任何人见了都会说没那个必要。德昌老汉自有他的想法。他从远处背来了树根底下的浮叶土,这种浮叶土经过枯枝落叶腐殖发酵过,肥得很。德昌老汉把它们回填到树坑内,然后才把松树苗栽了进去,用脚踩实了,再在树苗四周垒上土堰,最后去山下河里挑来了水,小心地倒在土堰内,饱饱地把它们灌透。栽树的过程才算结束。功夫不负有心人,四棵松树苗全活了。
接下来德昌老汉修的是通往山下的阶梯。阶梯一定要先码上石子,然后再垫上土,否则到了雨季山水一冲又白忙活了。德昌老汉拎了篮筐,从山路两旁捡来不大不小的石子,码放整齐了,再铲些土铺在上面,然后用脚踩实。
这一工程德昌老汉用了将近半个月的时间。
这一天,最后一级台阶修完了。德昌老汉沿着阶梯上下检查了一遍,大黄跟在后面上蹿下跳。德昌老汉数了数,整整一百零八级。德昌老汉只是按照步子的距离大约摸修的,没想到应了个正着。宗先生说,佛家有一说,说人生有一百零八种烦恼,所以一般寺庙的台阶都会修成一百零八级。一百零八级台阶代表着一百零八个法门。每上一级台阶,就意味着跨入一个法门,解脱一种烦恼。德昌老汉沿着阶梯来到老婆子坟前,把自己的这个惊人的发现告诉了老婆子。他说,以后咱们就一点烦恼都没有了。
最后,德昌老汉要做的是修篱笆围墙。农村讲究这个,再困难的家庭,就是用高粱秸,用砖头瓦块,也要垒上围墙。围墙可以挡住外面的煞气,没有围墙就不是过日子的人家,是要被人耻笑的。德昌老汉考察了一番,觉得做篱笆最好用榆树。榆树抗旱,耐寒,成活率高,枝条绵软,利于修剪。再一个就是可以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山下小河边的榆树毛子有的是。
这天,德昌老汉吃过早饭,拿过一个塑料袋装了两个早晨吃剩的馒头,又灌了一瓶子水,这段时间以来,德昌老汉的午饭一直都是在山上解决。准备完毕,德昌老汉扛了锹镐出了家门,大黄雷打不动地跟在后面。
几个老哥们坐在大柳树下歇凉闲聊。以往,德昌老汉也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员。唠唠家长,聊聊收成,是他们这个年龄段最主要的任务。几个人见他走了过来,同他打着招呼,德昌啊,还去呀?这段时间早出晚归的,几个老哥们都知道了他的大规划。是啊,再有个一两天就完了。一个就说,我听说盘龙岭被人买去了,准备把山劈了,把山上的石头拉走填海。那片地方恐怕保不住了啊!真的?德昌老汉心里一紧。另一个说,都这么呛呛,谁知道真假。这时,村里的扩音喇叭响了,村长杨二壮大声小气地公布了这件事。德昌老汉扛着锹镐,登时就杵在了那儿。
对于这件事,村里人议论纷纷。有的说,好好的一座山,不能让他们说劈了就劈了,总得给子孙后代留点什么吧。另有消息灵通的就说,来这开山的是县里的一个企业家,政协委员,听说根基实力都强着呢。村里几个能说会道的联合起来去了村委会,回来说,这是镇里的决定。村长杨二壮也说了不算。
这两天,德昌老汉整天蹲在大柳树下打探着事情的发展情况。他真希望这件事能黄了。这天,扩音喇叭又响了。村长杨二壮宣读了迁坟公告,要求在一个月内把在盘龙岭上的坟墓迁出,否则按无主坟处理。还当场宣布,每户迁坟的,除了享受镇里的一千元补助外,县里的企业家还将补助两千元。德昌老汉树桩子一样呆呆地站在太阳地里。
大势已定,盘龙岭上有坟的,就去村委会签了协议,领了补助。
德昌老汉躺倒在了炕上。儿子大顺谨小慎微,见众人都去签了协议,回来同德昌老汉商量。德昌老汉面朝墙壁躺在炕上。隔了好一会儿,大顺才听见德昌老汉轻声说,去吧。
领了补助后,接下来就是迁坟了。大翠从县城回来,把她妈的骨灰盒挖出来带走了,说准备寄存在殡仪馆。德泰住在省城的大儿子也回来给他爹迁坟。德昌问他如何安置他爹,德泰大儿子满脸愁容地说,他每月就那几个退休金,老婆有病常年吃药,买墓地他实在承受不起,只能将他爹的骨灰海撒。说是一种文明节俭的殡葬方式,国家提倡,费用也不是很大。
德昌老汉知道,德泰大儿子说的海撒就是把骨灰撒到大海里。周总理、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骨灰就是实行海撒的。不过,德昌老汉闻听还是一哆嗦,好像要海撒的不是德泰,而是他自己。
其余的几家都是坐地户,在村里都有或多或少的土地,所以都选择葬在自家的地里。德昌老汉没有办法,也只好选择把老婆子安葬在他家耕种的责任田里。
德昌老汉是最后一个从盘龙岭上迁坟的。山脚下,开山的工程队已经进驻了,凿岩机轰隆隆整天响个不停。十二轮的翻斗卡车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向外拉着石方,巨大的车轮碾轧着地面,轰隆隆作响,像地震一样。不搬走老婆子的日子过得也不安生。
迁坟那天,儿子孙子都到场了。德昌老汉从墓穴内颤颤巍巍捧出老婆子的骨灰盒,无比心酸地说,老婆子,你看好的这个地方不让待了,咱走吧。
孙子志强接过蒙着红布的骨灰盒,祖孙三人沿着阶梯向山下走去。德昌老汉走在最后面。他回过头,四棵小松树苍翠葱郁,槐树枝叶茂密,在风中不舍地摇曳着。德昌老汉禁不住老泪纵横。大黄也回过头呜咽着。
玉米地的地头隆起了一个褐色的潮湿的小土丘。
德昌老汉家只有一亩责任田,在南平洼。以前是块水田,栽的都是水稻。后来因为连年干旱缺水,村里号召水田改旱田,就都种了玉米。玉米已经快一人来高了,大顺在地头割了半铺炕大的地方,将老娘安置下来。
摇曳的青纱帐渐渐掩住了儿子和孙子的身影。剩下德昌老汉独自站在土丘前。
老婆子,以后这就是咱的家了。唉,没办法呀!大翠她妈的骨灰盒被寄存在殡仪馆内,一人一个小格子,挤挤喳喳的,左右一个也不认识;德泰更别提了,听说海撒了。老话说入土为安,唉,咋就到水里了呢?这两天我总是梦见德泰,浑身上下湿漉漉的,冷得直打哆嗦……
这个地方没山上眼亮,可这里是咱家的地,咱自个说了算。这轮土地承包期延长到三十年,这才过去七年,还有二十三年才能到期呢。这回你就安安稳稳地在这儿待着吧。以后我一边侍弄庄稼,一边陪你说话……
德昌老汉站在土丘前叨念着。大黄立在一旁。
从此以后,人们常常看见德昌老汉背着手弓着腰,向南平洼走去。大黄跟在后面,东闻闻,西嗅嗅,见德昌老汉走远了,箭一般撵了过去。
玉米该追肥了。天气预报说明天有小雨,这时候追肥正是好时候,明天小雨下来,尿素融化了,正好吸收,一点也不会糟践。儿媳桂香要来,被德昌老汉挡下了。一个人推了独轮车,驮着尿素,追肥来了。
德昌老汉弓着腰从刀剑相错的玉米地里钻了出来,布满沟壑的脸上淌着汗,灰色的外衣后背上已经湿了,现出一圈圈白色的汗渍。追肥这种农活儿,人们一般都会选在早晨或者傍晚进行,阳光不是很强,相对来说比较凉爽。这个时候太阳已经很毒了,实在不是追肥的时候。大黄趴在玉米叶子垂下的阴凉里,伸着猩红的舌头,呼呼喘着气。
德昌老汉一屁股坐在停在地头的独轮车旁,拿起旁边装了凉水的瓶子,仰头喝了一气。水顺着敞开的干瘪的胸膛淌下来,德昌老汉撩起衣襟抹了一把脸,掏出装烟的铁盒,从里面拿出一颗喇叭筒,点燃吧嗒吧嗒抽了起来。
往年,追肥的活儿都是儿子儿媳一起上阵,用不上两个小时就干完了。今天虽然自己一个人干,德昌老汉并没着急,干得不紧不慢,不急不忙。他准备在日头落山前把这片玉米地追完肥,他准备在这块地上干上一整天。
一缕缕青烟在耀眼的阳光里升腾起来,笼罩了一张沟壑纵横的脸。德昌老汉眯着眼睛打量着老婆子的新坟。虽说没有在盘龙岭上的大,但是很圆很周正。老婆子刚埋在这里那两天,德昌老汉没事就扛了锹来到这儿。南平洼的土质不错,更没有树根野枣刺儿之类的东西。德昌老汉一边修一边左右端详着,像在完成一幅杰作。
老婆子活着的时候,两个人经常一起到这地里来干活。你刨埯儿,我撒种;你掰棒子,我撑口袋,老两口配合得很默契。后来老婆子的身子骨不行了,地里的活儿也干不动了,但还是经常到地里来,坐在一旁看着德昌老汉干,时不时跟德昌老汉说上几句话。
老婆子,除了德泰和大翠她妈,剩下的都埋在自家的田里了。其实这地方也挺好,春种秋收,你都能看在眼里。就是没有花呀草的,可有的是咱的庄稼,也不比花呀草的差多少……你看咱这苞米叶子,黑油油的。你再看那边邓老四家的,比咱家的早种好几天,瞧那叶子那杆儿,跟吃二两粮时的人一样,黄皮拉瘦的。咱这块地我足足上了两车猪粪。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老话说得没错。等下上一场透雨,你就听苞米杆子咔嚓咔嚓拔节吧……
一丝风也没有,阳光静谧地普照下来。德昌老汉雕塑一样靠在那里,和这岁月一样宁静。
秋风起,发黄的玉米叶子在秋风中哗啦哗啦唱起了歌。看不见人影,却不时会听见从发黄的田野深处传来的嘎吧嘎吧掰玉米棒子的脆响。
德昌老汉挎着篮子从玉米地里钻出来,篮子内是金黄饱满的玉米棒子。大黄从老婆子的坟前直起身,摇着尾巴迎接着满载而归的德昌老汉。
往年收玉米,都是儿子儿媳一起参战,三个人把玉米棒子连皮从玉米杆上掰下来,运到家里。然后德昌老汉坐在小板凳上不慌不忙地扒。然后将金黄的玉米棒子摆在窗台上,或吊在屋檐下,暗淡的农家院子里便多了一道金色悦目的风景线。今年德昌老汉谁也不用,说他自己一个人就行,让儿子儿媳忙自己的。秋收是一年中最忙碌的季节,人手不够的人家都要雇人。一亩地一百块钱,儿子儿媳每年这个时候都会在这上面有所进项。儿子大顺说,一亩来地呢,你一个人什么时候能掰完?德昌老汉说,掰一棒少一棒,总有掰完的时候。总不会越掰越多吧。最后爷俩达成一致协议,德昌老汉先一个人掰着,晚上儿子两口子收工,再把玉米棒子拉回家。德昌老汉点头答应,挎着篮子就来了。
老婆子的坟前放着一卷用麻绳捆好的编织袋。德昌老汉拿起一个,撑开袋子嘴儿,把玉米一棒一棒放进袋子内。
老婆子,今年风调雨顺,家家户户的苞米都大丰收。你看这棒,足有一尺多长。你再看这粗细,赶上大人胳膊了。你再掂量掂量,沉甸甸的压手,没有一斤也有八两。这棒也一样。我看这亩地亩产达不到两千也得到一千八……
德昌老汉把篮子里的最后一棒玉米放进袋子里。然后坐在那卷袋子上,掏出铁盒,拿出一棵喇叭筒点燃抽起来。几乎每次从玉米地里钻出来,德昌老汉都要在老婆子的坟前坐上一会儿,抽上一颗喇叭筒,一边抽着,一边把有关丰收的新发现第一时间对老婆子诉说一遍。
老婆子你看见没?好端端的盘龙岭像被狗啃了一样,凿岩机成天轰隆隆地响着,大车小辆成宿隔夜地往外拉着石头,用不了多久就会成为平地了。宗先生说,石是龙的骨,龙脉被挖断了,不吉啊!
德昌老汉凝视着盘龙岭,忍不住咳嗽起来。老婆子走的头一年,德昌老汉的气管开始不好起来,动不动就会咳嗽上一阵。老婆子劝着德昌老汉,准是那些烟闹的,戒了吧。德昌老汉笑着说,那你给我卷的那些喇叭筒咋办?老婆子说,扔了呗。德昌老汉说,扔了多可惜,你一颗颗卷的。这样,等我把你给我卷的那些烟都抽了,我就戒了。以前德昌老汉的烟量不是很大,一天三颗两颗的就够了。现在德昌老汉的烟瘾大起来了,每天都得十颗八颗的,眼瞅着塑料袋里的喇叭筒渐少。
老婆子,我进里面掰去了啊!一会儿出来再和你说话。德昌老汉止住咳嗽,手脚并用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挎起篮子,蹒跚着向玉米地里走去。渐渐地,那个灰色微驼的身影便被那片黄色的海洋淹没了。
土地的颜色看不见了,只有收割后的玉米秸茬尖利的上端还突兀地暴露在寒风中——冬日里的第一场雪严严实实地覆盖了南平洼。
一行蹒跚的脚印直通向南平洼,后面是两行梅花脚印。
德昌老汉挥着扫帚,一下一下扫着坟上的雪。动作很轻柔,像怕惊醒里边人的梦似的。
下雪啦老婆子!俗话说瑞雪兆丰年,这雪下得好啊!明年准又是一个好年景!你猜今年咱家打了多少斤苞米?差几斤两千斤!昨天来人收走了,一块一一斤。大顺说明年再多上一车粪,收成还差不了。咱这块地是块宝地啊!
雪后的阳光金针一样逼人的眼,德昌老汉拄着扫帚眯起了眼睛。大黄也郑重地坐在雪地上眯着眼睛。
出了正月十五,看了舞狮子,吃过了元宵,年也就算过完了,因过年而松散下来的心思也回到了一年中的重中之重筹备春种上。这几天德昌老汉就在琢磨,自家的一亩来地,自然还是种苞米。苞米好管理,水肥跟上,看住病虫害,就能大丰收。去年的玉米种子是在镇种子站买的,棒大,高产,抗倒伏。今年是接着种呢还是选新品种?老汉决定改天去种子站看看,好好比较比较再做决定。村东老吴家养鸡,和大顺商量商量,买两车鸡粪。不能靠二铵,还是粪养庄稼。至于在老婆子坟前种点什么,德昌老汉思虑了再三。栽树不行,树根在下面串根,影响庄稼生长,长高了还瞎庄稼。要不种几棵向日葵吧,既能看金灿灿的葵花,到秋熟了敲打下来,还能收几盘毛嗑,一举两得。老婆子也一定会同意的。
就在德昌老汉为他的一亩三分地作新一年的筹划时,一个消息再次把他击懵了:南平洼被征用了,准备建工业园。
不是签了三十年的土地承包期了吗?这才几年,怎么说变就变了?德昌老汉的心跟油煎似的。村里极少上了岁数的也和德昌老汉一样,持反对态度,山被铲平了,地再没了,让老百姓怎么活?
镇长和企业家开着小车来到了盘龙岭。财大气粗的企业家叉着腰在村民大会上郑重宣布:只要乡亲们愿意,工业园可以无条件地招收你们为工人。到时候你们就可以像城里人一样,每天穿着新崭崭的工作服,骑着锃明瓦亮的自行车,到点上班,到点下班。到了月底,嘎棱棱的票子就到手了,再也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汗珠子摔八瓣儿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事啊!何况我们还会给大家一定数额的土地补偿金,何乐而不为啊!
在企业家的一番鼓动下,年纪轻的就有几分跃跃欲试。和德昌老汉一起开始持反对意见的,在家人无限憧憬的熏染下,反对的声音也渐渐弱了下去。就连大顺的眉宇间甚至也有了一分向往。
事到如今,德昌老汉只有再一次重新安排老婆子的住处。
盘龙岭被夷为了平地,不久的将来南平洼也将矗立起一片车间厂房,德昌老汉真的不知道将老婆子安置在何处。
这天,儿子大顺风风火火地从外面回来了,对德昌老汉说,我听说二姨夫的老爷庙村山上有地方,给人家村里五千块钱,就可以埋。
那么多钱?德昌老汉一惊。
大顺说,爹,钱的事你不用管,村里不是给了迁坟补偿款了吗?我去二姨夫那儿问问。随后叫媳妇桂香,你从补偿款里拿五千块钱,老爷庙那边吐口,我就把钱交上。说完把头扭了过去,不接媳妇的目光。
媳妇桂香在原地站了一会儿,进了里屋。隔了好一会儿,才面沉似水地走了出来,把一个团成一团的塑料袋扔在了炕上。
大顺没看媳妇的脸色,拿起钱塞进里怀兜里,大步流星向外走去。
德昌老汉想制止,张了张干瘪的嘴,把话又咽了回去。
儿子走后,儿媳桂香把锅碗瓢盆摔得叮当响,还踹了大黄一脚。大黄呜咽着,夹着尾巴躲到了一旁。
德昌老汉看出来了,儿媳妇摔摔打打的,是在心疼钱。五千块呀,他一想起来心也疼。他一点也没有怪罪儿媳妇的意思。孙子在县上处了个对象,正准备贷款买房子。说好了儿子给付首付,剩下的由孙子自己每月还贷。首付的十万元儿子到现在还没凑齐呢。
德昌老汉低眉顺目地出了院子,大黄紧跑几步跟了上去。
德昌老汉又来到了南平洼。
老婆子,儿子去老爷庙他二姨夫那儿问去了。要五千元,太贵了!话都到了嘴边又让我咽了回去,山被劈平了,地也被征用了,现在实在是没地方可去啦!桂香是在心疼钱,那么多钱,搁谁不心疼啊!
这一次,德昌老汉没能在南平洼逗留太长时间,工夫不大,便往回赶,老婆子,我回去看看,大顺去了一头晌了,也快回来了。
德昌老汉没有回家,而是径直来到了村子西头,站在一处高岗上,一边抽着烟,一边注视着通向村外的路。
大黄仰头叫了一声。大顺骑着自行车的身影出现在德昌老汉浑浊的视线中。德昌老汉急忙迎上前去。
大顺一脸的愁云,二姨夫他们村村长因为这件事被撸了……
德昌老汉再一次将老婆子的骨灰盒从墓穴中取了出来。
老婆子,这里也不让咱待了,咱回家吧。
接近正午的阳光在德昌老汉眼前炫白一片。
如今,老婆子的骨灰盒就摆放在北地的柜盖上。老婆子的骨灰盒严格意义上来说不能算作骨灰盒,它比一般的骨灰盒要大,看上去形状像棺材,只不过没棺材大。五年前的那个春天,当把老婆子穿戴整齐脸上蒙着黄裱纸安顿在堂屋的门板上,灵前长明灯的灯花开始摇曳时,德昌老汉就不见了。他一声不响地躲在房西的偏厦内,施展出年轻时的木匠手艺,锯子、刨子、凿子轮番上阵,为老婆子打造“老房”。不大的骨灰盒,德昌老汉却足足用了两天时间。骨灰盒呈棺材形状,棺头刻着寿字。可以说就是一个浓缩版的棺材。虽说用的是普通的杨木板子,却很厚实,足有两三指厚。在大翠她妈坐在蒲团上拍着大腿如泣如诉数叨着老婆子生前的种种节俭和不易声中,德昌老汉挥着刷子,为骨灰盒涂上了最后一遍朱红色的油漆。
现在,老婆子这个与众不同的“老房”只能暂时寄居在此,与自己同居一室。
村里那几个和老婆子一样葬在自家责任田里的,大部分都选择把骨灰盒送进殡仪馆寄存。还有两家干脆抱着骨灰盒去了一百华里外的海边,进行了海撒。
孙子志强从县城回来了,带回来的消息是,城郊一处陵园墓地,零点八平方米,价格三万……
儿媳桂香打断志强,什么?屁股大点儿的地方要三万块?
孙子志强坐在地下的一把椅子上点着头,而且产权二十年。
德昌老汉被烟呛得咳嗽起来,好半天才好不容易止住咳嗽。
儿子大顺坐在炕沿边上,那二十年之后呢?该不会收回去吧?
不想收回只有续费。如果不交,墓园有权收回墓地使用权。如果家属不及时领取骨灰和其他物品,墓园将有权利进行处理。孙子志强解释说。
大顺说,交那么多钱就管二十年啊?
孙子志强说,现在哪儿都这样。我们这儿还算好的呢。省城一平方米墓地的价格都在八万以上,大理石围起来的绿地小院的,高达好几十万。
儿媳桂香嘟囔着,够买一套房了。
孙子志强接着说,现在的墓价超过房价。而且大多是“期墓”。
啥叫期墓?儿子大顺插话问。
就像现在买房的期房一样,暂时还未开盘,要等到新墓建成才可入葬使用。孙子解释说,我打听的城郊大青山墓园就是期墓,要到明年上半年才能投入使用。
屋子内一时沉寂下来。
大顺唉声叹气起来。
儿媳桂香站起身,让你爷歇着吧。说完向爷俩递了个眼色。爷俩跟在桂香身后向外屋走去。
屋子内剩下德昌老汉一个人。
大黄悄无声息地钻了进来,仰头冲坐在炕上的德昌老汉摇了摇尾巴。见德昌老汉没理它,径直走到炕沿下,蜷了身子趴了下去。
外屋传来了说话声。
要不咱也海撒算了。儿媳桂香的声音。
爹跟我说他总梦见德泰叔浑身水淋淋的……儿子大顺低低的声音。
爷这是迷信,人死如灯灭,什么也不知道了。要不树葬吧。移风易俗,国家现在正提倡。孙子志强的声音。
没听说吗,咱这盘龙岭村马上就整体迁出,镇北头已经开始码地基准备盖楼了。往后连棵树都没有了,咋树葬?大顺说。
那就只有送殡仪馆存上了,每年交一百多块钱保管费,费用不算高,还能承受得起。孙子志强说。
大顺说,老话讲入土为安……
什么老话新话?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说现在咋办?总不能就那么明晃晃地摆在家里吧?看着我就瘆得慌!儿媳桂香不耐烦的声音。
没听见大顺说话。
外屋没了声音。
德昌老汉靠在炕脚的铺盖卷上,从腰间掏出铁盒子,打开盖子,见里面只有一颗喇叭筒孤零零地躺在那里。这是最后一颗喇叭筒了。德昌老汉拿了出来,在手里摩挲了一会儿,擦着火柴点燃,默默抽了起来。
灯光昏黄,德昌老汉把目光落在柜盖上那个蒙着红布的骨灰盒上。因了灯光的原因,红布看上去颜色也不那么鲜红,旧突突的,像蒙了一层灰。
这一次,德昌老汉没有和老婆子说话,他相信老婆子一定也听见了一家三口的讨论。他伸手拉灭了灯。一时间,他忽然感到很累,浑身散了架子似的,上眼皮和下眼皮在不住地打架。恍惚间,德昌老汉做了一个梦,梦见前面有一个身影背对着他,从后面看很像老婆子,他紧追几步,却始终追不上,那个身影还在他的前面。于是他又向前追去。前方出现一个黑洞,从旁边经过时,黑洞像有一股巨大的引力,吸着德昌老汉飘飘忽忽向里面沉下去……
德昌老汉顺着铺盖卷萎了下去……
大黄从炕沿下方探出头来,向炕上望了望。炕上无声无息,一片黑暗。大黄咕唧了一声,复又缩了回去,将头俯在两只前爪上,沉沉睡去。
这是一个静谧的春夜,旷野像进入了远古蛮荒时代一样沉寂,大自然中的万物都沉浸在酣睡中。
屋子内,除了大黄睡梦中偶尔发出的一声梦呓,一片阒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