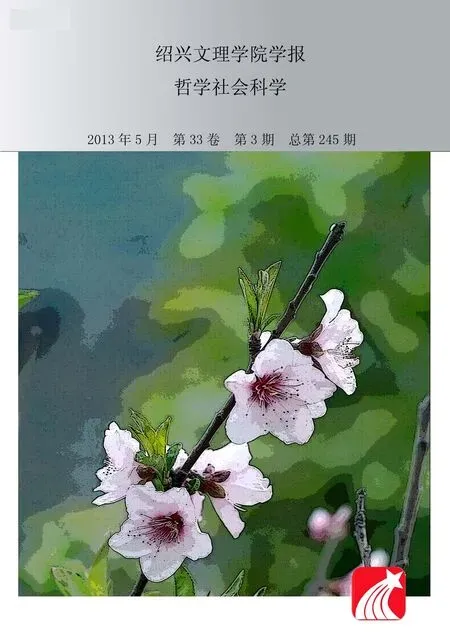寓园的人文情趣及人本特色
宋 源
(中国美术学院 建筑艺术学院,浙江 杭州310024)
祁彪佳(1602-1645),晚明绍兴府山阴县梅墅村人,著名的戏曲家、藏书家、造园家。其17岁(1621)举乡试,21岁中进士,次年授福建兴化府推官,崇祯年间授御史,出按苏、松道诸府,文治武功俱佳。弘光元年(1645)时局动乱,清军兵临杭州,以书、币诱招,祁彪佳写绝命书,在寓园自沉。
崇祯八年(1635),祁彪佳以事忤当权者,从苏、松道巡抚任上“引疾南归”。是年他在绍兴城西南20里柯山对河的寓山筑园,名为“寓园”。《寓山注》则为造园过程中反映其主体价值空间的内心写照。祁彪佳退隐后,遍游越中园林,追寻山水经验,开发审美能力;园林的生活实践,使其在纷乱中找到了心灵的安逸。如今斯人已逝,寓山依然在,昔日的寓园虽早荒芜在柯岩风景区一角,但《寓山注》中49篇园林小景与陈国光的卷首《寓山园景图》,仍鲜活地再现了明末园林特点及其人文情趣。
一、祁彪佳与寓园的分期营造
1.寓园与《寓山注》简介
寓山位于柯山余脉,寓园是一个顺着山丘和水道稍加整治而成的天然山水园。寓山西与柯山相望,东西面是古鉴湖,与内园水道相通,东、南、北三面视野深旷。造园便利用这一地形条件,把远近山水佳景尽收眼底,开发远眺之旷朗景观;建筑物则因山就势,呈“屋包山”态势。
《寓山注》记载了寓园建造的历史。序文说,“往予童稚时,季超、止祥两兄,以斗粟易之。剔石栽松,躬荷畚锸,手足为之胼胝。予时亦同拏小艇,或捧土作婴儿戏。迨后余二十年,松渐高,石亦渐古,季超兄辄弃去,事宗乘;止祥兄且构‘柯园’为菟裘矣”[1]150。孩提年少时,祁彪佳尾随填石栽树造园的季超、止祥两兄玩耍,有了20多年“松渐高,石亦渐古”的积蓄,才成为寓山的继承人、造园家。可谓“园林兴造,高台大榭,转瞬可成,乔木参天,辄需时日”[2]11。
其父祁承爜(1562-1628),字尔光,号夷度,又号旷翁、密园老人。明代藏书家、目录学家。祁父亦有“园林之好”,造有密园、夷轩、澹生堂、旷亭、紫芝轩、快读斋、蔗境等。并撰有《密园前记》《密园后记》等。
受父兄影响,祁彪佳性耽山水园林,几近痴迷。在营造寓园时,集设计施工管理等于一身。“卜筑之初,仅欲三、五楹而止。客有指点之者,某可亭,某可榭,予听之漠然,以为意不及此。及于徘徊数四,不觉向客之言。”[1]150其初无规划,只是因地制宜而展开。犹如苏轼作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2.营造寓园的三个时期
第一期(1635-1637):崇祯八年冬至十年春夏之交,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崇祯八年冬至九年夏秋,“榭先之,阁继之,迄山房而役以竣”。在寓山上逐次建成了志归斋、寓山草堂、太古亭、友石榭、烂柯山房等,大致以寓园山石区的居住建筑为主,但“一径未通,意犹不慊也”[1]151。第二阶段:崇祯九年冬至十年春,“凡一百余日,曲池穿牗,飞沼拂几,绿映朱栏,丹流翠壑,乃可以称园矣”[1]151。值此构建了水明廊、读易居、柳陌、四负堂等,主要建造了园门一带、让鸥池畔的系列景点。第三阶段:崇祯十年春夏之交,辟丰庄、豳圃为农庄园圃。近两年的造园,确立了寓园主体,寓园美景呼之欲出。
第二期(1637-1639):崇祯十年秋冬至十一年秋基本完工。检阅其《山居拙录》《自鉴录》《弃录》等日记,期间为两个系列的营造,以溪山草阁为起点,在十月兴工,年底建成,然后由寓山山麓之袖海、瓶隐,延伸向南池水岸的处理,而有孤峰女玉台、芙蓉渡、回波屿、妙赏亭等。另一系列则是在让鸥池东北岸的建筑群,依陈国光《寓山园景图》所展示的规划图,在读易居往北通过海翁梁,衔接试莺馆,与四负堂相背有即花舍,经归云寄可达八求楼,步宛转环则可与寓山山坡相接。还有未入《寓山园景图》与《寓山注》的可与语石、筠巢、浴花台、瑟疄等均已落成。那两年,祁彪佳投入寓园,“则以其暇,偶一为之,不可以时日计”[1]151。
第三期(1640-1645):崇祯十三年至弘光元年。祁彪佳完成寓园主要景点后,由于祁母去世节哀守丧,加之山阴、会稽一带江南饥荒波及,他无心力、财力再对寓园继续大规模的营造,只能建一些楼廊小阁,砌池、整花石,栽种树木花草。如崇祯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为新建成的茅庵命名为“竺(竹)深留客处”[4]第6册39;崇祯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督庄奴卸屋为古樟砰一小亭”[4]第7册38,六月十八日,“古樟砰一阁已稍有成规,登而憩之,为园中最幽胜地”[4]第7册43。因而三期工程“深在思致,妙在情趣”[5]8,情致所至,随意点染。
3.寓园与祁彪佳生命相始终
台湾大学曹淑娟教授认为,祁彪佳对寓园,“在床头金尽、形躯劳苦之外,更有其整体生命意识的投注”[6]69。他倾心血构划、经营,亲自动手修筑、整理。“构置弥广,经营弥密,意匠心师,每至形诸梦寐”,而且“寒暑劳役,几以是益我沉疴”[7]1039。松径从崇祯九年开始施工,十一年种植花草,十二年开凿土石、累石,至弘光元年仍在构筑小廊。瓶隐于崇祯十一年竣工到弘光元年才告成。归云寄从崇祯十二年定址,十三年浚池,十四年竖石、分楼为二,十五年疏泉,十六、十七年累石,至弘光元年移廊至竹林。在逝世的前一月,弘光元年的六月初二日,祁彪佳还“芟竹于后圃”[4]第10册乙酉日记17。
二、寓山注与寓园的人文情趣
园林取名为“寓”,本有“寓意则灵”,也蕴涵寄居、寄托之意。《寓山注》总名曰“注”,既隐含山水园林经典化、文本化的概念,诠释寓园的品质;又有“解释”之义,即说明各景点命名的来由、依据,并记录祁彪佳对寓园的认知与实践。在《寓山注》中,《序记》阐发园之沿革、开园总纲、营造原则,其后49记则叙述园林布局、观赏景象等。49个景点多为祁氏亲自命名,其立意高远,独抒性灵,情趣横生。
1.芙蓉渡
芙蓉,也称木芙蓉,秋日开花,且耐寒不落,又名“拒霜花”。此篇从“草阁”“瓶隐”起笔,直到曲廊临流,寒玉秋声。祁彪佳“会心处”,不在红英绿水,碧池黄鹂,而情系“秋江寂寞时,与远峰寒潭,共作知己”[3]427的冷香芙蓉。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8]104这“会心处”实为一幅画面,一种境界,反映出祁彪佳审美的独特取向。他追求一种清冷寒峭、幽韵灵动之美,这固然与其气质秉性、审美品质以及生活阅历分不开。
2.志归斋
“斋,戒洁也”,指在敬神之前戒除不洁使自身清净,由此而引申为一种清幽净洁的建筑物,如书房称之书斋,学舍谓之东斋。“志归斋”是寓园最早的建筑物,“当开园之初,偶市得敞(敝)椽,移置于此”。其建筑格局是:“斋左右,贯以长廊,右达寓山草堂,左登笛亭。”[3]428
题名“志归”,所记辞官归里,亦以示归田之志。望着“平畴远风,绿畦如浪”的家园景色,祁彪佳亦觞亦咏,“乃此是志吾之归也,亦曰归固吾志也”[1]160。志归斋有一种平淡冲远、古拙浑厚之美,是一种典型的诗意的栖居地。这种诗意,是以陶渊明为代表的田园诗意,它以牧歌般的旋律缭绕在祁彪佳的心胸,催生着他挥之不去的“归去来”绵绵情思。
3.酣漱廊
酣漱隐含着“漱石枕流”的典故,出自于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在原典中,“枕石漱流”用以表达归隐林泉之意,“漱石枕流”则更彰显祁彪佳孤介远引的性格,增以“酣”字,加深其沉湎的程度。“虽是洗耳辈嫌其多事,似犹胜竹林嵇、阮流也。”[3]429相传晋代“竹林七贤”的阮籍、阮咸叔侄曾归隐于离寓山不远的阮社,耳闻目染,于是祁彪佳的性格中平添了一份晋人遗风。
4.让鸥池
古人常以“鸥盟”来隐喻退居林泉之想。所谓“鸥盟”或“盟鸥”都是指与鸥鸟为盟,同白鸥相伴。让鸥池的命名表现出他与鸥鸟的意会之神交。他把自己与鸥鸟摆在同等的地位,欲将自己最爱之池水割与鸥鸟,即以池引鸥来栖,此乃真性情也。鸥与人的关系处理表现出祁彪佳恬静自然、超尘脱俗的志趣,以及所涵藏的内敛人格化倾向。
5.选胜亭
“北接松径,南通峦雉,东以达虎角庵。游者之屦常满,然而素桷茅榱,了不异人意。”[3]426此亭构造简朴,一点也不吸引游者的眼球。然而登亭眺望,胜景扑面而来,使人油然而生山水鱼鸟之情。
“能品园,方能造园。”[5]16当祁彪佳一边建筑寓园时,一边游览越中园亭名胜。然而引起他兴趣的不是那些可以复制的园林细节,而是成为每一处景点之一部分的景观。其欣赏一座亭楼,常常为从某处可以“尽”全景而赞叹不已。从齐氏园,“尽湖山登览之胜”[1]178;从淇园可“北望海,东南望诸山,尽有其胜”;从砎园,“收拾龙山之胜殆尽”[1]183。依祁彪佳之见,景观是重中之重,以致它们能弥补其他方面的不足,正如他注意到绍兴城王士美的蒹葭园:“构室不甚工,而蕺山之胜乃全得之。”[1]185鉴于此,尽管他承认沈玉梁的可也居其亭台营构亦有小致,“惜在委巷中,无可登眺耳”[1]192。同样,他不遗余力地称赞倪元璐的衣云阁,“回环映带,更辟一绝胜地”[1]195。祁彪佳对设计用来获得景致的建构特别在意。
6.远阁
如名所示,强调一个“远”字。景必以远观为佳,悠悠天钧,茫茫地表,极目无穷,乃见气势。阁之名谓远,非指阁建于远处,而是指入阁能得以远望。祁彪佳建阁于山之顶,且“尊而踞”,奥秘在此。远阁便“宜雪、宜月、宜雨”,四时景色,各有美妙之处。而这所有的景致,都以远望才得其佳妙。其总结出“态以远生,意以远韵”[3]431的美学观点,无论诗境画意,还是园林景致,都是如此,而且在这种远观的态度背后是祁彪佳做人的潇洒神韵。
7.丰庄和豳圃
寓园大功告成后,祁彪佳归农之兴尚殷,于是又建丰庄和豳圃。丰庄在园之北,是一片田园。“十月纳禾稼,邻火相舂,荐新粳,增老母一匕箸,及蚕月,偕内子以居焉,采桑采蘩,女红有程课。……余将以是老矣。”豳圃在园之南,是果园,种有桑树及梨、橘、桃、杏、李等果树。“每对田夫相慰劳,时或课妇子挈壶榼往饷之,取所余酒食啖野老,共作田歌,呜呜互答。”[3]432祁彪佳在著述中常有提到陶渊明,并引以为楷模。丰庄和豳圃,既是其理想的养老之地,更是其对陶渊明《归园田居》的最好注解。
此外,“冷云石”之虽静犹动;“太古亭”,追求的是“太古之遗制”;“梅坡”之抖擞江村沙浦野趣;筑室名为“约室”“静者轩”“四负堂”,是为了修身养性……,所有命名都反映出祁彪佳的匠心独具、寓园的多姿多彩以及其人文情趣无处不在。
三、寓山园林的人本特色
寓园营造了一个充满人文情趣的生活世界。祁彪佳对每一景点的描写,可谓“处处邻虚,方方侧景”[9]171,使寓园走向更为广阔的自然天地,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其园林的主要特色有:
1.自然借景
在寓园登高远眺,可览四时变幻。“园尽有山之三面,其下平田十余亩,水石半之,室庐与花木半之。”[3]421亭台楼阁在寓山中,被山阴秀色笼罩,“幽敞各极其致”。依祁彪佳之见,园林设计必须得力于山水。寓园依山成园,借景西山、鉴湖、柯岩,由山生园,由园生景,由景生情,而情无限。寓山四野低平,独自兀立。西干山连绵不绝,豆雾尖山高出云表;鉴湖纳三十六源之水,而秋湖在上,脚下帆影点点,可谓“千岩竞秀,万壑争流”。
“亭不自为胜,而合诸景以为胜。”寓园中亭子多为借景佳构。从选胜亭徊望,“每见霞峰隐日,平野荡云,解意禽鸟,畅情林木”[3]426。在妙赏亭“仰面贪看,恍然置身天际,若并不知有亭也”[3]428。榭也是借景的建筑小品,友石榭位于寓园适中处,主人感叹“旷览者神情开涤,栖遁者意况幽闲,莫不留连斯榭,感慨兴怀”[3]424。静坐读易居,“自贮之以水,顽者始灵,而水石含漱之状,惟‘读易居’得纵观之”[3]422。从通霞台眺望柯山,“则台之为景,有不必更为叙志者矣”[3]430。面对“银海澜回,玉峰高并,澄晖弄景,俄看濯魄冰壶;微雨欲来,共诧空蒙山色”[3]431胜景,祁彪佳在远阁处不由发出“盖吾阁可以尽越中诸山水,而合诸山水不足以尽吾阁”[3]431的感慨。
2.就地取材
祁彪佳对寓山的整体营造,得景随形,利用寓山本身的“高凸”“曲深”“俊显”“平坦”,自成天然之趣。寓园佳处,祁彪佳首称石,故用石颇多。石之来源:一为本地山石。崇祯十一年二月十三日,“至寓山,旋至柯山访石”[4]第5册自鉴录6。三月十五日,又“至柯山选石”[4]第5册自鉴录9。二十二日,在扫墓归途“偶得花石移归为园中需”[4]第5册自鉴录10。五月初九日,从萧山“牛头山运花石至。午后累之屿上”[4]第5册自鉴录15。二为寓山山石。崇祯十年六月十三日,祁彪佳“令平头搜剔山石,渐露巉岩”[4]第4册山居拙录20,至十五日,“剔石竣事”。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督奴子开山见石壁峻立,又辟一胜境矣”[4]第4册39。祁彪佳还请石工在穴石之骨刻出听止桥,把小斜川凿成“石趾已棱然欲起,及深入丈许,窄怒出,有若渴骥奔泉、俊鹘决云者”[3]425的山石相激画面。又凿石室取名“袖海”,能使数十人卧入其中,“寒雪沁肌,不复知人间更有六月”[3]426。志归斋北的铁芝峰,此处为寓山之巅,顶上有一石如芝状,上可坐数十人。池上理山,园中第一胜也。邻水处的山石更构成了意想不到的佳境,在回波屿处上演了一处山石相斗相噬的好戏。季超、止祥两兄20年前开山时,发现的一石,隆起如覆盂,亡兄麟佳(元孺)顾而乐之,取苏轼“马上倾倒天瓢翻”[3]429之意,题之曰“天瓢”。祁彪佳在欣赏山石时,无不同山石进行着对话。片片多致,寸石生情,寓园中的山石以形取胜,动静结合。在其上、其旁又栽种植物景观,“红紫杂古翠间”[3]425,石群周围,建亭台楼阁,使山石建筑群疏密得宜。
3.循环利用
比起清代江南园林的人工化,在真山真水中的明代园林建筑,更为古朴、自然。计成在《园冶·相地》章云:“旧园妙于翻造,自然古木繁花。”[9]56寓园虽谈不上旧园,但建筑崇尚简朴,多用旧料建构。太古亭,“在幽篁老干间,潇然独立,不共花鸟争妍冶,亭可谓得其所矣”[3]425;志归斋,“忘其为简陋,而转觉浑朴之可亲,遂使画栋雕甍、俱为削色”[3]429。为建丰庄,崇祯十年二月二十一日,祁彪佳“同郑九华至刑塘,市败屋数间,欲构堂于丰庄,即名四负堂”;二十三日,“时闻柯山有旧屋可为庄,所偕郑九华往观之”;二十八日,“与郑九华至旧屋,折卸所移之庄内”[4]第4册山居拙录6。笛亭是就地取材,用生长于斯的竹子搭成。梅坡结茅为宇,为增园林野趣。寓园主人在茶坞种茶,用沁月泉品茗,“闲啜于长松下,趣亦不恶”[3]424。在豳圃植橘、桃、李、杏、栗等,栽紫茄、干瓜、白豆等蔬菜,在丰庄养蚕和家禽,足以果百人腹。一幅幅农家景象,平淡中亦见风致。
4.社交中心
寓园是一个流动的、开放的、大众的社交中心。明末的大部分文人园,是文人士大夫从社会和政治生活隐遁所依附的寄托。寓园和外界的联系依赖水路,园林意境的创造符合陶渊明描写的桃花源。与其描绘的世外桃源明显不同,它有越中园林的个性:园林作为主人隐秘世界的同时,也是对外开放的,成为主人和外界的交流媒介。
寓山建筑景物的功能涵盖了主人同自己、家人、游人和农夫四者关系。这四者之间的关系在那里达到了相当程度的和谐。寓园富有特色的水面入口,要将“应接不暇”的游客带到一个异乎寻常的地方。园中游人纷沓而至,主人则在烂柯山房读书。寓园将耕作纳入景观的一部分,也让它作为子女读书、体验生活的地方,体会农民的辛劳。由抱瓮小憩、丰庄、豳圃构成的景园良田的象征和实际意义并重。寓园中晚明浙东最大、最著名的藏书楼八求楼也是用来和当地精英会晤、进行戏曲表演娱乐的场地,而彪佳作为晚明著名的戏曲家,更喜欢将整个园林中的景物作为戏曲表演的舞台或背景,这些已成为其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寓园中只有小部分建筑,主人保留内部空间的隐私权,更多的建筑因开放吸引着各方游客和知音。通过公私空间的正确处理以及开放时间的控制,寓园作为主人和家人修身养性的场所的同时,也成为一个受公众欢迎的公共空间。
“人在园在,人亡园废”是一种历史现象,其深处蕴涵着中国古代园林旨趣。正如王澍先生所说:“中国文人造园代表了一种和我们今天所热习的建筑学完全不同的一种建筑学,是特别本土,也是特别精神性的一种建筑活动。它和今天那种设计建成就调头不管的建筑与城市建造不同。园子是一种有生命的活物。造园者,居园者是和园子一起成长演进的,如自然事物般兴衰起伏。”[10]随着我国城市化、现代化的加速,今天的城市与建筑活动方兴未艾,古代园林留下的物质和精神遗产就是:由于人的存在,营造即为生活;建筑是有生命的,人文情趣比技术样式更为重要。当下,人的生活世界的营造趋势,应该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统一,中国本土建造艺术与当代可持续性建筑概念的结合,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

寓山园景图 [明]陈国光绘 许经纬描图
[1][明]祁彪佳著.祁彪佳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0.
[2]童轠著.江南园林志[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
[3]陈从周,蒋启霆选编,赵厚均注释.园综[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
[4][明]祁彪佳著.祁忠敏公日记(共10册)[M].绍兴:绍兴县修志委会校刊出版,1937版,1982影印本.
[5]陈从周著.说园[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
[6]曹淑娟著.流变中的书写:祁彪佳与寓山园林论述[M].台湾:里仁书局,2006.
[7][明]祁彪佳著.祁彪佳文稿(第二册)[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
[8]王国维著,滕咸惠译评.人间词话[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
[9][明]计成著,赵农注释.园冶图说[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
[10]王澍.造园与造人[J].建筑师:2007(2):83-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