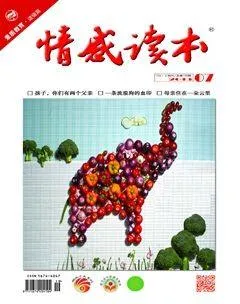我妹林月
岑桑
一
我叫林强,林月是我的妹妹。她从小就被我欺负。揪她辫子,给她画花脸,都是常有的事。开始她会向爸告状,但后来就不会了,因为她想做我的“跟班儿”。
少年时代的我,还是很拉风的。我是那一片孩子的“老大”。骂过人,打过架,每天放学,都会带着一帮兄弟,骑上自行车,按着车铃,呼啦啦地穿过大大小小的胡同。
那时,林月会死命跳上我后座,抱住我的腰不放。我说:“放开,干吗总缠着我!”她就会坚定不移地说:“我不放,我要做你的跟班儿!”
我和林月是在京城胡同里长大的孩子,大概也要一辈子住在那里,它们是永远不会被拆迁的,因为它们是文物。知道文物什么意思吗?就是它们破成渣,也得戳在那儿。
高考那年,我落榜了。其实是在意料之内的事。我在家里窝了半年,爸决定送我去学厨师。他认为有手艺在身,一辈子饿不死。我们家只有他这一个家长,他的想法就是“圣旨”。后来,我被送去了河北一家很有名气的厨师学校,那里的一位老师是爸的朋友。
我在那里学习了一年,寒暑都忙着实习。最后考到证书,才回到北京。那天林月来车站接我。我问:“爸呢?”
她说:“在家等你呢,不过你得有点心理准备啊。”
我一听,心里就有种不祥的预感。结果回去才知道,爸中风了,整个人半瘫在床上。我忽然就有种天塌下来的感觉,整个人都蒙住了。我愣了半天想起问:“什么时候的事?”
林月说:“你走没两月,他就瘫了。”
“那你怎么不告诉我呢?”
“告诉你有什么用啊?你学费都交了,难道让你回来啊?”
“那我一年的生活费都哪来的钱啊?”
“我打工呗。”
这一年,我爸49岁,我20岁,我妹16岁。我们一大一小两个男人,靠我妹整整养了10个月。她每天到快餐店卖8小时汉堡,然后回家给爸做饭,帮他擦身,换尿布,最后再去小区里的黑网吧,做半宿网管。有时候回想起来,真不知道她一个女孩子,是怎样撑过来的。
那天,我拉着她瘦巴巴的手问:“你不上学了?”
她说:“那怎么办?咱们家存折里就剩500元了,我不打工,都喝西北风啊?”
二
回到北京后,我在一家饭店里找到了工作。有了固定的收入,生活也就稳定了许多。我让林月回校复读了高二。其实,她的成绩并不好,但我觉得至少要读完高中。我爸的身体,在第二年开始有了好转,能说清楚话,还能拄着拐杖,简单地走几步。
我觉得命运终于向我们家露出了善意的微笑。
林月高中毕业后在一家公司找了个电话客服的工作。她人长得不好看,但声音特别甜,尤其是性子够和善,不论怎么骂都不还口,还是笑嘻嘻地礼貌应答。上班第一年,就被评为优秀员工。拿到奖金那天,林月请我和爸吃饭,我说:“有我还用去饭店吗?”
她说:“当然了,意义不一样。”
我爸看着一儿一女都能挣钱养活自己,笑得口水都流到碗里了。那天从饭店出来时,刚好遇到了一个小学同学。我没认出他来,但擦肩而过的时候,他认出了我。他说:“唉哟,这不是强哥吗?”
看起来,他混得不错,西装革履的,浑身都是名牌。我和他简单打了声招呼,就扶着爸转身走了。
然后,我听到身后那位同学和他的朋友说:“看看,这货以前是我那片霸主儿,现在混得特惨,听说就在小饭店当厨子……”
我默默听着,心里忍不住酸。照以前的脾气,我非把他揪过来揍一顿不可。但是工作之后,那些往日的火气,也就渐渐磨没了。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现实,你没本事,别人理所当然地会笑你。
可是,我扶着爸刚走了几步。林月就转身回去了。她指着那个比她高一个头的男人,大声地说:“哎,你说谁呢!嘴巴放干净点。今天我爸在这儿,我哥不爱理你,要不然你别想活了!”
那个同学吓得连忙说了一串“对不起”,灰溜溜地走了。我和爸转过身,惊讶地看着她。可林月却跑过来,调皮地吐了吐舌头说:“怎么样,霸气不?”
我哈哈地笑了,说:“就你这样的脾气,怎么拿的优秀员工啊?”
林月说:“那不一样。别人骂我,怎么都可以,但是说你就不行!”
“为什么啊?”
林月挽住我胳膊说:“我是你跟班儿啊,哪能让他们瞧不起我老大呢!”
那时已是12月,夜晚的北京,吹着凛冽的风,可是有我妹紧紧地挽着我,我就会感到一种踏实的,历经风雨也不会消散的温度。它不热烈,却持之以恒。
三
林月是家里唯一的女性角色,所以总是兼顾母亲的职责。当我向30岁靠拢时,她开始催婚了。她说:“哎,哥,你是不是该谈个对象了,怎么一直没见你有动静呢。”
我无奈地说:“现在的女孩活得多明白,像我这样挣得不多,长得不帅,还拖一中风老爸的主儿,谁敢爱啊?”
林月撇嘴说:“切,那是她们没眼光。”
不久,林月就私自做主把我的照片登在了相亲网站上。于是相亲电话,一个接一个地打进来。后来我认识了何丽。
何丽是丹东人,开朗热情,在北京工作了4年,说一口爽快的东北话。我们在几次见面中,都比较谈得来。之后,她要来家里看看。
一直以来,我都没说我爸中风的事。我只告诉她我和父亲、妹妹住一起。因为我怕还没开始就把人吓跑了。
所以,带何丽回来的周末,我如临大敌。可是那天等在家里的只有林月,爸不在。
何丽问:“你们家就你们兄妹两个啊?你爸呢?”
林月说:“这是我哥的房子。我和我爸不住这儿。”
何丽捶了我一拳说:“行啊你。还和我留一手。怕我为你家文物房子找你啊。”
我忙解释说:“没,没那意思。”
那天何丽一走,我就追问林月,把爸弄哪儿去了。
她说:“我租了个房子,把爸接过去了。以后,你就不用怕女朋友突击检查了。”
“你一个人,能照顾得了爸吗?”
“怎么不能呢?我租的楼房,可好住呢。等你把嫂子娶回来,我们再搬回来住。”
林月用她那种坚定不移的目光看着我。我知道,再劝也没什么用了。
四
2007年我和何丽结婚了,那时林月带着爸在外面已经住了一年多。何丽是个明白人,她知道了事情的原委,要我把爸接回来住。可是林月却不同意,她说:“嫂子毕竟是外人,爸那么麻烦,久了肯定要抱怨。到时候闹起来,谁都不好过。”
我把曾经她说我的话倒给她:“现在是你没结婚,你带着爸,有人要你吗?”
可林月却有了另一套说法。她说:“呀,就因为带着爸就不要我,那样的男人能嫁吗?我爸就是检验男朋友的试金石啊!”
林月总是有这样的本事,把不好的事,看成好事。把任何麻烦,都转化成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虽然何丽是直性子,但很会操持生活。家里在她的打点下,很快有起色。2009年,我们开了一家小饭店。我做大厨,她来管账,日子辛苦却也红火。每个周末,林月都会推着爸回来。那时爸的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脑子也变得不太清楚。但一家人聚在一起,总是其乐融融。第二年,我和何丽有了儿子。林月这个小姑,高兴得天天来看侄子。我看她喜欢的样子,劝她说,“你该找一个了啊,哥看着都替你急。”
林月却不在意地说:“瞎急什么啊,恋爱结婚是讲缘分的。”
可我知道,她是为了照顾爸。那时的爸,已经完全像个小孩了。林月不忍心把他送去养老院。她在网上看了虐待老人的新闻后,害怕神志不清的父亲被欺负。而我因为有了小孩,也无暇顾及到他。
有时,我很懊恼自己的自私,作为一个兄长,却习惯了让妹妹去承担麻烦。我从没想过,这些看似快乐的日子,却掩藏了许多我从不知晓的秘密。
那是2012年的12月。林月突然在夜里打来电话,叫我快过去看她。我听她的声音都在发抖,顿时慌了。我连夜打车去她那。爸藏在床底下,嘀嘀咕咕地不知道在说什么。林月坐在电话旁的地上,头破血流。
我连夜把她送去了医院,替她包扎的医生出来对我说:“你是林月的哥哥吧?”
我点点头。他说:“你是怎么当哥的?你妹妹长期遭受家暴你不知道吗?她浑身都是伤!”
我站在苍白的日光灯下,霎时傻掉了。
林月说,早在半年之前,父亲就已经开始有暴力倾向,有时只是粥不合口,就会动手打人。这一次林月替他盖被子的时候,手指戳到他的脖子。他就拿拐杖砸了林月的头。林月一直都不敢和我说。因为她怕我知道了,会把父亲送去养老院。那天,我要她去医院做个全身检查。开始她死都不肯,直到我发了脾气,她才答应。
一周后,我陪着她去医院拿检查报告。医生说:“你这个哥,真够可以的。你妹得肝癌了,知道吗?”
我这才明白,她为什么不去体检。她早就知道了,所以才不恋爱、不结婚。林月说,“我都这样了,不能去连累别人。”
五
我和何丽商量,把爸和林月接回来住。她一边点头,一边抹眼泪说:“这么多年,真是难为你妹了。都接回来,我伺候。”
那已经是新年的1月,我爸到家后,一上床就睡了。林月一直站在院子里。我说:“进屋吧。外面空气太脏。”她却转身说:“哥,你答应我。以后什么情况,都不能把爸送去养老院。他是有儿女的人,不要扔下他一个人。”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
她像心里放下一块石头似的,微微笑了。
这就是我妹,一辈子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感人事迹,也没什么爱好和追求。在她善良单纯的世界里,就是想让她的亲人过得好一点,好一点,再好一点;至于自己,一切都无所谓。
一天,林月看见靠在墙角的旧自行车说:“这老古董还能骑不?你再驮我去胡同里转转吧。”
我说:“行,哥带你兜风去。”
那天北京下了纠缠不去的大雾,林月坐在后座上,像从前那样,紧紧地抱着我的腰,说:“哥,你怎么还这么拉风,这么帅呢?”
我说:“你可真会哄我开心,哥的脸都老成长白山了。”
林月清爽地笑了。她把头轻轻靠在我背上,说:“哥,我好想一辈子都做你跟班啊。可惜我这一辈子,有点短了。”
刘大伟摘自《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