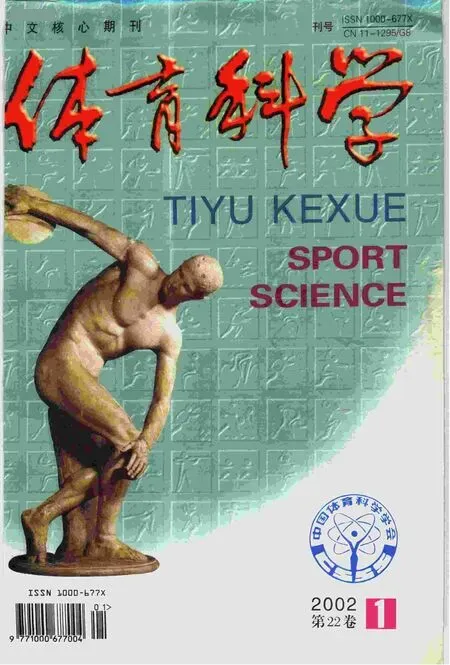游戏冲动:席勒美学思想观照下体育的审美本质
杨 韵,邹玉玲
18世纪的西方,那轰轰烈烈的以思想解放为核心的启蒙运动,既赋予了席勒(Schiller)以浪漫主义情怀的文学创作灵感,也激发了他那以独立自由为根本的美学思辨之源。这位横跨文学、哲学、史学等多个领域的启蒙思想家,在他不到半个世纪的短暂生命历程中为世人留下了丰厚而深刻的文化财富。而这其中,被誉之为德国古典美学开端的席勒美学思想,则无疑是其理论成果最为集中的体现。这一以游戏理论为中心的美学思想的诞生,不仅为美学理论的日趋成熟奠定了坚实基础,更是游戏这一独特的理论学说得以创生与承继的根基。然而,无论是游戏与体育那息息相关的本质联系,还是席勒在其游戏理论探究过程中不时提及的体育运动问题,似乎都在吸引着我们投身到这个深刻而新奇的游戏之域,对其所渗透出的体育本质进行更为深入的理论探寻,寻找那潜隐于游戏中的体育线索。
1 席勒美学对人性的省思之路:感性冲动、形式冲动、游戏冲动
延续着文艺复兴对人本价值的唤醒和启蒙运动对人之理性的崇尚,席勒美学思想也同样发端于人性这个基本理论出发点,而对近代社会中普遍崇尚的理性和普遍忽视的感性,这一极端对立的现实发展状态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席勒认为,理性至上的人类社会,如同是“一种精巧的钟表结构,无数无生命的部件拼凑在一起,构成一种整体的机械生命”[8]。而原本有着鲜活生命力的人之个体,则不过是其中无数运转着的齿轮之一。在这其中,人的存在价值逐渐被其创造出的财富、拥有的技能等物化了的理性所遮蔽,使人的情感、兴趣等感性体验日趋被压抑和束缚在理性的捆绑之下,不被社会所关注,甚至也难以被其自身所感知。在这种理性与感性极端对立着的社会状态中生存的人,是分裂的人,也是缺乏完满人格和生命自由的人。
而在席勒看来,这种人性的分裂与人格的缺陷,也正是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与发展困境得以产生的根源所在。因而在此基础上他也进一步提出,对社会改造与发展的根本便在于对人的改造与教化,在于对真正能够融感性体验与理性思维于一身的人的完整性的追寻。然而,现实社会所秉承的对人的改造与教化,却更多地呈现为一种压迫与强制化的外在约束力而在社会环境中蔓延开来,这似乎除了激起人们愈发明显而强烈的反抗情绪外,并不能够对人的完整性的塑造起到真正的推动之效。这也使席勒将改造人的意图转而倾注于更为主观的人的存在,将其对人的完整性的追寻诉诸于更为抽象也更注重感性体验的美,认为唯有通过审美教育的过程,“人才有希望获取自由的社会存在,才可能恢复人性的完整”[1]。
席勒对美的概念的提出,首先是将人视为感性与理性相统一的生命存在,认为人本身内在的具有两种相互对立着的自然冲动。一是意图使生命潜能等感性内容外化为一种客观物质实在的冲动,即感性冲动(sensibility impulsion);二是运用人的理性而赋予物质世界以规律与法则等形式的冲动,即形式冲动(modality impulsion)。然而,“感性冲动使人感到自然要求的强迫,而理性冲动又使人感到理性要求的强迫”[9]。为了对感性与理性在这种强迫作用力下的对立形势的缓解与消融,就不得不寻求一种能够消解其压迫与束缚感的内在中介,使人的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能够在内在融合的同时保持其原有的本性。席勒认为,这种内在的中介实质上是一种“游戏冲动”(game impulsion),是连接起人的感性与理性的第三种冲动,更是真正能够通达人的完整性这一根本目的的核心驱动力。
游戏冲动能够“把形式送入物质之中,它消除了感受和热情片面的自由,使之与理性相协调。同时又去除了理性法则的强制,使它与感官的兴趣相一致”[4]。从而使感性冲动所迸发出的生命活力,能够真正地与理性冲动所构建的外在形式在不受束缚的状态下相融合,形成一种真正归属于人的、充分自由的存在着的“活的形象”。在席勒看来,这种真正归属于人的自由体验也正是人之所谓美的集中体现,对自由的追寻与通达便是审美的本质所在。因而,游戏冲动的根本也正在于通过审美过程达到人对于美的探寻、对人之自由本质的实现。例如,席勒美学思想中最具代表性的论述所言说的那般,“人只有在他是十足意义上的人时才进行游戏,只有在他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个人”[8]。
然而,席勒对其美学思想过于抽象的思辨与论述,也使得人们对这一游戏冲动的审美本质持质疑的态度,而认为席勒“试图以审美教育达到人性自由不过是构造一虚幻王国”[6]。的确,作为根基于人之本质的美学思想,倘若只是在抽象的哲学思辨层面作出分析与论述,而没有回归到人最为现实的生活世界作出更为详尽的解读,自然会使人们产生空洞虚幻的误解。而作为根基于人的发展的身体活动形式,体育则无疑是集感性体验与理性思维于一身的人的完整性最为集中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因而,本研究也尝试在席勒这一以游戏冲动为核心的美学思想的关照下,遵循着他对人性的反思与追寻、对人之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的思辨以及对游戏冲动理念的提出这一思想轨迹,在体育的范畴中对席勒美学思想作出更进一步的解读,使其能够更为具体而真实地呈现出体育的审美之义。
2 体育的感性冲动:从生命潜能到物质实在
感性冲动在席勒美学思想体系中,既是人性分析不可或缺的两个固有内在属性之一,也是审美活动得以生成的首要条件。席勒对何为感性冲动有过这样的解释:“它来源于人的肉体存在或人的感官天性,它的任务是把人置于时间的限制内,并使它成为物质。”[8]而它所作用的对象则是最广义的生命,“是感官中的一切物质存在和一切直接现实”[8]。这个抽象而晦涩的解释说的简明些,实质上是人在建构与外在世界间的关联时所迸发出的内在生命能量的释放,是人对于外在于自身的客观世界的占有。其所意图的,是通过这种生命能量的释放而在客观世界中明确与巩固自身的生命存在感,使人的内在生命力能够成为一种外显的生命形态而被感知。
感性冲动这种本质的生命潜能释放,实质上也是对人之生命力的塑造与突显,这在以人的身体运动为根本的体育中有着显而易见的体现。诸如生命活力、激情、力量之类积极而极具感召力的语汇愈发频繁的被用于形容体育之于人的感受,似乎也在不断强化着人们对体育本质那内在而深远的生命力的感知与认同。例如,美国作家克里斯托弗?麦克杜格尔(Christopher McDougal l)曾在其著作《天生就会跑》(Born to Run)中对跑步这一基础而又有着十足代表性的体育运动形式所体悟的那般,人类依靠奔跑而在与动物的竞逐中得以生存下来,又在奔跑中感受着“肌肉、呼吸和思想融为一体”[5]的生命活力,更在长距离耐力跑所带来的身体极限中,体味着人作为生命个体那迫切而炽热的生存需求与生命意志。诚如书中所言,“人类天生就具有奔跑的欲望,需要做的只是将它释放出来”[5]。人们似乎是在奔跑中感受和体验着自身的生命存在,跃动的身体不断感受着原本外在而陌生的客观世界,呼吸与脚步寻找着人与世界朴素而真诚的沟通,又在沟通与互动的过程中逐渐的融入其中,而在客观世界中建构着外显而生动的奔跑着的人的生命形态。在这一过程中,运动的身体俨然也成为了客观世界中生命体的构成,而使人的生命潜能释放有了具象的物质化显现。这便是席勒所谓人之感性冲动具体的体现:人需要将自身潜能转变为一种物质实在,这种需要是生命存在的自然驱动力,是生命潜能亟待迸发的自然表征。体育使人通过运动着的身体这个物质化实在而觉知到自身生命活力的存在,这是惟有运动着的身体才能显现出的人那与生俱来生命潜能,也是人的感性冲动在体育中最为真实而形象的体现。
然而,在席勒看来,感性冲动作为一种自然法则的具体体现,只是人性中那种依靠自然而生存着的内在属性所必须的能量积聚与释放,这虽是人得以生存于世的必要条件,却并非是人性内涵的唯一。倘若人仅仅依靠感性冲动所释放出的生命能量来占有世界,只是将人的价值限定在无限制的物质实在的生成之上,“人就只是粗鄙的物质”[4]。对于这种近似于粗鄙的物质化的人,席勒也曾以古希腊奥林匹克竞技的高尚与古罗马角斗的异化这一对比而加以批判:“要是希腊部族在奥林匹克竞技场上高兴地观赏比力量、比速度、比机敏的不流血竞赛以及才智之士更为高尚的比赛,要是罗马人目睹一个被刺倒在地的斗剑武士或他的利比亚的对手的殊死战斗而大饱眼福,看这一个回合便会叫我们明白,我们何以不在罗马,而是要去希腊寻访爱和美的女神维纳斯、最高希腊女神朱诺、光明和艺术之神阿波罗的理想形象。”[8]古罗马的角斗场在席勒看来就好似人的感性冲动失控般的宣泄,那本该内在于竞技中的生命力量似乎完全倒退到了野蛮时代的动物本能尚未褪却的状态,异化而成1种残酷血腥的斗争形式,正如匈牙利运动史学家拉斯洛·孔曾描述的那样,“竞技场表演变得愈来愈残忍,罗马游手好闲的居民对美感和道德的需要已经减少,他们喜欢看流血的场面,追求强烈的刺激”[3]。失控的感性冲动是人意图达到完整之境所必须要控制与缓解的内在驱动力,而对这一缓解之力的追寻,席勒则选择了理性这一被其以形式冲动为名加以思辨的人之本质属性。
3 体育的形式冲动:从物质实在到理性生存
如果说人通过感性冲动而实现了自身由生命潜能到物质实在的转化,继而占有了客观世界,那么形式冲动则意味着人在对客观世界的占有基础上更为彻底而全面的控制,它使人独特的理性思维能够赋予物质世界以形式,并逐步的具体化为规律、法则、真理、正义等等社会化生存所必须的永恒而普遍的形式化存在,使人所生存的世界能够真正以其为核心而建构着持续性、永久性的历史演进之路。这种对人类社会的持续性与永久性的向往,便使形式的构建成为人内在而深刻的自然欲求,而以冲动的形式显现出来。美国哲学家维塞尔(Leonard P.Wessell)在对席勒美学思想进行解读时曾对这一形式冲动理念做出过根本性的解释:“这种冲动存在于各方面与秩序相关的所有人类活动的背后,它使人们对经验中永久的、普遍的或形式的东西感兴趣。”[7]
以理性生存为根本的形式冲动在体育中同样也有着显而易见的体现。美国体育史学者阿伦·古特曼(Allen Guttmann)在对现代体育本质进行剖析时便明确指出过现代体育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特征,他认为体育本身就是一种“有组织、有规则的游戏”[2]。事实上,也正是因为人类理性作用下形式的逐步具体化,赋予了体育以愈发明确而全面的规则体系,从而使其得以从最初人之个体间朴素而简单的发展雏形,逐步依靠内在统一的规则与模式而以一种普遍化、平等化的形式为人们所共识和接纳,成为一种普遍化了的社会存在方式,体育在人类社会的演进中才真正有了得以承继与发展的根基。因而,形式的构建俨然是体育得以生存与延续的根本,是一种必然而内在的发展需求。而且,体育的这种对形式的内在需求还将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更新,以适应社会的发展需求。正如篮球运动自詹姆士·奈史密斯(James Naismith)在1891年的发明之始,便在飞速的发展与传播过程中不断的变化着自身规则的制定来适应最普遍的人的需求。在那之后五年,“五人队伍成为定制,1893年策应被允许,1896年运球被允许,1913年双方疯狂抢夺界外球的规则被淘汰”[2]……篮球运动的规则化的愈发彻底和全面,与这一项目在世界范围内的风靡之势显得相得益彰,便是体育中形式冲动之重要性的明证。体育唯有在对形式化欲求的不断生成之中,才能够保持其普遍化发展与延续的社会生存根基。毋庸置疑的是,形式冲动推进下的理性生存本质,与感性冲动推进下的生命潜能物质实在化一样,是体育得以延续与发展不可或缺的内在属性。
自然,体育中形式冲动在规则之外还有着更为广泛而深入的体现,诸如高科技的引入、比赛形式的量化之类,皆是形式冲动在体育发展进程中的具体显现。也正是形式的日趋复杂化,构筑着体育本身那深刻而丰富的内涵,不断生发着越来越多的社会生存价值,延续着自身,又发展着自身。然而,也正如席勒在最初的人性分析时所批判的那样,理性思维的根深蒂固固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诉求,但倘若这种理性的运用逐渐的取代人最为根本的生命存在而成为人类社会至高无上的生存表征,人们也将逐渐在这种理性的遮蔽下迷失着那个充满生命活力与情感体验的自我。正如古特曼在其代表作《从仪式到纪录:现代体育的本质》中所指出的那样,现代体育本质中对量化(Quantification)与纪录(Records)的崇尚与追捧,事实上正潜移默化的将体育的本质异化成为一种对数据的呈现。人们对体育的关注点开始集中在竞赛的成绩、纪录的刷新之类的具体数字化形式之上,而逐渐遗失着对体育运动本身的热情,这不得不说是形式冲动的失控之下对人之感性冲动的一种复归般的诉求。人性本质的这两个总是对立而又互为生存根本的内在冲动,究竟该以怎样的形式才能够达到一种和谐完满的境地,而达到人的完整性这一被席勒谓之为人性发展之根本的目的呢?
4 体育的游戏冲动:从理性生存到审美自由
感性冲动与形式冲动之间这般尖锐而难以调和的对立的状态,在席勒看来却正是唤醒一种新的冲动形式,即“游戏冲动”的根源所在。席勒认为,对立的状态是感性冲动与形式冲动这两个内在冲动之间的一种必然存在状态,感性崇尚潜能的释放而形式则要对这种释放加以控制,这种极端对立的内在本质使它们不会在相互的冲突中自然的达到和谐一致的状态,而必须借助第三种冲动形式的唤醒来作为中介,使感性冲动不再受到控制般的约束而形式冲动,也不必失落人之生命存在。这便需要给予二者一种公平而恰当的自由延展空间,构建起一个宽松而舒适的环境以适应其生存与发展的需求。在席勒看来,这种自由空间得以生成的根本便在于游戏。游戏中的人不必受形式的束缚而有着灵活多变的表现方式,同时也不必压抑自身生命潜能的释放而将自我完全的交付于灵活的表现形式之中,恰如朱光潜先生所形容的那般,“鱼水相得,便是一种游戏的状态”[9]。
这种游戏的状态在体育中俨然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内在关联。这里我们不妨以本文之前所提及的那部《天生就会跑》的著作中所描述的那群以奔跑为生的人们来加以阐释。作者所倾力描画的正是这样一个让世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奔跑着的群落塔拉乌马拉人,他们似乎总有着几乎消耗不尽的充沛体力和向前奔跑的热情,“仿佛拼命奔跑能唤起他们更旺盛的生命力”[5];在几倍于马拉松距离的长跑比赛中,他们只有破旧的装备和匮乏的营养,却能够在身体极限到来时将那种受压迫的困窘之境适时地调节成为自我意志的体验,进而将身体那因运动过度而疲劳沉重的脚步,也逐渐随之而调整到轻盈流畅的节奏感上。奔跑中的他们总是露出一种淳朴而真诚的微笑,身体仿佛是与外在的环境融为一体般的和谐而美好,他们只觉得自己是在享受奔跑的过程,在身体那历经无数次极限与超越的感受中体验着奔跑所带来的愉悦与畅快。因而,极限在意志的自发调节之下便演变成为超越的成就体验,比赛的成绩在奔跑的愉悦感受中也不再重要。这便是一种游戏的状态,他们在奔跑中充分地释放着自己的生命潜能,进而将其外化为物质实在而不断延展着脚下的路;又在对这种生命潜能的转化有了充分的体验之后,享受着这样的感性冲动所带来的愉悦感受,超越了比赛这一形式冲动的局限,而在不自觉的状态下自发地延续着比赛的进程,从而使感性冲动与形式冲动在这一游戏冲动的生成之中,达到了恰好的契合而汇集于人之本身,在这个运动的身体之上完善着人之完整性。
这种奔跑中的游戏冲动,不禁让人联想起近年来饱受诟病的学校体育中的长跑之困。与塔拉乌马拉人截然相反的是,如今的学生群体面对跑步这一基础性的体育运动项目,不仅没有游戏冲动的感受,连最为根本的感性冲动中的生命潜能也鲜有体验。以文化课教育为核心的应试教育体系使学校体育的重要性日渐衰微,而跑步在这种不被重视的体育环境下又往往被指定为应试标准。这就使得多数学生在未曾有感性冲动之时,便不得不承受着形式冲动的压迫,致使以增强体质增进健康为初衷的长跑,自然而然地成为一种达标式的考核压力,而积淀起学生群体普遍存在的抵触情绪。跑步这项原本充满生命活力的体育运动项目,也在如此这般的抵触与压抑之中逐渐遗失着原初的生存空间。这事实上也正是体育中游戏冲动本质的一种充分而生动的反证,没有感性冲动中那自然生发的生命潜能的释放,再严密的形式刻画也无法通达体育所意图构造的完整的人的境界;没有融感性与形式两种冲动于一身的体验,以享受和感悟为目的的体育参与的自由状态也自然难以触及。
自然,跑步的问题只是体育中的游戏冲动一种最为集中的表现之一,游戏冲动在体育中无疑有着更为宽广而内在的本质体现。正如同样饱受诟病的中国足球发展问题,便也无疑是游戏冲动的另一种充分而生动的反证。在人们普遍对中国足球水平的持续低迷而痛心疾首的同时,对于世界范围内的高水平足球运动的欣赏与钦佩,却也逐渐成为人们那不断高涨的体育热情中最为典型的表现之一。且以被誉为足球王国的巴西足球为例,我们在谈及巴西足球时,除了那闪耀的历史战绩所积淀下的威望之外,更多的还是被那极具代表性的桑巴舞步所折服。精湛而细腻的脚法、变幻莫测的进攻方式、传切配合时天衣无缝般的流畅表现,如此种种的语汇所聚集而成的巴西足球,俨然成为了一种艺术的身体化表达形式而成为体育运动中无以取代的经典。
然而,这种近乎至高无上的足球运动之巅又究竟是如何生成的呢?悠久的历史传统与天赋的身体素质固然是不容置疑的优势,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巴西足球是一种近乎全民化普及的体育运动,无论年龄、性别、专业化水平的差异,人们总是能在一种积极而热切的状态下享受着足球运动带来的愉悦体验,仿佛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生发出来的感性冲动一般,人们只是将自身对于足球的向往以生命潜能的外化形式而显现出来。正如走在巴西街头总能轻易的遇到在街头颠着足球嬉戏的孩童一样,他们那纯真的身体运动中并没有过多的形式化约束,而只有奔放而积极的生命活力的充分显现。反之亦然,在高度专业化的巴西职业足球中,形式那近乎最大限度地发展并没有使得巴西足球显现出脱离人之生命体验的机械感,有的只是充分地融入了形式冲动之规律化的运动着的身体。这便是游戏的状态,是在游戏冲动推进下总是融运动热情与精湛球技于一身的巴西足球人最为彻底的表现。正如诸多的体育评论所感慨的那样,足球在巴西人的脚下仿佛有了生命一般,巴西足球也仿佛凝聚成了一个活生生的运动着的人的形象,而印刻在世界球迷的脑中。
一个活生生的运动着的人的形象,这不仅仅是体育所赋予人最为鲜明而独特的一种审美体验,事实上也正是席勒在论述游戏冲动时所着重强调的理念。在席勒看来,以人的自由为核心的游戏冲动,其所作用的对象正是一种“活的形象”,也是美的本质最为集中的体现。正如他曾以大理石与雕塑间的本质差异所隐喻的那般,“一块大理石虽无生命、也永无生命,但经建筑师和雕塑家之手仍能成为栩栩如生的形象;一个人虽然活着,也有形象,却因此还远远不是一个活生生的形象。这需要他的形象是生命,他的生命是形象”[8]。体育中的人的存在也是一样。倘若只是简单而机械地释放着自身的生命潜能,不断地用身体运动占据着其置身其中的物质世界,那么,他只是一种生命存在的显现,与动物无异;而倘若只是不断强化着体育中对内容的量化与对纪录的追逐,那么,他只是对人的理性思维的一种形式的体现,与机器无异。
感性冲动与形式冲动,唯有在互为需求又互为促进的过程中既唤醒了感性冲动所引起的内在生命潜能,又将形式冲动所引起的理性思维充分而恰当的运用其中,才能够使人在理性的指引下真正体验到自身的生命存在,从而达到一种完整的人性的探寻,也便呈现出了人作为一种审美的存在所特有的生命自由状态。因而,体育中的人,也只有在充分地释放自身生命潜能的同时,将体育的理性化元素积极而全面的融入其中,并使其真正渗透为生命潜能释放过程中的一部分,使生命潜能与理性生存在体育的过程中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的凝聚合一,才可能在体育的过程中达到对游戏冲动这一体育本质的体验与融入,才能真正使自身的体育过程成为审美存在之于人而言的身体显现。正如上所述,那些充分享受着游戏状态的体育中的人,无论是巴西足球那艺术般存在着的桑巴舞步,还是塔拉乌马拉人那轻盈而愉悦的奔跑,皆是这种审美的自由在体育中最为具体而真实的显现,也是体育那深刻而内在的审美本质以游戏冲动的形式而显现出的最为完美的活的形象。
行文至此,对席勒游戏冲动理念在体育范畴中的解读,似乎也完成了一个初步而相对完整的结构式的勾勒。不可否认的是,对于体育与游戏之间关联的思辨,早已是学界探讨的焦点问题之一,但对席勒的游戏理论,却大多只是作为西方游戏说的开端而简略提及,而鲜有全面而深入的论述。事实上,正是席勒对游戏冲动理念的提出所开创的游戏学说,赋予了体育本质以一种全新的解读与分析的理论视角。这种游戏概念的引入,并非只是形式上对游戏与体育之间关联的一种简单比较,而更重要的是对其中作为一种精神与理念存在着的游戏状态在体育本质中的融入,是游戏的精神在体育领域中的一种引领与感悟。而被席勒所突出的游戏与美的本质关联,则更是对体育作为一种审美的存在更为深入而彻底的解读。游戏冲动引领下的体育之美,不仅仅是以往人们所熟知的对体育所展现出的人的身体形象的欣赏与体验,更是体育对人之精神实质的一种渗透与升华。它所渗透的,是体育之于人而言的审美存在,更是体育在人的精神世界中更为深刻而内隐的美的显现。
5 结语
席勒的美学思想秉承着对人的完整性的追寻这一核心理念,既超越了将生命潜能化作物质实在的感性冲动,也超越了将物质实在化作理性生存的形式冲动,转而探寻能够将这两种人的基本内在冲动形式在不受束缚而充分自由的状态下相融于一体的人的第3种冲动,即游戏冲动。在席勒看来,正是这种游戏冲动,使人能够在真正自由的空间中感受和体验着自身存在,从而也在客观世界中将其逐渐对象化为一种活的形象。而这种活的形象的产生,也便是一种审美的存在,一种人的完整性的实现。
而在席勒美学思想的关照下,体育中的人也是在生命力的释放与理性思维的运用这一内在交融,又不断冲突着的感性冲动与形式冲动之间,生成着融二者于一身的游戏冲动。这一游戏冲动的实现,使人在体育的过程中能够以充分自由而积极的状态,调和着自身的生命活力与理性思维,既能够切身体验着体育所给予人的生命潜能的释放,也能够在理性思维的指引下实现着体育所特有的规范与形式,从而构建起体育运动中人所呈现出来的一种活的形象,一种审美的存在。正如被誉为古希腊雕塑之里程碑的“掷铁饼者”,其所呈现出的体育之美便既非单纯的生命力量的释放,也非单纯的身体外在形象之美的显现,而是融二者于一身的、体育之于人而言的活的形象的展现。它那相对静止的投掷动作所渗透出的体育之美,事实上正是那未曾显现却深刻的潜隐其中的、完整而生动的投掷运动所给予人的充满活力的体验所衬托而出的。而这种体育的生命释放与体育的形式显现在游戏冲动的引领下所通达的体育之美的生成,也正是席勒所谓游戏冲动所激发的、体育中人的审美本质之真义所在。
[1]杜卫.美育:审美现代性话语的创建——重读席勒《美育书简》[J].文艺研究,2001,(6):12-19.
[2]古特曼.从仪式到纪录:现代体育的本质[M].花勇民 等编译.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12.
[3]韩志芳.角斗士古罗马体育的异化[J].体育文化导刊,2004,(2):64-65.
[4]李克.试论席勒对人的思考[J].学术论坛,1994,(5):73-78.
[5]麦克杜格尔.天生就会跑[M].严冬冬 译.海口:南海出版社,2012:96,10.
[6]彭富春.康德、席勒、马克思的审美哲学[J].文艺研究,1989,(1):39-49.
[7]维塞尔.席勒美学的哲学背景[M].毛萍 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196.
[8]席勒.席勒文集(VI)[M].张佳珏 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9]朱光潜.席勒的美学思想[J].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63,(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