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想象,谁的民国?

张慧瑜 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
近些年,在大众文化尤其是图书市场中,“民国范儿”的图书特别畅销。不管是乱世英豪、文人雅士,还是大家名媛、革命女侠,就连民国教科书、民国版图书也如出土文物般“重见天日”,以至于《走,回民国住两天》、《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活在民国也不错》等,仅从书名即可获悉这是一趟穿越到民国的文化列车。诸如《民国风度》、《民国气质》、《民国衣冠》、《民国底气》、《民国风景》等林林总总的民国叙述,不再是一个“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意识形态战场,也不是“落后就要挨打”的血迹斑斑的近现代中国悲歌,更不是从一次又一次的挫败中最终走向新民主主义胜利的革命史。这些念兹在兹的“民国范儿”无心也无力搭建一条连接近代、现代与当代的高架桥,反而倾心于装饰一座民国化的主题公园,让人们在文武北洋、民国先生、民国女人、民国大学等系列橱窗中流连忘返。如此这般的民国想象,就像一个乱花渐欲迷人眼的万花筒,任凭历史的车轮如何翻转,看到的总是“那些人,那些事”。
“民国范儿”的写法
“范儿”是一种北京方言(“儿话音”就很有北京范儿),“够范儿”、“有范儿”是指能够代表某种风尚或风格的气派和劲头,就像京剧演员唱念做打的一招一式就很“有范儿”,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视觉形象。顾名思义,民国范儿就是一种与民国有关的劲头和作派,按照知名文化人陈丹青的定义,民国范儿是“一种趣味、一种风尚和一种美学”。如此民国范儿与其说是那个时代固有的风采,不如说是这些年重新发现并赋予民国的特殊风韵。也就是说,只有当民国范儿作为一种命名方式被发明出来之后,那些散落在现代中国历史中的风土人情才能被摆放在民国的橱窗里。这种民国想象固然与图书市场的策划以及跟风效应有关(仅以《民国范儿》为书名的图书就有好几种),但声势如此浩大的民国风恰好是在中国经济崛起时代浮现出来的文化想象,这也反映了当下都市消费的文化心理。
如果把《新周刊》2010年9月的封面专题《民国范儿》作为一种标识,那么这种新的民国想象让人们“蓦然”发现原来并不陌生的民国竟然如此“有范儿”,“数名流人士,还看民国”。在《民国范儿》一书中,民国既不是有头有尾的历史大叙述,也不是政治、经济、社会等国计民生的大主题,而是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的民国风情、掌故和逸闻趣事,即使作为系列文章推出的“民国先生”,也是如词条般排列的人物小传,这种字典式的春秋笔法本身是为了实现“可以触摸的民国”的效果,曾经明争暗斗、民不聊生的“万恶的旧社会”华丽转身为民国“新天地”。这些铺陈、罗列式的写作方式也成为其他民国图书效仿的民国范儿,就像《民国说明书》、《民国就是这么生猛》、《那个离经叛道的民国》一样,民国文化经过民国范儿的烤箱变成了风流倜傥的各色糕点,每个糕点都有不同的口味和成色,如章太炎是“疯”、刘文典是“狂”、辜鸿铭是“怪”、蒋廷黻是“犟”、胡适是“雅”、梁溯溟是“呆”与“直”等。在这种事无巨细的叙述中,历史并不长的民国变成了消费主义时代的文化景观。
与上世纪80年代所呈现的民国乱世英雄、大时代(大上海)的风云儿女不同,民国范儿更擅长讲述大人物的小日子、名士的“微历史”,恰如《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的序言中所述“这是一本随意翻翻的书—没有头尾,没有章节,没有次序”,内容就是民国名人们的饮食、穿戴、居所、家事、家境、起居、聚会、恩怨等日常琐事,或者如《民国笑忘书》中所述胡适的糖尿病、陈寅恪的择偶观以及《活在民国也不错》中公务员鲁迅买房记等民国八卦。这些民国图书如同供游客使用的旅行指南,只负责展示、呈现一种文化场景,并不诉诸于解释或探究风景背后的历史与社会缘由,仿佛一切都是浑然天成、自然而然。这种从大历史、政治史、国家史向小历史、个人史、物质史的转变,也是冷战终结、后现代文化的产物。文化不再像文化斗争、文化革命的年代那样承担着政治实践的功能,而蜕变为一种能够被展示、被消费的去政治化的旅游经济学,甚至连传统与现代、封建与启蒙、东方与西方等之间的价值对立也不存在了,都可以彼此兼容、打包销售。这种如中国卷轴画似的民国风物志,就像一张张孤零零地穿越历史尘埃的老照片一样,既储藏着照片所拍摄年代的文化信息,又在当下读者的注视下从具体历史脉络中抽离出来,变成一处可感、可触、可闻、可观、可把玩的文化“古玩”。
民国先生、民国女人、民国军人
在这场民国文化“展览”中,有3个展厅尤为引人注目,这就是玉树临风的“民国先生”、雍容华贵的“民国女人”和正义凛然的“民国军人”,这些曾经在中国革命史及近代史中隐而不彰的群体成为民国舞台的主角。民国先生是指有风骨、有气度的民国知识分子,“爱屋及乌”地,民国先生所属的民国大学也受到追捧(如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民国女人是有才华、有性情的名家闺秀;民国军人则主要指国民党抗战老兵。如果说民国先生是8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想象的新形态、民国女人展示了新的女性故事,那么民国军人则借他者之躯重述新的国家神话。正是这样3张面孔成为吸引人们“回民国住两天”的精神动力,也是“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诱惑所在。
民国先生是这三种形象中最具有民国范儿和民国精神的“模特”,也是民国图书中出版最多的主题。作为“民国背影”、“民国风度”、“民国底气”、“民国风骨”的民国先生,可谓包罗万象,几乎把近现代知识分子一网打尽,既有大学校长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傅斯年、蒋梦麟等,又有国学大师梁启超、钱穆、陈寅恪等,还有乡建知识分子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这些耳熟能详的民国先生成为“名角”与新时期以来关于知识分子的想象有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知识分子以归来的受难者、劫难的幸存者、暴力的反抗者的身份成为批判“文革”、反思革命的主体,形成了政治、体制、组织作为“压抑”与自由、独立、个人作为“解放”的二元对立修辞方式。如果说主动参与政治、自觉承担文化革命的责任是“五四”以来现代知识分子的主旋律,那么80年代逃离政治、追求自由精神则成为新一代知识分子的自我想象。这种体制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对立在90年代被表述为体制内与体制外、官方与民间的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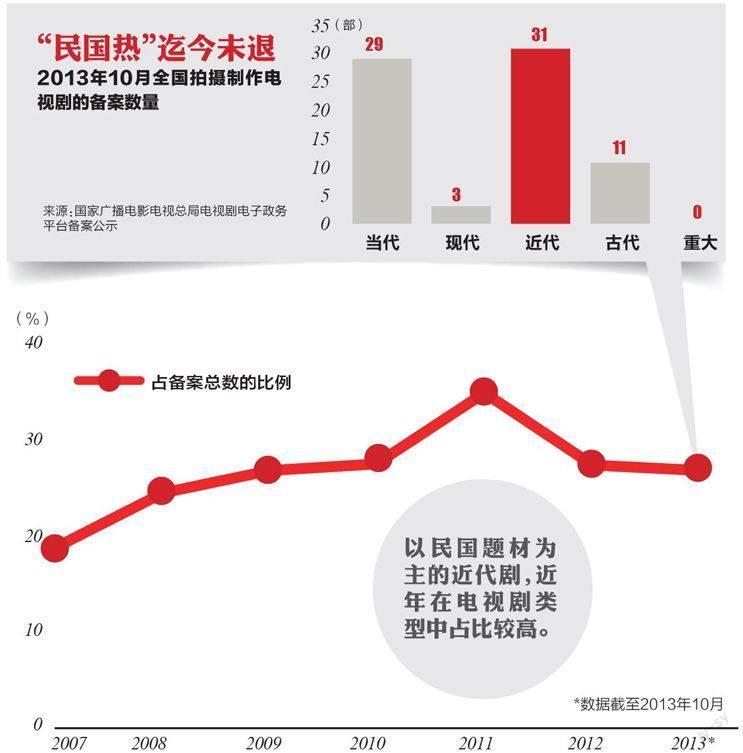
在90年代的大众文化中,最为流行的文化热点就是以亲历者的回忆录、随笔集为主的“反右”书籍,遭受政治迫害的右派被书写为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表,其中50年代受到批判的经济学家顾准、国学大师陈寅恪以及90年代成名、早逝的作家王小波则成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实践者,是反体制的文化英雄。相比80年代知识分子在体制内完成自我批判,90年代较为自由、独立的知识分子有了更为坚实的制度基础,这就是90年代市场化进程为体制外的民间想象提供了“真实的”社会(市场)空间。当然,在这种略带悲情的自由知识分子想象中,看不见的是同样在90年代处于体制外的农民工和从体制内下岗的工厂工人的身影,他们显然无法分享因市场的来临而释放的独立、自由的幻象。新世纪以来自由(民间)知识分子被民国先生的形象所取代,民国先生不仅大多拥有留洋(美)背景、是文化知识精英,而且在民国政府中担任要职,还保留着传统文人的风雅和趣味,可谓“脚踏政治、文化两只船”。从这里可以看出,民国先生绝非布衣先生,而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民国大佬、上流权贵和名人雅士,这也呼应着近些年对“富而有礼,贵而不骄”的贵族文化的向往。
与之相似,被人们津津乐道的民国女人也绝非“寻常百姓家”。如果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怀旧潮中晚清歌妓、民国月份牌美女以及旗袍女郎作为摩登上海的性感尤物,那么在民国范儿中女人则变成了一种“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名媛”。在《民国女人》一书的彩页中依次出现的女性是宋美龄、冰心、李霞卿(中国第一位美女飞行员)、林徽因、张爱玲、赵四小姐、何香凝等,这些出身显贵的女性不仅有大人物做丈夫(预示着和谐美满的家庭),而且也是有自己独立事业的职业女性(新女性)。这种新女性与高阶层的社会身份的结合,无疑示范着当下社会最让人“羡慕妒忌恨”的成功女人的形象。
在民国军人的想象中,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不是决定“建国大业”的国共之争,而是抗日战争。与民国先生、民国女人收编了八九十年代的大众文化想象相似,80年代就出现了国军正面抗战的历史叙述(如电影《血战台儿庄》等),以至于在《南京!南京!》(2009年)、《金陵十三钗》(2011年)等国产大片中抵抗日军的中国军人都是英勇善战的国军将士。最近新发掘出来的民国军人,是1942年作为英美同盟军的国军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已经出现了多部关于中国远征军题材的图书、电视剧和电视专题片,这些被遗忘的、承担国际责任的抗战老兵被命名为国家英雄。正如在一本“献给为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而战的中国军人和盟军军人”的书《国家记忆》中,作者从美国国家档案馆中找到当时美国随军摄影师拍摄的赴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的身影。在序言中作者深情地写道,“直到此前多少年,做梦都想不到,有那么多父辈的影像,如此清晰,宛如眼前。”这是一次借助美国摄影师的目光把曾经的敌人、国军重新指认为“父亲”的故事,而同名作者的另一本书直接命名为《父亲的战场:中国远征军滇西抗战田野调查笔记》,这种寻父之旅所实现的是把当代中国与现代中国“合并”为抽象的民族国家的过程。
民国想象的文化功能
从民国先生、民国女人和民国军人的形象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民国范儿与当下的主流文化有着多重的结合关系。只是这种去政治化的民国想象中渗透着充裕的政治偏见,这就是在这幅风姿绰约的民国图景中唯独没有左翼、革命、苏区、解放区的位置。虽然在陈丹青的《民国答问录》中提到纯正的革命范儿也沾染民国气息,但几乎没有左翼知识分子、左翼文化人出现在民国范儿的风景里,正如民国军人的序列中无法看见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身影。在这里,不用过多解读,人们“心知肚明”这种民国范儿是谁的民国、是哪一个民国。这种民国世界中反叛者的缺席,使得民国好风光无需面对为何最终付诸东流、烟消云散的疑问。这与其说展现了一个真实的中华民国,不如说是新时期以来从国共冷战对抗到恢复国民党作为民国正统位置的历史重写及其历史主体的置换。不过,借用一句老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以及福柯的名言“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民国想象的文化功能在于使当代中国实现了两重身份转换。
在50到70年代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叙述,一直采用从“近代”到“现代”再到“当代”的命名方式,当代中国(新民主义中国和社会主义中国)不仅是对现代中国(旧民主主义中国)的批判,更是一种超越。80年代在新启蒙、回到“五四”的历史想象中,当代中国比现代中国“进步”的逻辑发生逆转—现代中国被想象为启蒙与现代化的起点、当代中国则成为破坏现代化进程的“封建残余”,正如在上海怀旧潮中改革开放后的新上海直接把解放前的老上海指认为“前世”。在8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用现代化把当代中国与现代中国整合在一起的 “20世纪中国史”的论述(一种去除了50到70年代异质段落的历史),于是,当代中国完成了“去当代化”、变成了追求现代化的现代中国。90年代中国进入从体制内的微调转变为双重体制的转轨,30年代老上海、摩登上海、咖啡馆、购物街成为现代都市文明的理想空间。从这里也可以看出,90年代支撑上海怀旧的社会主体是刚刚离开体制获得自由的文化小资,而当下的民国范儿所询唤的主体则是随着中国经济崛起所浮现出来的社会上流精英。当然,从上海热到民国范儿的升级中,历史叙述的主体也从一个城市变成了民族国家。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加入WTO并实现经济崛起,一种从晚清到新中国的革命史、悲情史逐渐被大国复兴之路的历史叙述所取代,支撑这种宏大历史叙述的主体就是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核心情节为在挫折中不断追求现代化的历史。在这种背景下,已经现代化的当代中国再度“民国化”。这种“民国化”的过程,不仅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之交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角色转型,而且在想象中扭转了80年代以来个人(知识分子)与体制的对抗关系。与90年代“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不同,“民国先生”不再焦虑于体制与民间的二元对立,知识分子与政治、体制的关系从一种逃离、反抗变成了既深度合作又在“借古讽今”中保持独立人格的主体想象。人们穿越到民国不是一种从现实世界中解脱,而是渴望在民国中遭遇到更加真切的现实,一种与民国先生、民国女人“做朋友”的幻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