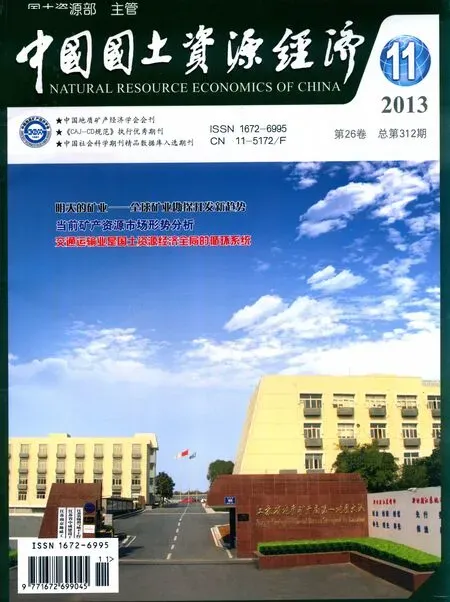交通运输业是国土资源经济全局的循环系统
徐 焘
交通运输业是国土资源经济全局的循环系统
徐 焘
各类交通运输设施网络是十三亿百姓生存空间的循环系统,也是提高国土资源使用价值和物化劳动价值的能动性因素。迄今为止的运输经济学虽言称要涉及到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两个方面,但是常止于把宏观效益视为各个运输环节单一价值要素迭加而成的所谓国内生产总值。然而,运输体系各个环节收支对比的总和仍然只是其微观效益,它的宏观效益是增减该环节对国土经济全局的实际影响,即所谓增益弹性,它必将牵动整个社会和国际间的诸多方面。
国土资源经济;交通运输业;循环系统;微观效益;宏观效益;增益弹性
环环相扣的陆路、水路、空运和通讯设施是把国土资源提升为更高层次经济实体的能动性因素。如果没有交通运输业和国土资源一体化的观念,就没有生动的国土资源经济学,运输业经济学也将限于门户之见。运输业经济学需要在国土资源经济学的基础上开辟自己的道路,同时也给后者注入新的生机。由此所涉及到的社会上和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更是学术界面对的开阔领域。
1 运输业的效用在于提高国土资源的经济功能
目前在学术出版物上能看到的提法大体是:交通运输业是国土开发、城市建设和经济布局的重要因素,因而需要从宏观上、战略上、全局性的高度突出交通运输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这些提法固然必要,但是还没有说到交通运输设施一经融入国土二者就一同跃升为更高层次的有机体,也没有涉及如何对二者协调功能的提高作量化分析途径。
通行的观点是:交通运输业属于第三产业的服务行业,能够支持各个地区发展经济,而它本身不提供实物产品。然而,如果鞍山的钢材不运到大连,不论鞍山还是大连都造不出海轮。可见,运输业是跨地域物质财富的生产环节,所以不可分别就运输或国土本身论事,需要把二者概括起来才能展现出更高层次的经济实体。在这当中,交通运输设施是国土资源得以成为各方通达的有机体的循环系统,是各地自然资源和劳动人口能协调运作的能动性工具。
修建通往松辽、新疆、西藏、南海诸岛和任何地区的水道、公路、铁路、航线以及通讯设施,是把国家主权范围内的所有地区提升为繁荣昌盛的家园和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需要。兴建跨国通道则是超越国家主权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步骤。马克思曾经提到交通运输业对土地经济丰度的差别“会发生拉平的作用。”[1]不言而喻,交通运输设施也能使原来有较高经济丰度的土地进一步升级。总之,马克思把运输业放到土地经济学的背景上来分析是我们需要深刻领悟之处。
国土资源与交通运输设施既然是有机的整体,就需要把二者当作统一的研究对象。否则,国土资源经济学会降格为类似东周时代的诸侯国土地经济学;而交通运输设施则会有百年前正定到太原窄轨铁路那样的狭隘性,或者像南满铁路那种自外插入吮吸民族膏血的管道。
与耕地开垦、城镇开发和矿藏探采作业一样,运输工程一经落地,就成为后者使用价值和物化劳动价值两重性功能升级的要素。这里说的使用价值指各个地理位置间的客货运输;这里说的物化劳动价值指社会必要劳动消耗。由于种种运输投资并非时时全额有效,而且有所谓沉没成本的不可逆性,比如闲置的路基只是土石方,无矿可采的井巷只是洞穴。就它们本身而言,毫无独立的资产可以估量,需要估量的是它们在发挥国土资源功能中的作用。这不像制造业设备那样能按原值和折旧率推算其现有资产值。
如果把某项交通设施提高国土资源功能的作用完全归结为前者的贡献,就像把马蹄铁说成是马能奔驰唯一的原因,未免以偏概全。交通设施是筑路者对早已是人们生息之地经济功能的提升,然而那是从基底更上一层楼的行为,不是在空间画彩虹。地面和高架路都要占地,航空站场和航线也要用地和地上的空间,通讯业仍然要立足于各方的地盘。没有任何不依存于土地的运输和通讯设施,就像没有任何不刻在石料上的印章或者不落在面料上的刺绣。无论道路的经济功能有多显著,如果没有人们共有的土地将无路可建,正如内陆国家不可能打开出海的通道,而有了土地就总能走出路来。交通设施既然要附着在土地上和为提高土地的经济功能服务,它的运营就不可自我规范,而要从属于全体人民的合理需要。因此,建设高铁和国道并不是交通运输部门筹措到资金就可以独立决策的。
贯通全国的交通运输业分层次经营属于微观经济行为,依靠交通运输业提高国土资源的层次则属于宏观经济运作。取舍个别运输环节对经济全局的量化影响可称为增益弹性,比如,铺设通往某边远地区铁路的货运能力增益弹性指数可写为:

铁路运力增益弹性指数E的取舍标准属于长远和全局性规划目标。
某项运输工程的总成效是其各个环节增益的积分。详尽地做出这类计算并非易事,但又不可绕行,于是就需要持续积累信息和逐步逼近准确答案。
交通运输业的均衡运行和它对国土经济全局的促进作用唯有通过理性的规划和调控才能实现。国家通过运输业影响经济全局是日常任务,开辟跨地区新干线是战略性举措。即使单从技术观点上看,也不可能由局部环节的运输业操控全局。所以诸如加开普通列车多载客还是加开高速列车多赢利那样的选择,应当根据四面八方客流和物流的需要安排,不能单纯按运输业利润率决断。
由此可以归结如下:
任何交通运输设施一经建成就与国土资源融合为有机的整体;
需要评估的是承载运输设施的国土资源经济功能的增益效应。
2 含运输设施的土地资产即其超额利润净现值
综上所述,既然运输设施一经落地就成为国土资源两重性经济功能有机的组成部分,前者将难以表征为投资者单一价值型金额资产。之所以直指公路或铁路作单一价值型资产评估,是投资者为了尽享国土资源之上交通业所得超额利润之举。这个评估金额无非按某时间段内该运输业现金流量和贴现率算出,即使评估者另作高深莫测的演算,其结果必定以或高或低的超额利润净现值为框架。在某个节点上高取评估值有利于原有股权但不利于新增股权,低取评估值则有相反的效果。其中的伸缩性尤其是局外者费解之处。
西方交通运输业是各个垄断集团耗竭需求者支付能力的竞技场。那里的火车票价与飞机票价一样浮动,以致同一班火车上相邻座位的票价都可能相差显著。
运输业资产评估金额也是核定其经营权发标价格的依据,以及相应股价总额起伏的回归线。
运输业股权的魅力,在于本该逐个反复核定其超额利润税率的理论、方法和制度还遥不可及,而且因赋税周期漫长就更有弹性。设置偏低的交通运输业经营权标底更网开一面。能够捷足先登者要的是筹措资金的能力,这也是金融业把握运输业的商机。尽管炒作者在角逐中莫测前景,毕竟能指望从截留超额利润税中得益(见表1)。
催生运输业板块高价的超额利润既然如马克思所说是消费者“过多支付的东西”[2],运输业投资者能赚取的理应只是工商业平均利润,超额利润当与房地产业中的土地增值税和矿业中的资源补偿费一同上缴国库,否则就难以防止投资者把广袤国土上的运输大动脉当作酷似油田井喷那样的财源。
不论运输业经营者获得超额利润是否合理,只要行规尚在,颁发其经营许可证的各级职能机构就会门庭若市,跨地区性运输业股权板块更是投资者趋之若鹜的热门。运输业板块指数也是沪深股市指数中的大项。其炒作者最希望有更大幅度的“国退民进”。这就是旅行者、货运者和股票炒作者身在局中而不尽知其真面目的交通运输业。
在高速公路入口处收费固然是偿还筑路和养路支出的需要。一度逐段无序设卡收费则属于巧立名目索取买路钱,或者垄断性土地使用权的非规范运作。动辄提升客货运价格和附加各种名目的提成亦属此例。
由于收缴矿业权价款者的“一堑”尚未转化成交通运输业利润税管理者的“一智”,以致由投资方和各级政府分割这同一项财源必有纠结:总额偏高会增加消费者负担,反之会使投资者暴富,最后的结果一概要回归到居民项下。
一旦运输业超额利润税制得以规范化,这个行业自行其是的资产评估也必将改弦更张。既然不论有无交通设施的国土资源都归劳动者共享,就没有买卖双方的对局,任何人本无需关注承载交通运输设施的土地价值几何,因为那是不可估量的“无价之宝”,不论何许都是公有。体现运行交通业费用的合理运价才更实在。
由此可以再作归纳如下:
运输业资产是由承载运输设施的国土资源所获超额利润净现值;
运输业超额利润税当与矿产资源补偿费和土地增值税同例上缴。

表1 运输业超额利润走向
3 运输业自主权是国家领土完整的重要方面
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时需要区别对待各行各业。与加工原材料并销售成品的制造业不同,亚非拉诸国的运输业如果办成类似两百年前的英资南亚铁道网,或者像上世纪初中国境内的俄资中长线、日资南满线、德资胶济线、比荷资陇海线、法资正太线和滇越线,就将使自己沦为网中之鱼。全国百姓夺回胶济线的群情曾经是五四运动的重要原因,收回中长线的协议在中苏建交初期终于达成,其它各条铁路也先后实现国有化,尤其是保护成渝线开发权的民族传统更得以延续至今。
加拿大作者所著《世纪大拍卖》报道了前苏联门户洞开变卖不动产落入“华盛顿共识”的设局,使这个泱泱大国积累七十多年的巨额财富支配权梦魇般灰飞烟灭[3],尽管年久失修的实物性生产和生活设施仍在原地。东欧各国捐弃公有制进而丧失民族独立性的灾难表明,危机临门前必须果断实行任何自然资源开发业的国有化,优柔寡断将万劫不复。早在中苏建交的1950年初,中方就留意到共同开发新疆矿藏应当无损自己的主权,的确有深谋远虑。
由此可以进一步归纳如下:
运输设施及其依托的国土资源不仅是公有财产而且体现国家主权;
投资者即使能分享经济收益也无权支配运输设施及其立足的土地。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733.
[2]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745.
[3]克里斯蒂亚·弗利南.世纪大拍卖[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240.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is the Circulatory System for the Overall Economy of Land and Resources
XU Tao
The network of all kinds of transportation facilities is not only the circulatory system for the living space of 1.3 billion people; but also the dynamic factors for improving the use value and materialized labor value of land and resources. So far, stating the transportation economics would involve two aspects of microeconomic and macroeconomic, but it stops at the so-called gross domestic product which considers the macro beneft as the superposition of a single value element of all transport links. However,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total of the contrast of income and expenditure with regard to various links of transport system are still its microscopic beneft; and its macro-beneft is to increase or decrease the real impact on overall land economics of this link, namely the so-called gain elastic, which is bound to affect many aspects of the whole society and internationally.
land and resources economics;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circulatory system; micro benefts; macro beneft; the gain elastic
F062.1;F503
:A
:1672-6995(2013)11-0014-03
2013-08-26
徐焘(1933-),男,上海市人,研究员,大学本科,20世纪60-70年代曾在冶金系统从事矿藏勘查、资源管理和矿业经济学研究,80年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及研究生院作为副教授从事技术经济学研究和教学,并在有色金属加工工业协会任研究员;90年代初起在加拿大德林矿业咨询公司任高级经济师;90年代末至今从事独立的国际矿业经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