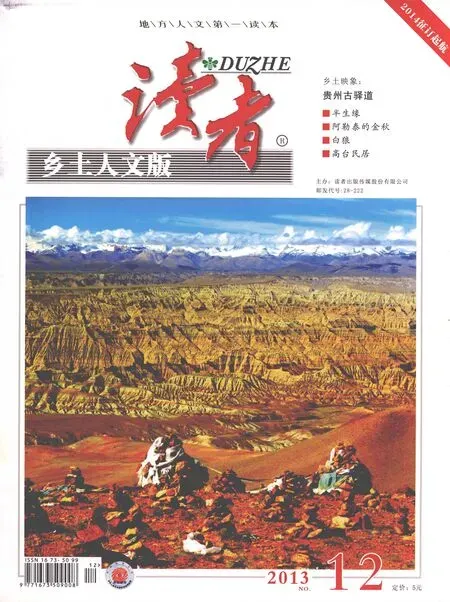陕 北 柳
文/朱景敏
陕 北 柳
文/朱景敏




走进陕北,随处可见一种伞状的柳树。这种柳树树身短粗,顶端一根根笔直的椽子像伞架般张着,一头的翠绿盖在这些椽子上。
陕北柳不似江南柳般婀娜,不像塞外白杨般挺拔,不及黄山松之长青,不如曲阜柏之长寿,只是极普通的树。因为普通,陕北的河道、沟渠、山坡、崖畔,处处都有它的身影。然而,它是一棵母亲树。它像那片土地上的母亲们一样,一生都在为自己的儿女出力流汗、耗费心血,直到老朽成一根枯木,也要再挣扎出一丝绿……
带着母亲的血肉和体温,它出嫁了,嫁时还没有一丝根须。它从母亲的身上被直接砍下来,削得只剩一根直杆时,嫁给了河边的泥土。它就这样赤条条地安家,光溜溜地奋斗,从滴血的伤口上生根,从裸露的肌肤上萌芽,在第一个冬天来临之前,努力地长成了树形。
摇摇摆摆度过冬春,它学着母亲们的样子,开始了第一次梳妆。它将几支倔强的小辫冲天扎起,辫梢的绿就如花般散开。它总是迎着风娉娉婷婷地站着,少女般期待着人们对它的赞美。那时,它不但纯洁甚至还有些懵懂,它不知道那冲天的小辫,完全是一个女性为了一生的繁衍而孕育出的生命的胚胎。
长到五六岁时,冲天的小辫儿变成了硕壮的椽子,浓密的绿已经在为怕晒的懒狗和倒沫的老牛遮阳。放学后的孩子再也撼不动它的腿脚,小雨前的清风也再扭不动它的腰肢。毛驴靠在它身上蹭痒,它不恼;山羊抵在它身上磨角,它不烦。它早已成熟得像陕北的母亲们那样,过早地开始履行生育的天职,开始承受生活的苦累。
它努力地将树枝向上竖起,为的是让阳光更近地温暖每一片叶子。它拼命地把树根向下扎去,为的是使水分更近地滋润每一丝根须。它尽情地享受着大自然的恩赐,很快就用阳光雨露喂养出第一茬茁壮的孩子。
送子出征或送女出嫁是激动人心的事,但母亲们在那一刻常常流着酸涩的泪水。第一批椽子成熟了,当主人提着利斧向它走来时,它颤抖着摇落了一树黄叶。那个季节,主人已收获了当年所有的谷禾豆薯,它擎托着的椽子,是主人这个秋天的最后一笔收成。它早已从追逮蚂蚱的裸身小子或驱牧鹅鸭的赤脚少妇嘴里得知,主人正等着用这些粗壮的椽子,给他第三个儿子的新窑洞制作雕龙的窗棂和添置待客的炕桌。它为自己孩子们的成材而自豪,它为能给主人的生活带来幸福而自豪。它时时都在想着报答主人的养育之恩。它面对利斧时的颤抖,只是分娩前的阵痛和离别时的酸楚,它的心里是甜的。
从献出第一茬椽子开始,陕北柳再也没有停歇过,每隔三五年,它就几根、十几根、几十根地将椽子呈奉给主人。于是,主人家屋里屋外、门前院后便处处是柳制的家什—门窗、箱柜、米仓、面囤、扁担、水桶、锄把、连枷,甚至毛驴的驮架、黄牛的犁杖、绵羊的圈栏、猪娃的食槽……
年轻的主人变成耄耋老人时,陕北柳也能说出老人膝下几十个儿孙的名字,但它无法计算出从自己的身体上究竟砍下了多少根椽子。它忘记了多少个夏天,炸雷在头顶轰响,洪水在脚下吼叫;它记不起有多少个冬天,狂风从身上刮过,大雪向肩头压来。炸雷烧焦了它的梢,洪水冲露了它的根,狂风刮断了它的枝,积雪压弯了它的腰……但它始终坚持着。它坚持着,因为在它的早已老朽的身体上,正擎托着几十个嫩绿而茁壮的孩子……
它渐渐老去的时候,孩子们继续发疯般地成长着,它们毫无节制地攫取着它的营养。它们的精力是那样旺盛,它们的胃口是那样空阔。它越来越力不从心,它拼命从大地深处汲取营养,但无论如何也无法满足它们急于长大的需求。于是,它开始透支自己的身体,把自己的血和肉直接输入孩子们的体内。孩子们长大了,而它的身体被掏空,只剩下一层坚硬的皮壳,支撑着一树翠绿的重压。
在最后的日子里,它变得枯干老丑,粗壮的树身只是一副皮囊,顽皮的儿童随意从它身上的那个树洞钻进去,顺着它空阔的胸膛就能攀上树顶。树顶只剩一两枝有绿的细椽,其余全是当年一茬又一茬砍椽子时留下的结成疙瘩的疤痕。枝头上少了喜鹊,树洞里没了狐狸,就连好心的啄木鸟也不再来它身上敲打,因为它已枯竭得无法提供几只虫子的营养。
陕北柳终于老去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它的树身甚至枯朽得不能成为引火的劈柴,只能慢慢腐朽成一堆泥土,最终融入陕北的黄土地。黄土地上的陕北柳,黄土地里的母亲树,它就像我们黄土地上的母亲们一样,养育了黄土地的一切……
(金曼余摘自《散文百家》2013年第9期)
——碧麟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