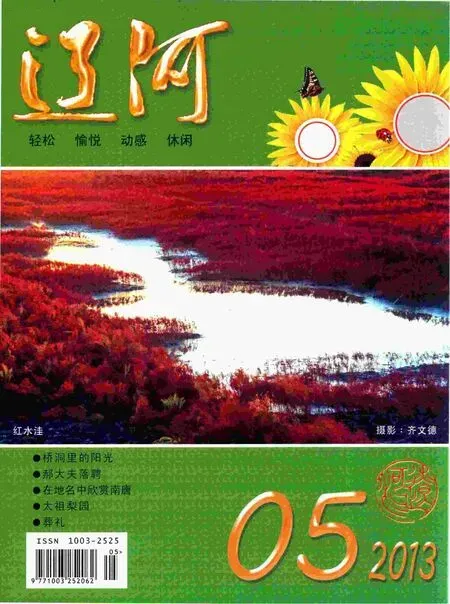久远的弥香
李秀荣
面酸酸的烀山杏
“当——当——当”,一阵响亮的锣声在山顶上震颤过后,兰姨便扯开她铜锣似的高嗓门,“唿嘘——唿嘘——”地吆喝起来。
兰姨,十八九岁的样子,细高个,梳着两条甩过腰的大辫子,格外精神。嘴不大,但嗓门却赛过铜锣。也许正因为她嗓门最尖,生产队才让她看青的。
那是四十年前的事了,那时我才七岁,还没上学呢。一年四季,经常去姥姥家玩耍。
那年头,生产队种完地后,各个山头都要派一个人看青。所谓看青,其实就是站在山头提着一面铜锣,像电影中的更夫那样在山头巡逻,看着老鹰、獾子和野鸡野兔野鸟什么的别偷吃刚下地的种子。俗话说,“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有钱买粱,没钱买苗”,春天种子下了地,要是让山上的动物扒吃了种子,那一年的收成就泡汤了。
兰姨也许是最认真的人,要不怎么会让她看青呢?我没怎么考虑这些,也不记得她到底看几面山梁。只记得,那天早晨,她身穿天蓝色对襟小夹袄,一双家做的蓝帮布底鞋,特别精神。她闲悠悠地从姥姥家门前经过,见我站在门口,就亲热地招呼我跟她一块上山。
我经常去姥姥家,早就认识兰姨。我和她亲近,是在一个火热的夏天。姥姥领着我去南沟割韭菜,路过兰姨家门口,兰姨正光着脚丫,坐在窗台上纳鞋底。她一见我,大声喊我等一下,我还没反应过来,只见她鞋子也不穿,“腾”地从窗台上跳下来,跑进院中的菜园,就给我摘了两根水灵灵的嫩黄瓜。
兰姨唤我,我欣然跟她去南岭玩耍。
从姥姥家出发,兰姨一手提着锣,一手拉着我,沿着南沟蜿蜒曲折的羊肠小路,一边哼哼着没有名字的小曲,一边眼睛滴溜溜四下搜寻。我乖乖地跟着兰姨,好奇地四下看着。山坡上,那些粉嘟嘟的杏花都变成了玻璃球大小的山杏了。矮墙下和地边,很多很多的杏芽菜和蒲公英,水灵灵的,鲜嫩嫩的。
兰姨对这些似乎不关心,只是眼睛滴溜溜只瞄着墙窟窿。果然,不一会儿工夫,竟然从墙窟窿里掏出一窝鸟蛋。一数,竟有七个呢。“快,给你!”兰姨把鸟蛋小心翼翼地装进我的衣兜,然后跑到地边的老杏树下,又摘了满满两小兜的山杏。
生产队已经种完了地,南岭的沟谷和山梁一片葱绿,大树小树都枝繁叶茂。我最喜欢的映山红已经卸下了盛装,只有那些素雅的小白花还神采奕奕地绽放着妖娆。山坡、地头一树树山杏,亮星星一样闪着银辉。
站在山梁上,兰姨“当当当”,先打了一通锣,然后又放开嗓门吆喝一阵。锣声、吆喝声,吓得山鸡和野兔从树窠里“扑棱棱”,立刻就飞远了。这样兰姨就完成了任务。这会儿便是哄我玩了。只见她在山梁上猫腰走了几步,就找来了三块不大不小的薄石板,在避风的大岩石旁三下两下,就搭成了一个小锅台。只见兰姨先把兜里的山杏都掏到了锅台的石板上,再把我的鸟蛋放在山杏上面。然后又寻来一块薄石片,盖好鸟蛋和山杏。兰姨是有备而来,捡一些干树枝,填在临时的灶台里,点燃火柴,一股青烟袅袅升起。我惊奇地望着兰姨娴熟地做着这些,只觉得有一股清香沁入心脾。
等到山杏、鸟蛋烀熟,兰姨熄灭火,揭开石盖,我俩就坐下来尽享美味。鸟蛋,兰姨都让给了我;山杏,酸酸的,软软的,面乎乎的,那美味四十年后依然还在我的唇边萦绕。
一连好几天,我都跟着兰姨上山,每次,都能吃到烀山杏和鸟蛋,直到今天我还想吃兰姨的烀山杏。
可是,后来,我上学、上班了,等我假期再去姥姥家时,兰姨已经嫁到很远的他乡去了。几十年过去了,我竟无缘再见兰姨。
每到花开时节,我便会想起身着蓝夹袄,甩着长辫子的兰姨,好想好想再吃一顿她烀的山杏!
皱巴巴的麻楸子
说起核桃,恐怕谁都知道它的营养价值,但若说起楸子和麻楸子,恐怕就鲜有人知了。
小时候,我一去姥姥家,姥姥就端个四方方的小升,颠着小脚给我舀楸子。那升是木头做的,是过去称粮食的计量工具,四方方的,称粮食一升正好十斤,十升正好一斗。姥姥端来满满一升楸子,里面还有许多皱皱巴巴的麻楸子,很像核桃,但又不是核桃。那麻楸子其实是一般地方难得见到的。一个麻楸子足足顶两个楸子,它皮厚,略扁,和核桃一般大小,但比核桃皮厚,其果仁富含植物油,只因皮厚不能与核桃媲美。
三舅搬来一大一小两块石头,给我和小姨拍楸子吃。大石头垫底,放在屋地当央,正对着后门,小石头当锤子。姥姥家的后门外,是一片绿油油的果园,有梨树、杏树、桃树,还有麻枣树,还有什么树,我都记不清了。园子上面,几块不大的梯田,长着茁壮的苞米和高粱,地头还有一畦绿盈盈的大葱。梯田之上,是高耸的山峦,密密匝匝的树木,遮挡着姥姥家的后门和当屋。我和三舅、小姨坐在小板墩上,一边吃楸子,一边尽享风凉。
姥姥给我们每人各找一个纳鞋底的锥子,让我们自己拨楸仁吃。我们三个围在一起,边吃边说笑,一升楸子常常吃个小半天。
那时,我最喜欢吃楸子。小姨常常吃了一把楸仁,就说腻得慌,然后就把楸仁拨出来,给我和姥姥吃。而三舅则是边用石头拍楸子,边顺手捡起掉出来的大仁往嘴里扔。三舅拍楸子,是用一块长方形的小石头当锤子使,左手捏着楸子的中间部位,右手举起小石头,不偏不歪,正好砸在楸子的顶部。楸子中间有一道竖纹络,砸正了,楸子会顺着纹络裂为两瓣,两边金黄色的楸仁就鼓冒出来。有不太成熟的,可以用手指捏出来,但大多需要用针状的东西拨出来才能吃到。那年月,楸子对于小孩子来说,是最美的佳肴。我们从小就学会了吃楸子,拿起楸瓣,放到嘴边,一边用锥子拨,一边往嘴里吮吸,常常吃得嘴丫子直冒油。吃渴了,就咕咚咚舀凉水喝。
三舅手不闲着,嘴也不闲着,尤其是砸到麻楸子,三舅就撂下石头,自己先掰大仁吃。小姨看见,撅着小嘴一个劲埋怨三哥贪吃,不知怜爱我这个小外女。其实,小姨只比我大四岁,三舅不过比我大六岁。望着眼前一大堆的楸子和楸仁,我觉得三舅和小姨特别可亲可敬。
“知了,知了!”秋蝉在姥家门口的麻楸树上,高一声低一声地欢叫着。麻楸树约有一搂多粗,很高很高,树底下是一块比三户人家房子还大的青石板,斜铺在河对岸山坡上,清亮亮的小河长年潺潺地流淌着。
三舅和小姨都上学去了,我便跑到下坎儿的老张家,去找比我小两个月的芹,一起玩耍。
芹也7岁,和我一样,都没上学。她长得有点矮,但眼睛很大,嘴角总是带着甜甜的笑。她整天扎着一个小歪辫,一跑小辫子就一晃一晃的歪来歪去。我和她嬉笑着在门口的小河里戏水,逮小鱼,玩腻了,就爬上麻楸树下的青石板去晒太阳。一会儿仰躺着,一会儿对坐着,一会儿又瞪起眼睛找寻“知了”隐藏在哪片叶子下面,一会儿又淘气地找根长长的柴禾棍,跷起脚尖,捅下一串低垂下来的麻楸子,然后蹭下青石板,到小河边捡起刚刚捅落的麻楸子,在水中的大石头上,把麻楸子厚浊的皮磨得干干净净。然后我俩一人手里攥着三两个麻楸子,再一次爬上那片大青石板。
其实,那时的麻楸子已经成熟了,只是姥爷习惯让它长到自然落地,说是那样楸仁更成熟。
对于麻楸子什么时候成熟,我并不在意。我只觉得那棵麻楸子树特别高大,特别有趣。又大又扁的麻楸子攥在手心里,皱皱巴巴,麻麻约约的,比核桃好玩多了。砸开,楸仁比一般的楸子要多一半,真的趣味非凡。还有芹,我们天天在麻楸子树下玩耍,总有做不完的游戏,总有无限的快乐,更有依依不舍的情。
记不清了,曾有多少个流火的夏日,多少回小河里的嬉戏,且吃过多少普通的楸子和那形状怪异的麻楸子。几十年过去了,三舅和小姨早已成了大人,芹也嫁到了异乡;小河依然清清凉凉,河对岸的青石板依然干干净净,可那棵高大的麻秋子树却不知怎么不见了。
去年冬天,隔壁的三哥领来一位远方的客人,四处打听哪里有卖麻楸子的,说一个麻楸子价值6元。
天啊,我大吃一惊!那皱巴巴的麻楸子何以这般高贵?我不禁默默呼唤芹——你还记得那棵麻楸子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