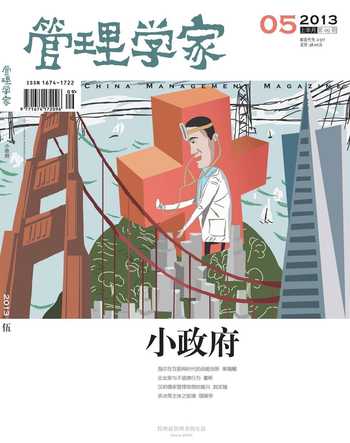秦制和楚风之间的儒学复苏
秦始皇建立起来的大一统国家和皇帝体制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经过汉代的传承,秦的王朝体制延绵达两千年。学界把秦汉之间的制度传承概括为四个字——“汉承秦制”。从国家管理的角度看,汉代的各项制度规范多数出自秦朝。然而,强调汉承秦制者往往忽略了秦与汉的差异性。西汉王朝的开国者,多来自楚地,在骨子里渗透着楚人的不羁血性。汉继楚风,从而扭转了汉初国家的价值取向,如果没有汉人对秦制的调整,秦制就可能延续不下去。从秦到汉,我们既可以看到制度的延续性和国家管理的路径依赖,又可以看到文化的变异性和社会风俗对国家管理的重大影响。学界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史学领域,往往对汉承秦制较为重视,而在文学领域,往往会首先感受到汉人身上的楚人习气。汉代的制度框架是秦制,而汉代的精神状态是楚风。或者说,汉制即秦制,汉韵即楚韵。把握大汉文明的特色,这两者不可偏废。
在秦制与楚风之间,汉代走出了一条国家管理的新路。在这条路上有两个人值得重视,一是告诫皇帝不可“马上治之”的陆贾,二是以秦为鉴提出“治安策”的贾谊。他们的思想,不仅在汉初影响到当权者执政风格的变化,而且对以后的王朝体制如何治理社会起到了探路作用,最终走向以儒术治国。
陆贾是楚人,不过,他的学问来自儒家。清朝唐晏在校注陆贾著作时说,陆贾是荀子的学生,而且是谷梁学的祖师,排在汉代公认的谷梁学大师申公之前。正是这种儒学功底,为他扭转西汉治国方向奠定了基础。在秦末天下大乱中,陆贾追随刘邦,鞍前马后,以口才著称,战争中陆贾表现出来的不是儒家学问,而是纵横捭阖的游说才能。他曾经在刘邦进军关中时游说秦将,在楚汉相争时与项羽谈判。在刘邦建立汉朝后,陆贾列在首位的功绩是出使南越说服赵佗臣服汉朝。不过,就管理思想而言,陆贾的最大贡献,是促使刘邦立国后由武功向文治的转化。
按照司马迁的记载,刘邦在打天下的过程中是看不起儒生的,而陆贾难免显露出儒者本色,同刘邦谈话时常常引用《诗》《书》,所以遭到刘邦的叱骂:老子的天下是马背上打下来的,凭什么要遵循《诗》《书》?陆贾正色回答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从历史经验看,吴王夫差,晋国智伯,都是崇尚武力的强者,结果却亡在了武力上。秦朝严刑酷法,迷信暴力,结果却断了自家香火。如果秦朝建立后改弦易张,“行仁义,法先圣”,陛下还能得到天下吗?刘邦说不过陆贾,就下令道:“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于是陆贾写出十二篇治国镜鉴。“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史记 · 郦生陆贾列传》)可以说,陆贾在扭转汉初的治国方向上是有所贡献的。
陆贾之后,在治国理论上进行系统思考的还有不少人,沿着儒学路径向前走的代表是贾谊。贾谊是河南洛阳人,少年聪颖,“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史记·屈原贾生列传》)。18岁时,就被河南郡守吴公看中,网罗于门下。汉文帝时,吴公升迁到中央当廷尉,向朝廷推荐贾谊,于是贾谊被征召到首都任博士。
博士是秦汉设置的顾问应对官职,没有编制限制,没有具体职掌,以议论朝政为业。所以,博士能不能发挥作用,主要看皇帝是否重视。秦始皇时,“天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虽有几十名博士却“备而弗用”。汉文帝时的博士就不一样了,文帝由藩王入主朝廷,在朝中缺少亲信,急需得力辅佐。而贾谊在博士中最为年轻,头脑敏捷,应对得当,在一群老朽冬烘先生中脱颖而出。“是时贾生年二十馀,最为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孝文帝说之,超迁,一岁中至太中大夫。”(《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贾谊的思想很杂,其少年的知识基础当以儒家为主,欣赏他的吴公又从李斯之学,贾谊有可能会受到其影响,司马迁说贾谊和晁错“明申商”,即对法家学说比较熟悉。他还跟随御史大夫张苍学习过《左传》,在汉代率先对《左传》进行文字训诂研究,汉代《左传》的流传实际是从张苍和贾谊开始的。另外,贾谊还受到当时流行的黄老之学的影响。所以,尽管刘歆称文帝时“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汉书·刘歆传》),但贾谊带有汉初儒者不同于先秦儒者的明显特色,即杂糅百家,兼习道法。这一过程,到董仲舒方告完成。
贾谊少年得志,意气风发,渴望在政界施展才能。文帝也确实欣赏贾谊,很快就把他由比六百石秩级的博士提升到比千石秩级的太中大夫,相当于今日由副处一跃而进入司局。级别倒是小事,关键是他因为皇帝的重视而进入了决策核心。政策的变化,法律的修改,对诸侯管理策略的调整,都出自贾谊的提议。于是,文帝打算把贾谊进一步提拔到公卿之列。但是,朝中的反对意见越来越大,一批元老大臣担心贾谊得宠,开始攻击他。中国的政治体系有个特点,欲速则不达。如果贾谊停留在太中大夫的层次暂时不动,尽管元老仍然会讨厌新贵,但多半会看在皇帝的面子上容忍他。现在皇帝有意让他进入三公九卿行列,这就危及到开国元勋的地位。于是,以丞相周勃、太尉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为代表,下决心要把贾谊拉下马。他们对贾谊的评价是“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政事”,必欲除之而后快。文帝的帝位又是这些元老与吕氏争斗而得来的,朝中几乎没有文帝的亲信,他只有表现出对周勃等人的高度尊敬和信任,皇位才可稳当。所以,文帝只能牺牲贾谊,把他外派为长沙王太傅。长沙王是当时唯一的异姓王,经过汉初的权力纷争,其他异姓王都已经被铲除干净了,只剩一个根本掀不起风浪的长沙王,这个王爷自己都提心吊胆,何况辅佐他的太傅。把本来在权力中心的贾谊派给长沙王,几乎同流放差不多。贾谊自己也灰心到了极点,凭吊屈原,写《鵩鸟赋》,摆出一副人生道路走到尽头的架势。这个时候的贾谊,已经淡漠了儒家的进取理想,沉湎于楚风骚韵。如果当时有现在的医疗检测手段,恐怕能给他检验出抑郁症来。
天无绝人之路,文帝思念旧情,召见贾谊。时值文帝正在祭祀,便在未央宫的宣室询问贾谊鬼神之事。贾谊对答如流,再次给文帝展现了他的才能。诗人李商隐曾感慨文帝“不问苍生问鬼神”,给世人留下一个文帝对贾谊用非其才的印象。其实不然,在汉代,祭祀是政治行为中相当重要的活动,鬼神与国家安危大有关联。但是,文帝受制于大臣,不能把贾谊直接用到中央关键岗位,也是实情。这次召见后,贾谊的命运明显改观,他被改派为梁怀王太傅。同原来的长沙王太傅相比,这两个太傅大不一样。在长沙王那里,等于政治生命的终结;而在梁怀王这里,等于政治生命的重新开始。梁怀王刘楫是文帝的小儿子,聪颖好学,深得文帝喜爱。让贾谊辅佐梁怀王,无疑等于明示:好好干,总有出头之日。贾谊对此当然心领神会,于是,在辅佐梁怀王之馀,又开始上书朝廷,畅言国事。根据学界的考证,贾谊最重要的政治论述《治安策》,就是这一时期写出来的。
然而,世上不如意事总十有八九,意外往往会打乱事先的筹划。梁怀王坠马身亡,对贾谊的打击太大。史称“贾谊自伤为傅无状”,哭泣岁馀而死。很明显,贾谊既为梁怀王的夭亡而哭,也为自己的命运而哭。但一切都无法挽回,梁怀王死后仅仅一年光景,贾谊也郁郁而亡,年仅33岁。
秦王扫六合,睥睨天下,建立了大一统的秦制。外表十分威猛的帝国,却被不读书的项羽刘邦推翻。高唱《大风歌》的汉高祖,以楚风的豁达消解了秦制的戾气,却未能改变自身的赳赳武夫形象。此后西汉的变革,开始于秦制和楚风之间的儒学复苏。这一儒学复苏过程,同叔孙通、陆贾、贾谊、晁错都有关系。叔孙通最先以礼仪形式为儒术见用于朝廷做了铺垫,然而这种铺垫并不具有思想史意义,仅仅是让刘邦感受到儒术对维护皇帝的尊贵有用而已。陆贾真正开启了汉代儒学之端,他以纵横家的口才留下了“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的名言,并提出了取守异势的基本思路。贾谊实现了儒家学说与帝制关系的改造,使仁政王道与中央集权融合,同时又在具体治国方略上吸取了法家的具体举措,把国家制度与风俗文化结合起来,形成了以儒术为主的治国方向。晁错在贾谊的基础上,向法家靠拢,在儒术的外表中更多地注入法家的内涵。到了董仲舒则以诸家渗透的方式完成了儒家学术的大一统修正,汉制由此确立。汉宣帝所说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深得汉制的精髓。给汉制奠定儒家基础和王者形象的,以贾谊最为着力;完成这一演变过程的,则以董仲舒最为出名。
儒学复苏和儒者从政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陆贾和贾谊的政治命运,是儒者从政的一个范本。严格来说,从陆贾开始,儒者从政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先秦儒者不少,孔门弟子有的在政坛相当出色,然而,他们面对的是列国纷争,在秦完成统一后,儒者还能不能在政坛上有一席之地,谁也难以断言。人们所熟知的焚书坑儒,给从政的儒者敲了一记警钟。叔孙通为此不惜放弃儒家的思想内涵,可以用谀言奉承秦二世,可以用楚服换掉儒袍讨好汉高祖,进而可以用古礼夹杂秦仪设计出朝贺仪式取悦皇帝。在叔孙通导演的朝贺仪式中,刘邦发出“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的感叹。这不是儒家从政,而是儒者在政治面前的屈膝,所以,坚守儒家信念的人鄙视叔孙通。陆贾则触及到了以儒术治国的本质,但是,陆贾的形象,更多地偏于策士和辩士。同贾谊相比,陆贾要幸运得多,这种幸运,正是来自于陆贾对儒术的变通。以陆贾获取极大名声的出使南越为例,在游说南越王赵佗时,陆贾说服赵佗的观点,来自儒家的夷夏之辨和孝悌之道,而打动赵佗的方式却是王国安危和利害关系,显然,儒家式的道义观念,法家式的利害算计,纵横家式的危言耸听,被陆贾糅合为一体。陆贾的这种策略,使他既能做到要求刘邦“下马”,又能确保自己安然无恙。当他给刘邦提出“下马”建议时,既强调“行仁义,法先圣”,又推崇俭约,要求人主无为。陆贾的聪明,还表现在对待吕氏上。当吕后把持朝政时,陆贾称病引退,悠游享乐。但他又私下给陈平出谋划策,让陈平结交周勃以对付诸吕。文帝能够当上皇帝,也有陆贾一份功劳。文帝即位后,陆贾又担任太中大夫,后来再度引退,“竟以寿终”。班固在比较陆贾和郦食其、朱建、娄敬、叔孙通等人后赞曰:“陆贾位止大夫,致仕诸吕,不受忧责,从容平、勃之间,附会将相以强社稷,身名俱荣,其最优乎!”(《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可以说,陆贾以其灵活变通,为后代儒者从政提供了一个榜样。如果说叔孙通是内圆外滑的“识时务”儒者,那么,陆贾就是内方外圆的“善变通”儒者。
贾谊同陆贾有相似之处,就是在思想上都受到道家、法家的影响,其儒家基调虽在,却已经不能回归到先秦儒学,只能根据大一统格局调整自己的治国学说。但贾谊与陆贾的不同在于,他的行为不善变通,有点“一根筋”,这同他早年一帆风顺有关。吴公的赏识和推荐,文帝的器重和提拔,使他不知什么是挫折,看不到政治的险恶。他本来要一鼓作气,主持汉朝的制度变革,“汉兴至今二十馀年,宜定制度,兴礼乐,然后诸侯轨道,百姓素朴,狱讼衰息。”文帝当然乐意接受贾谊的提议,按照《汉书·礼乐志》的记载,文帝虽然高兴,但周勃灌婴等人不高兴,他们本能地觉得贾谊以年轻新锐的角色冲击着元老勋臣的地位,于是共同发力,把贾谊赶出朝廷。对于贾谊受到排挤这一事实,学界主要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源自汉代刘向,认为贾谊才高遭忌,庸臣排斥贤能。“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汉书·贾谊传》)这种说法得到后代的多数人认可,尤其是怀才不遇或者才高见弃者,很容易对贾谊产生同情心理。加上司马迁把贾谊与屈原合传,更会使读者类比屈原而产生联想。另一种解释以苏轼为代表,他专门写有《贾谊论》,认为贾谊自己处置不当。苏轼也承认贾谊是王佐之才,但不能“自用其才”。汉文帝不用贾谊,错不在文帝而在贾谊自己。“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绛侯周勃是拥立汉文帝的首席功臣,太尉灌婴统兵数十万与吕氏一决雌雄,他们与汉文帝的关系,要比父子兄弟骨肉更密切。贾谊一朝被重要,就不知天高地厚让文帝“尽弃其旧而谋其新”,这不比登天还难?贾谊要想站住脚,就应该“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以高超的政治见解打动皇帝,以优游浸渍深交大臣,“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谈之间而遽为人痛哭哉?”试观贾谊吊屈原,赋鵩鸟,“是亦不善处穷者也”。所以,苏轼认为贾谊是“志大而量小,才有馀而识不足也”。苏轼之所以专门把贾谊拿出来大发议论,其目的是为儒者参政提供一种思路。“愚深悲贾生之志,故备论之。亦使人君得如贾谊之臣,则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不能复振;而为贾生者,亦慎其所发哉。”平心而论,苏轼的议论不见得公允。例如,周勃、灌婴与文帝的关系,并不像苏轼说得那样和谐。然而,贾谊不能忍辱负重,确属其短。可以说,贾谊的悲剧,为儒者从政提供了两方面的教训。从与叔孙通、陆贾的对比来看,贾谊是真儒者,进取和狷介正是对先秦儒者精神的继承,而陆贾的圆融,有可能使儒者失去自我;叔孙通的不讲操守,更会以投机行为使儒者变质。贾谊的可贵,在于其守住了儒家的根本。然而,贾谊缺少了儒家通达的一面,经不起逆境磨炼,这又使其人生走向偏隘。平心而论,汉文帝还是尽可能采用了贾谊的政治主张。所以,班固才称其“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
此后历代王朝,儒者从政,基本上不出叔孙通式的放弃操守、陆贾式的圆通和融、贾谊式的耿介狂狷三种类型。而三种不同际遇,又对儒家管理思想的发展演变形成不同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