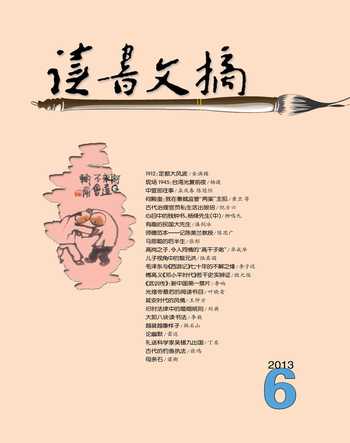有趣的民国大先生
金 岳 霖
金岳霖的癖好之多在朋友圈中那是出了名的。他喜欢诗词,尤其酷爱清人诗词,能熟背很多清代诗人的诗词。有时候兴起,他还会做一些“歪诗”,辛亥革命爆发后,金岳霖就剪去了头上的辫子,还仿唐诗《黄鹤楼》写了首打油诗:“辫子已随前清去,此地空余和尚头。辫子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光溜溜。”
诗词之外,金岳霖对对联也很感兴趣,他作对联时常把朋友的名字嵌入联中,妙不可言,他甚至会用英文作对联。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在《自传》中称赞过金岳霖的英语“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因此,金岳霖把英语也玩弄于鼓掌之间。
在绘画领域,金岳霖偏爱中国的山水画,他对山水画的布局和意境问题有深刻的理解。不过金岳霖很少收藏画,不像一些人喜欢就要占有,他经常跑到朋友的家里去看画,有时候从报纸上剪下来的画作照片可以让他反复欣赏很多天。
音乐方面,金岳霖是京剧的行家,他家中收藏许多名家的唱片。“文革”期间,红卫兵破“四旧”,把他的唱机抄走了,幸而唱片还留下。听戏已经形成习惯的金岳霖便时常把唱片拿出来把玩,他认为看着唱片,也仿佛听到了声音,大家戏称他爱听“无声的唱片”。“但识琴中趣,何老弦上音”,陶渊明喜欢弹无弦琴,金岳霖已经得到他“魏晋风度”的真传。
金岳霖还是一位美食家,大半生在北京的他对“舌尖上的北京”了如指掌,老北京有什么餐馆,餐馆有什么名菜,菜的特色口味他一清二楚,当时谁要下馆子聚餐有不清楚的问老金准没错。
研究哲学的老金竟然还喜欢看武侠小说,尤其是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不知道对于里面那些侠客们非常不符合逻辑的飞檐走壁、内力轻功,金岳霖有没有自己的想法?金岳霖有一次给同学们讲《小说和哲学》,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讲着讲着,他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说着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个跳蚤,得意地捏在手指里看看。“扪虱而谈”,这又是一种魏晋风度。
金岳霖向来憎恨收礼,但是有三样东西可以例外:年历,湖南菜,大梨。走进金岳霖的房间,往往第一眼被那些大水果吸引。老金喜欢搜集大苹果、大桃子、大桔子之类的大号水果摆放在案头,尤其酷爱大梨。即使晚年腿脚不便,他也要坐上三轮车到市场上把看到的最大的梨买回家。这些水果不是吃的,是用来观察的,除非老金最得意的弟子,很少有人得到他的“赏赐”,有时候老金会拿去和别的教授的孩子比赛,输了,就送给小朋友,再去买。
当然,金岳霖最有名的癖好还是养鸡。
金岳霖头一次养的鸡是从北京庙会上买来的一对黑狼山鸡。在老金的精心呵护下,没多久公鸡已经长到了9斤4两,母鸡也超过了9斤。冬天来了,老金担心它们受冻,看到书上说可以喂点鱼肝油御寒。他就用灌墨水笔的管子灌了它们一管子的鱼肝油。结果,这两只宝贝鸡很快就在窝里寿终正寝了。
后来,老金又养了一只云南斗鸡。这只公鸡能把脖子伸上来,和老金在一个桌子吃饭,老金与鸡平等共餐,安之若素。晋朝的阮咸曾经与猪一起喝酒,这又是老金魏晋风度的一个表现。偶尔,金岳霖会带着大公鸡出去溜达,引来很多路人围观,但鸡不在乎,老金也不在乎。
据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回忆,有一次她接到老金的一个紧急电话,让她赶快进城。杨步伟问什么事,老金支支吾吾,只是让她越快越好。当时老金正跟秦丽琳热恋,杨步伟以为是秦丽琳怀孕了,一路忐忑。到了金家,杨步伟才知道这件事跟秦丽琳无关。
原来,金岳霖养了一只母鸡,最近反常地连续三天不下一个蛋。老金担心鸡难产,赶紧请东京帝国大学医科博士毕业的杨步伟过来看一看。杨步伟听了之后又好气又好笑,把鸡抓来一看,原来老金经常给鸡喂鱼肝油,以至于这只鸡营养过剩,鸡蛋卡在屁股眼出不来。杨步伟伸手一掏,问题马上解决。金岳霖一见,欣喜不已。为表感谢,他特地邀请杨步伟一家去吃烤鸭。
贪玩的金岳霖像小孩子一样率性天真,我行我素,因此,也闹了不少笑话。
有一天,梁思成看到金岳霖的厨师外出采购,手捏一张五千余元的人民币活期存折,大为惊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五千多块可是一笔巨款。梁思成忙问金岳霖缘由,老金答:“这样方便。”梁思成说:“若不慎遗失,岂不是很冤枉?”老金还是说:“这样方便。”梁思成只好跟他建议:“这样吧,存个死期,存个活期,两全其美,而且‘死期利率高于‘活期……”谁知金岳霖连连摆手:“使不得的,本无奉献,那样岂不占了国家便宜?”梁思成无可奈何,只得详细为他解释储蓄规则,金岳霖这才理解了,满脸笑容,对梁思成说:“你真聪明。”
没想到,到了“改存”之日金岳霖又打起了退堂鼓。原来他预备在自己死后留一千元钱给自己的厨师,他想:“如果将剩余的钱都存了死期,万一某日我突然死了,钱不就取不出了?”这下梁思成哭笑不得,只好又将如何把那一千元抽出为厨师另立户头之事细细为他讲演了一番。金岳霖听完之后恍然大悟,喜作一团,竖起大拇指对梁思成说:“你真聪明。”据说,梁思成经常从金岳霖的嘴里得到这样的夸奖。
还有一次,三伏天,几位友人到金家串门,一进门,看见老金愁容满面,连连拱手,说:“这个忙大家一定要帮啊。”友人不知何事,但是念及老金一个独身老头儿实在可怜,便个个拍着胸脯作英雄状慷慨允诺。一会儿,老金的厨师为每个人盛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牛奶……原来,金岳霖冬天爱喝牛奶,订了好多瓶,他不懂得变通,以为订牛奶也要“从一而终”,到了夏天他饮量大减,天热又容易变质,于是出现了以上这一幕。
当时牛奶还是奢侈品,也只有老金这种拿着一级教授工资的单身汉才能经常消费,大家揩老金的油,几天后又来喝了一次牛奶。幸有一位好心人知道后,告诉老金牛奶订量可以自己做主,冬天多订,夏天少订。老金听完后大大的佩服,称赞他:“你真聪明!”
老金虽然像孩子一样天真,胸无城府,但是有些事绝对不是单单“天真”两个字可以衡量的。
林 语 堂
林语堂短暂的执教生涯和他漫长的著述生涯比起来,更像是人生中一段分量不算太重的插曲。因此,林语堂既没有桃李遍天下,也没有几个出类拔萃的高徒来追捧他。但林语堂的高超之处是他即使在这样无足轻重的插曲中仍然能够弹奏出几声天籁,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林语堂足以成为素质教育的代言人。
林语堂曾经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兼了一年的英文课,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林老师第一堂课竟然是教学生们吃花生米。按说这天林语堂带了一个大包到教室,学生们还以为这里面装的都是教学资料,看这架势不禁让人肃然起敬,心想这位拥有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和德国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文凭的老师果然深不可测。
不料,林语堂上了讲台,把包倒过来,往讲台上一倒,只见满满一堆带壳花生稀里哗啦全落在了台上。林语堂抓起一把花生,分给前面的学生,并请诸君自便。大家自打当学生开始,从来没遇到如此荒唐的事情,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敢先动手。林语堂知道同学们的心理,笑道:“吃花生必吃带壳的,一切味道与风趣,全在剥壳。剥壳愈有劲,花生米愈有味道。”他顿了顿,接着说道:“花生米又叫长生果。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诸君长生不老!以后我上课不点名,愿诸君吃了长生果,更有长性子,不要逃学,则幸甚幸甚,三生有幸。”
学生们闻言哄堂大笑。林语堂趁机招呼学生:“请吃!请吃!”课堂里立即响起了一片剥花生壳的声音。等到花生吃完,林语堂随即宣布下课,夹起皮包,一拍屁股头也不回地走了。
此后林语堂讲课,果然没有学生缺课,而且还有很多外来的学生慕名赶来偷师。这一方面是源于林语堂的学问和名气,另一方面是因为在林语堂的课上完全不会感受到拘束和压迫,有时候你甚至忘记了自己在上课。林语堂上课以不正经著称,他从不正襟危坐,喜欢在讲台上逛来逛去,三尺天地他却能闲云野鹤,有时讲着讲着干脆一屁股坐到讲台上。林语堂很少坐在椅子上,讲得兴起的时候偶尔会忍不住将穿着皮鞋的双脚跷到讲台上,他认为这样的姿势很舒服。
更绝的是,林语堂所执教的课程,竟然从不举行考试,每到学期最后一节课的时候,林语堂便端坐在讲台上,随手捡起学生的花名册一一唱名,念到名字的学生依次站起来。这时,林语堂便如相面先生一般,细细把这个学生打量一番,然后在成绩册上记上一个分数,这就是该生本学期的成绩了。林语堂“相面打分”的故事堪称教育界的一大奇闻,并引起了一些老师的模仿。
林语堂这样做的直接原因是他对刻板的考试制度的厌恶,他说:“倘使我只在大学讲堂演讲,一班56个学生,多半见面而不知名,少半连面都认不得,到了学期终叫我出10个考题给他们考,而凭这10个考题,定他们及格不及格,打死我我也不肯。”他还把考试比成大煞风景的“煮鹤”,说:“恶性考试艺术就是煮鹤艺术,可惜被煮的是我们男女青年。”
令人称奇的是,那些被林语堂“相面打分”过的学生接到自己的成绩后个个心服口服,没有一个人上校长那投诉,而且大家公认林语堂相面打下的分数,其公正程度,远超过一般以笔试命题计分的方法。其实,林语堂记忆力超群,他平时在上课的时候,通过提问、交流等方式早已对每一个学生知根知底,他的这种相面打分看似及其随意,实际上是在了解了每一个学生的水平之后作出的合理决断,比起偶然性很大的一次考试反而更显出其公平,也更显出林语堂授课之用心。
林语堂别具一格的教育方式就连自己的三个女儿也深受熏陶,乃至改变了她们的命运。林语堂的二女儿林太乙回忆自己小时候上学很用功,常常一天晚上要花好几个钟头在灯光下做作业,哪个家长看到这样上进的女儿不喜上眉梢,但是林语堂却时常阻止她:“不要做啦,分数不要紧!”
林语堂认为社会是最好的大学,人生是最好的老师,他在教育自己的女儿时总是不遗余力地带她们亲自去体验这个世界。他带领女儿们去著名的维苏威火山探险,林太乙回来后还根据此事写成文章发表。有一次,他甚至带三个未成年的女儿在巴黎的夜场看了场脱衣舞,看到那些一丝不挂的舞者,女儿们个个掩面低头,林语堂却正颜告诉她们:这是最高雅美丽的艺术!
林语堂的三个女儿中只有小女儿上了大学,大女儿林如斯和二女儿林太乙都在父亲的建议下放弃了到大学进一步深造的愿望。林太乙是在美国读的中学,毕业时成绩优秀,完全有机会升入哈佛耶鲁之类的名校就学,但是父亲却告诉她像她这样有志于人文学科的人在家刻苦钻研一本字典学的就可以比大学里学的多,从而劝她打消了上大学的念头。
林语堂反对女儿上大学源于他对大学“极端不自由,极端不负责”的教育制度的厌恶,我不知道是不是林语堂在中国呆久了,把对中国教育的刻板印象带到美国去了,因为自由和负责向来是美国大学的优点,也是中国大学的致命伤。而且就中国的大学而言,至少一半的专业与课程其实是毫无意义的,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
林语堂的两个女儿虽然都没有上大学,但是照样很有出息,大女儿如斯后来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工作,台北故宫馆藏的英文介绍大多出自她手;二女儿太乙是《读者文摘》中文版的创始人,曾任香港《读者文摘》总编辑23年之久,她继承了父亲的衣钵成为了一个作家。更有意思的是,从没上过大学的林太乙居然在赫赫有名的耶鲁大学当了一段时间的老师,教的是中文。
林语堂这样的教育风格和理念早在他的学生时代就现出端倪了。读小学时,林语堂就曾在一次考试前夕窃取了老师的考卷,使得整个班级的同学在这次考试中一致得了高分。这件事让林语堂终身引以为豪,他鄙视那些所谓的优秀学生,认为这些人只不过是老师肚子里的蛔虫。
后来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时,林语堂照样“执迷不悟”。大考之前,同学连晚上都要挑灯夜战,林语堂却一个人跑到苏州河边去钓鱼,以此为乐。不过由于林语堂资质出众,每次大考还是高居第二,他在回忆录中解释自己没有考第一的原因:“我从来没有为考试而填鸭死记。在中学和大学我都是毕业时考第二,因为当时同班有个笨蛋,他对教授所教的各种学科都看得十分正经。”
在圣约翰大学,林语堂还是校讲演队(类似我们现在的辩论队)的主力,并因领导讲演队参加各种比赛屡创佳绩而声名大噪,轰动一方。此外,林语堂在圣约翰还学会了打网球,参加了足球校队,是学校划船队的队长。最出色的是,林语堂还创造了学校一英里赛跑的纪录,并代表学校参加了远东运动会。林语堂感叹自己上对了大学:“倘若说圣约翰大学给我什么好处,那就是给了我健康的肺,我若上公立大学,是不会得到的。”
吴 宓
吴宓对自己要求一丝不苟,对年轻老师也是如此督促。在西南联大时,有一次一位年轻的老师把自己上课的教科书丢了,想先跟吴宓借用一下,没想到遭来吴宓的一顿训斥:“教师怎能丢失教科书呢!一定要找到,上课前必须找到!”晚上宿舍已经熄灯睡觉了,吴宓还跑到那位青年教师的房前敲门,大声问:“教科书找到没有?”那位青年老师怕吴宓大动肝火,只好撒了个谎:“找到了。”吴宓这才放心,告诫他说:“那就好,教师不能丢教科书,下次再不能丢!”
要注意,那个时代是没有什么教参的,老师讲课都要自编讲义,水平优劣很容易判断,不像现在大多老师可以浑水摸鱼、滥竽充数。
在1943年的日记中,吴宓曾痛批西南联大的老师们整天想着挣外快,教书倒成了副业,讲课敷衍、作业不批,甚至连评阅新生考卷都不到场。反过来,吴宓当时已经是赫赫有名的大学者,他就连学生考试的时候,也要亲自陪在一旁,亲手准备糕点、茶水为学生服务。吴宓出的试题不好答,很费时间,有的同学用时太长,误了晚餐,他还会请他们上饭馆。
其实,吴宓未免有点苛责当时的老师了,在那样的战乱时期,老师们那一点薪水根本抵不上通货膨胀,“教授教授,越教越瘦”,陈寅恪这样的大教授都穷得要把自己的皮鞋卖掉,甚至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的夫人都卖起了糕点(这也是西南联大为何成功的原因),因此老师搞点副业还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吴宓的批评用来批判当今的大学老师们,简直十拿九稳,个别不想捞外快的是因为他们没这个本事,只能对别人羡慕嫉妒恨。
当然,吴宓上课不是一成不变地刻板,他也常常有激情燃烧,“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时候。
刘绪贻在西南联大时曾选修过吴宓的《欧洲文学史》,他回忆吴宓:“讲但丁《神曲》时,用手势比划着天堂与地狱,时而拊掌仰首望天,时而低头蹲下。当讲到但丁对贝亚特里切那段恋情时,竟情不自禁地大呼Beatrice!”
还有学生回忆:“雨僧先生讲课时也洋溢着热情,有时眉飞色舞。”在讲述欧美诗歌时,本身就是诗人的吴宓,讲到得意之处,常常拿起自己的手杖,随着诗的节奏,一轻一重地敲着地面。更有学生形容吴宓“上课像划船的奴隶那样卖劲”。
另外,看似严肃的吴宓老师不乏幽默的时刻。
在联大上课时,有一次吴宓在讲授《中西诗比较》课,学生李俊清养的一条大狗径自跑了进来,蹲坐在教室角落里。吴宓看见了,并没有使出打狗棒法,而是走到大狗跟前,很和气地对它说:“目前我尚不能使顽石点头,不是你该来的时候,你还是先出去吧!”说罢手一挥,那条狗竟似听懂了吴宓的话,低着头垂着尾巴悄悄地出去了,同学看到这一幕,不由地哄堂大笑。
1977年,在文革中饱受摧残的吴宓被他的堂妹吴须曼接回老家,在这里他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一年。吴须曼的小女儿在家待业,常来照顾吴宓,吴宓则帮她补习英语。在双方一次闲谈中,吴宓得知学校里还没有开设英语课,因为没有英语老师,他马上说:“为什么不来请我?我还可以讲课……”说这话的时候吴宓已经八十三岁高龄,重病在身,腿有残疾,一只眼睛已盲,另外一只眼睛也几乎看不见。
吴宓一生天真,这种天真也许也可以用钱钟书形容他的“为人诚悫,胸无城府”来概括。吴宓自称“一生不打诳语”,他在日记中喜欢臧否人物,毫不掩饰,缺乏中国学人含蓄蕴藉的共性。令人诧异的是,即使在“文革”这样危险的时期,他也照样“我口写我心”,比如他批评红卫兵运动如“以利刃置诸小儿之手,使之乱割,伤己伤人”。有时候,他还会把和自己一起挨批的一些“牛鬼蛇神”说的一些玩笑式的牢骚话记在日记里,还说明是“某君云”,大概他觉得这些话很好玩,后来害的这些“牛鬼蛇神”遭受更严厉的批斗。
吴宓一生写下几百万字的日记,这些日记记录了他的生命历程,见证了一个时代,也被他看得像生命一样重要。“文革”中,吴宓担心自己的日记被抄走,经过妥善安排,他把日记悄悄地转移到一个值得信任的门生那里。但是到了晚上,他却又忍不住在当天的日记中把自己转移日记以及托付于何人何地一五一十地记录下来。结果,在接下来的抄家中,造反派根据这次日记的记载,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吴宓的全部日记缴获了。吴宓闻知此事,痛不欲生,认为这是自己一生中干的最愚蠢的一件事。由于出言无忌,吴宓的日记被搜走后马上成为他最大的“呈堂证供”,其中很多页都被撕下来用作批判,成为今天无法弥补的损失。
吴宓的个性使他成了骗子最钟爱的对象。他有一块价值几百元的进口手表,被两个无赖忽悠后,换成了一个仅值六元钱的小闹钟。在西南师院时,有一次一个张姓同事告诉吴宓他的学生某某患了重病,需二百元住院费,希望吴老师先救一下急。吴宓拿出钱后,过几天这位同事又来了,说是这个学生需要开刀治疗,还差手术费若干。为了证实自己的话,这个人还带来了学生的求援信,当场念给吴宓听。这个时候恰好吴宓的佣人进来,看到此人念的是一张白纸,惊讶不已,忙密告隔壁房间刘尊一教授的女儿,让她唤来治保主任等人,将这个骗子扭送至学院保卫科。事后,吴宓对这个女佣人的精明赞不绝口。
1976年底,吴宓的堂妹吴须曼将生活不能自理的吴宓接回老家时,发现他所有财产只剩下枕头下的七分硬币。吴宓的工资并不低,只是都被人家骗走了,他被抄走的书被人家忽悠着用自己的工资再买回来。更可耻的是,吴宓身边有一伙人不断地编造各种理由从他那里骗取钱财,吴宓每个月的工资除了资助学生和亲友外,几乎全被这些小人骗走了,自己只剩下一点可怜的生活费。这些欺骗吴宓的行为有些被人发现,劝他揭发,他却说:“我承诺为人家保密,若揭发就是不守信,而不守信非仁者所为也。”
在骗吴宓的小人当中,有的就是吴宓自己的学生,这些当年欺骗、侮辱吴宓的人当中,据说有的目前正在大学以研究和吹捧吴宓为生。
按照学生季羡林的话来讲,吴宓是个“矛盾的人物”。吴宓的矛盾之处很多,有一点很有趣,他懂得多国语言,却坚持用文言文,他几十年来写文章都是直行书写,只写繁体字。“文革”时有人诬陷吴宓攻击领导的“屁股”云云,吴宓气愤地说自己一生只用文言文而反对白话文,涉及这一部位时,他一定会用“臀”,而绝不用“屁股”。
(选自《民国课堂:大先生也挺逗》/潘剑冰 著/广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