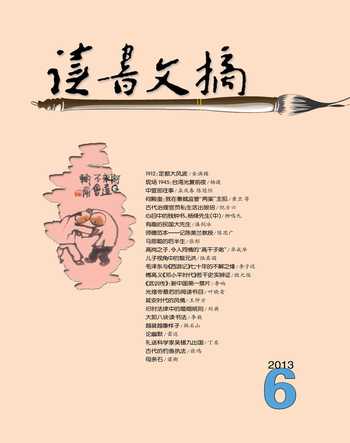心目中的钱钟书、杨绛先生(中)
在实际生活里,钱、杨很低调平实,他们除了在衣着上比较讲究外,在其他方面,不论是待人接物、人情交往,还是作派作风以至生活情调都力求低态亲和、平凡普通。这种低调,实际上就是有意冲淡自己作为高级学者甚至是作为学术泰斗而与身俱有的特质与标志。他们从不摆出身份架子,更没有半点作态,给人平易近人之感,不像有些名士那样身上总发散一种威严、一股冷气,使人难以接近。在我见到的大家名流中,他们要算是最为平实,甚至最为谦逊的两个。
如果你在门口迎面碰见钱钟书,他决不会因为你的辈份比他低、年龄比他小而气昂昂地当仁不让,倒会让在一旁让你先走,就像他与比自己年轻许多的中青年人有信札来往时,往往尊称对方为“××吾兄”,信札后尾往往署上“钱钟书上”,甚至是“敬上”的字样。即使在门口相遇他让不过你而先跨一步,脸上也会带着他那特定的、嘴角朝上、有点幽默意味的微笑,似乎在向你表示歉意。
如果你是初次认识杨季康,你也会很容易发现她待人接物的态度十分平实谦逊,她虽然有时穿得有点雍容华贵,但神情态度却平和得就像邻里的一个年长的阿姨或大嫂。她不会像某些女才人那样,一相识,一见面就言必谈学术与文化,似乎不那样就不显自己的身份与高雅,她倒是总爱聊聊家常,说说普通平凡的题目,显然,她在日常生活中,只想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与人进行交往,进行普普通通的交往。认识久了,她对晚辈后生则愈来愈有更多的亲切关怀,的的确确像一个慈祥的“阿姨”。
如果你到钱、杨家去,你会发现主人显然是力戒任何排场与气派。他们家的陈设家具可谓简单朴实之极,既无宋式或明清风格的桌椅,也没有款式新颖的西式沙发,没有古色古香、洋洋大观、包括诸子百家的书柜,没有气概不凡的文案。总之,名士方家书房里常有、甚至不可或缺的陈设,在他们这里几乎一样都没有。
他们家住在东四大院的小灰楼上时,我去过多次,客厅里只有再简单不过的几把坐椅。他们从干校回来后在文学所楼的西头居住时,我也常去,房子里更拥满了应付最简单饮食起居需要的日常生活用具,连一个像样的书架也没有。那时,院子里正荒置着一些图书馆的高大铁书架,日晒雨淋,已成废品,钱、杨从管行政事务的头头老姜那里,借来几块铁板,用砖头叠起来支在两头,铁板往上一搁就成为书架了。直到他家搬到三里河国务院高级宿舍楼后,这种特殊的书架在他们家还继续使用了相当长一个时期,到了后来很久,才见添置了一两个简朴的书架,但却矮小不如人高,容积很有限,似乎在宣称,我们没有多大学问,用不着放置多少书籍……所有这一切,与名学者教授家书架林立,琳琅满柜的景象,恰成鲜明的对照……
但只要一进入谈话,你面前就出现了蔚为壮观、令人目不暇接的知识大炫耀,红白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当然是钱钟书。只要有一个话头,有时话头是你引出的,有时干脆就是钱钟书本人提起的,只要话头一出,他就滔滔不绝了,几乎每句话都是一条知识,都包含一条典故,而且英文、法文,意大利文,以及汉语古文的语汇或语句,不时纷呈闪现……至于议论评述,则是上下古今,天马行空,文章世事,不免指点挥斥,甚至忘乎所以,口无遮拦的状态,亦不时有之。于是,在你面前就出现了一个学识上的“高人”,心气踞傲的智者,日常的低调平实终难压下超人的高个头,“种菜园子”的作派终难掩盖“心高气傲”的本色。
正如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看到的,靠身外之物不论是车马房舍,还是字画、条幅、书柜之类装点自己者有之,靠头衔冠盖炫耀自己者有之,靠故作重要之态、摆出威严架式,甚至是加大嗓门音调来抬高自己者亦有之,靠意气用事、称谓用词来计较高下、争强斗胜者亦有之,这种种世态背后,无一不是发虚的内心与贫乏的精神境界。钱、杨作为学富五车、意境高远的智者,显然瞧不起这类作态,他们不仅恶之、远之,而且有意逆反,不时有意“矮化”自己、“平凡化”自己,形成自己一种行事的作派与风格。我不知道钱、杨自己是否自觉地自我欣赏这种风格,但至少我自己对此是很赞赏的,而且,我猜想,透过日常那些平凡、矮化的外表,不时凸显出自我的高大与超人,这也不失为自我的一种乐趣与享受,在反差之中,这种乐趣与享受当更为令自我愉悦。
虽然他们在与你作谈话时,其学识是绝对地、显著上占有巨大优势,他们是站在明显的高处,甚至可以说有时就是站在云端,但他们特别避免有一种“居高临下”之态,避免有俯首而视之嫌,完全不像有的专家学者即使站在比你只高半寸的小小门槛上,也要摆出俯身示教的架势。钱、杨相反,不时总会显露出一种非常明显的意识:尽可能地冲淡与弱化他们自我,尽可能矮化自己的高度,拉近与你的距离。面对钱氏那种知识大裂变、知识大炫耀,你很可能有眩晕之感,有难以适应、难以跟得上的尴尬(至少我自己就经常如此),更不用说能够应对应和了,但你大可放心,你不会在难堪的低谷里难以脱身,钱、杨自会援你一手。杨季康常常会在一段段学术内容稔稠的谈话中,不时插进一两句家常内容或轻松内容的话,来有意地进行冲淡,进行稀释,使你如在学术知识洪流的冲击下,不时能碰上一片小洲、一块礁石,得以缓上一口气,小事休憩休憩。至于钱氏,他会有意识地照顾你的进度,让你跟得上他天马行空式的学术神侃,如果他引证了一句你所不懂的某种语句,他就会翻译成中文教你能懂,如果他引证了一句意大利文或德文,而你如果学过法文,他一定会用法文再表述一遍,似乎在说:“老弟,咱俩有共同语言。”有时他说得兴起,便把头微微一低,眼睛微微一眯,手轻轻一摆;有时,还用手在你的肩头上轻轻拍两下,或者轻轻一推,要不然就是把手在你臂上搁一下,似乎要用手的动作来加强你对他话语的记忆。这哪里像是宗师在讲学布道,哪里有半点“师道尊严”,而完全像是跟一个哥们儿小兄弟在聊闲天。甚至我常觉得,他似乎对“师道尊严”是毫不珍惜、不屑一顾的,他相信以自己知识的力量,就足以使对方五体投地了,何必求助高人一头的架势、威严与颜色?更用不着靠“师道尊严”之类的强制性的法规守则了。
我常想,钱、杨是生活在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之所以采取“种菜园子”的低调低姿态,有意识地自觉地拉近自己与芸芸众生的距离,甚至有时凡俗化自己,是因为他们性格上天然就有谦恭自卑的倾向?是因为他们在精神人格上有一种对谦虚美德的向往与追求?而其向往追求的程度又是那么强烈热切得不可抑止,以至形成了作风作派上的一种惯性,固化成了一种风格?实际上,他们都是心高气傲的智者(这么说恐怕没有冤枉他们),他们上述风格风度看来并非秉性使然,至于是否与精神人格上的追求有关系以及有多少关系,我一时也说不清楚,但有一点我很清楚,那就是既然他们是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以他们的高智商,当对这个时代有深刻透彻的认知与理解,杨季康甚至用了一整本书《洗澡》,描写过这个时代的尖锐时段与尖锐问题,因此他们采取何种存在姿态、存在色调,当然与时代社会有绝大的关系。
这个时代是“平均地权”的时代,是“打土豪、分田地”的时代,是大刮共产风的时代,是吃大锅饭的时代。在财产领域、在政治、法权领域,这一次次风潮、一股股急流又势必冲击、涌入、渗透进思想文化领域,并决定着这里的“财产再分配”。对于这一切,钱、杨都目睹亲闻,有切身感受,在一个“平均主义”盛行、并不断以平均主义的原则进行激烈“再分配”的社会里,什么色调、什么姿态比较安全?那便是平民色调,那便是平头百姓的低姿态。君不见在历史上,平民主义至上的法国大革命中,贵族都力图掩盖自己身上的印记?高贵者总力图沾上“泥腿汉子”的气息?钱、杨博古通今,具有极高的悟性,当然知道在现实生活和人与人的关系中,应该采取何种待人行事的方式,应该形成自己的何种风格。
七
这里我不禁想起与钱、杨唯一一次“共事”的经历,在我心目中,这件事既充分展示了钱、杨行事的作派,似乎也反映出他们的某种深层意识。
大概是在1964年,中宣部因文学理论批评界长期存在着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争论,便交给当时的文学研究所一个任务:编选出自古以来的外国理论批评家论“形象思维”的系统资料,以正本溯源。于是,文学研究所奉命成立了两个编译资料组,一个负责编译西欧古典理论批评家和作家论形象思维的资料;另一个负责编译俄国革命民主义批评家与苏联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有关论述的资料。前一个小组以钱钟书、杨绛为主,配备了两个年轻的助手,我与刘若端。另一个小组则由几个从事俄苏文学研究的学者组成,以后来担任了外国文学所所长的叶水夫为首。
任命钱钟书为西欧这一摊子的负责人,既是对他的重视,也是给他出了一个难题。说重视,是因为西欧这一摊子要涉及古希腊文、拉丁文、英、德、法、意大利、西班牙多种外语,国内恐怕只有钱氏才能担此任。说难题,是因为“形象思维”这个术语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苏联理论批评家根据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的“创意”而创制定型的。要到古希腊、罗马以及西欧的理论著作中找这个术语,就无异于要到海洋上去狩猎老虎,难题完全是中国理论界领导人主观上以为这个“苏式术语”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概念而造成的。
但难题并没有难倒钱钟书与杨季康,他们实事求是地解决了难题,最后编选翻译出了一份完整的理论资料,明确说明“形象思维”这一术语并不存在于西欧古典文艺理论之中,不过其中倒的确有一个与之相近的“同胞兄弟”,那便是“想像”。钱、杨所编译的这份资料实际上便是一份系统而完整的关于“想像”的理论资料。
作为一个青年研究人员,我当时能参加钱、杨的这个小组,要算是一种荣幸。就我的学力来说,选题的事我是插不上手的,我只是按领导的要求,当了当助手,跑了跑腿,没有什么事可干,不外是借借书而已。刘若端的情形也是如此。钱、杨怕年轻人坐在冷板凳上难受,便把法国16世纪作家伏佛纳尔克的一则论述交给我翻译,短短的仅五六百字而已,我译好后交卷,杨绛又作了校对修改,虽没有什么理解上的出入,但她把译文改得更精练更利索了。最后,这几份理论资料都在《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11册发表了,钱、杨的这一份共节选节译了32个理论家与作家的片断论述,篇幅不大,只有三四万字,但署上了“钱、杨、柳、刘”四个人的名字。我因为自己只是一个助手,出力很少,不止一次请求不要署我的名字,对此,钱、杨执意不听,一定要把四人都一并署上。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这个小摊子是由领导上共指派了四个人,所以,钱、杨坚持署名“一个不能少”,似乎是在坚持一个“集体主义原则问题”;另一方面当然也有提携两个青年研究人员的好意。但对这样一个结果,我心里老感到不是滋味,就像不得已蹭吃了一次“大锅饭”,也像在一次“知识共产风”中成为了一个“占了便宜”的人。那时,我虽然在学术资历上还没有修炼成什么气候,但还没有“一穷二白”到要靠蹭大锅饭为生的地步。不过,编选理论资料的其他两个摊子也存在“吃大锅饭”的问题,而且当领导的人自己就跟着蹭饭吃,社会风气如此,钱、杨不过是按不成文的法则办理而已,做小辈的不必太较真,恭敬不如从命就是了,随大流就是了。
事隔多年,钱大师去世之后,一家出版社要将上述那份理论资料收入钱、杨的集子,问我当时的情形,我如实作了说明,强调那份“理论资料”是钱、杨的心血与成果,两个助手在其中的工作量微乎其微,应该把这两个名字删掉。终于这家出版社听取了我的意见,扔掉了两个“小累赘”,不过,在删去了这两个小人物的名字的同时,伏佛纳尔克那一则译文也被删去了。其实,这倒没有必要,因为伏佛纳尔克并非文学史上一个特别显著的大家,要把他这一则论述摘选出来,只有钱钟书先生的学力才能做到,他为此肯定付出了辛劳,而且,那一则译文毕竟还是经过了杨先生的校改,应该算是他们的成果。季康先生真可以说是一位完美主义者,她力求绝对的纯净与利索,要真正做到“一尘不染”!
八
早从50年代起,钱、杨的生活中就出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那就是钱钟书参加了《毛选》的英文翻译定稿工作。时间持续很久,直到《毛选》五卷的英译本完成出版,前后共有二三十年之久,这么长的时间,当然就会对钱、杨的生活有所影响与作用。因此,与其说是一个方面,不如说是一个行程,一个进程。
首先,就其性质而言,就很不一般,甚至“非同小可”,这可不是小组长、小队长一级的领导人派你去多值一个夜班、多烧一炉开水,而是与中央领导直接有关的机构调你去参加一项无疑要算全国全党最最重要的任务。这一“上调”固然是因为钱钟书精湛的外文水平令高层领导不能不格外重视与重用,但无疑也相当大地提高了钱钟书作为技术专家的业务地位,使得他在同辈人文学者中更为突显,甚至头上有了一轮小小的业务光圈。说实话,这是他的《谈艺录》与《宋词选》所不能做到的,至少在现实的意义上是如此,这是此事对钱钟书的第一层含义。
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是,此事具有明显而光荣的政治意义。不论钱、杨主观上是否有不问政治、甚至有意疏远政治、清高超脱的倾向,但这件事却使得他们实际上进入了比较高层的政治领域。语言业务上对钱钟书的重用,首先就表明了政治上的信任,而他在这个工作岗位上的长期任职,而且在定稿工作中愈来愈重要的地位,也证明了他尽心尽职,为政治服务的良好的态度,以及他这种服务的优质优量,这就使得他完全成为了共和国真正的一级专家,成为党与政府所重视的“国宝”。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有这一些都未能使得钱、杨不被揪斗,不被侮损,但毕竟“情有可原”,最高司令部里正在搞“路线斗争”的大比武,斗得情急眼红,连编修圣书此种要事,也顾不上了,况且“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当然要打破一些“瓶瓶罐罐”,甚至包括“元青花大罐”一类国宝级的“极品”。只有双方的斗争有了某种“阶段性成果”,才会有想起保护国宝的事情。当然,最后尘埃落定之日,是“大乱”之后的“大治”之时,编修圣书的要事重续,钱钟书又得到了重用。这样一个过程虽然起伏跌宕、颇有周折,但最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毕竟水到渠成,导致了钱、杨在官方体制中地位的大幅度提升与确认,其具体表现则是在生活待遇上搬进了国务院高级宿舍的小楼,在名位上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能获此种待遇,在与他同辈的学者、专家中,特别是在人文学者之中,是绝无仅有的一例,这更确立了钱、杨在全国人文知识分子、学者中首屈一指的尊贵地位。
我再说一遍,这一切是一个进程,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客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钱、杨是“受格”,除了他以自己的语言技能、语言修养,尽心尽职地将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外,我们看不到他还做出过其他的努力,更不用说其他的经略与钻营了。他们仍然保持自己清高与超脱的姿态,不谈政治、不做政治性的表演。作为一个与钱、杨还有过一些接触与来往的晚辈,我在就近观察之中发现,他们对自己所处的这样一个客观的实际过程,始终保持着低姿态、低调门,从不提及某些可以炫耀自己重要性与荣誉性的“事实”、“细节”,某些可以抬高自己的人事与关系,甚至对参加《毛选》工作一事总是避而不谈。但学界不少人一遇到某种“官方荣誉”,哪怕只是受邀参加一次高级座谈会,甚至只是得到了人民大会堂联欢会一张入场券,却也难免喜形于色,辗转相告,津津乐道,相比之下,钱、杨的确要算清高了。我想,如果说“大隐隐于市”的话,那么,钱、杨就不仅是“隐于市”了,简直就是“隐于庙堂”,“隐于朝”,其“隐”之大,亦当首屈一指。这是精神人格上的真正的“隐”,由此,可见钱、杨作为知识分子学者的人格意境与魅力。
九
在文化大浩劫中,我们与钱、杨一别就是十年。浩劫伊始,一纸“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号令就把“走资派”、“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以及一切“地富反坏右”统统扫进了“牛棚”,而把“广大的革命群众”留在空旷的场地上,什么正经事也不让做,要他们专门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今天以这样的“最高指示”要求你投入“革命大批判”,明天以那样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命令,指引你去“文攻”、“武卫”,更绝的是,不仅有“无产阶级司令部”与“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划分,而且还有“革命派”与“保皇派”两顶截然不同的帽子。于是,在“牛棚”外的“革命群众”,就为了确认自己作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信众的身份,为了抢夺“革命派”的帽子,而争得不可开交,大打派战,一场荒诞的全民性的战争由此打响并一发不可收拾,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
在光焰万丈的红太阳足以穿透身心的射线的笼罩下,大伙却像着了魔似地忙碌,这是狂热的忙碌,荒诞的忙碌,虚掷生命的忙碌,互相敌对、互相伤害的忙碌……“牛棚”里的人忙于写认罪、忏悔书,交待材料、“揭发材料”,忙于一次次充当祭品被押上各种各样的批斗会、誓师会、庆功会、革命大串连会、革命大联合会。“牛棚”外的人则忙于“革命大串连”、到处闲逛、观摩大字报、观测风向、打听动态、写大字报、贴大字报与对立派辩论、口角,甚至动手……
尽管都是在同一个红太阳的照射下,但人们都被分割在一个个互不相通的间隔里。“牛棚”里与“牛棚”外是两个“性质不同”的世界,鸡犬相闻而互不往来。“牛棚”外是一个个对立的兵团、战斗队,乃至一条条楚河汉界与各种名目的“革命委员会”,互相戒备、互相攻讦、互相怒目而视,互相扔西红柿、扔臭鸡蛋、扔石子……偌大一个“翰林院”里,充满了狂热的政治、誓不两立的立场、慷慨激昂的笔战、知识分子文化人生平第一次玩弄的政治谋略与手段以及与之相关的种种不入流、不堪入目的小动作。花拳绣腿,应有尽有,惟独斯文尽失,斯文扫地。大家都把文化与学术抛在了脑后,甚至完全清除出脑海,一个个原来有志于学问之道的学人,都彻底告别了这个行当的任何习气,都铁了心要去当“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职业政治家、革命家与斗士。举例来说,我们那个研究所就有一位从前苏联留学归来的饱学之士,竟把自己全部的外文书、业务书共好几大车都当作“废纸”处理给了收购站,而每天全身心地写路线斗争的大字报,大有要成为职业革命家之势……
一开始的那几年,我着着实实是在浑浑噩噩地过日子。组织上多年的训导与熏陶,在我身上也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左倾幼稚病”,在一开始那种狂热的时空氛围里,也不免头脑发热、激昂慷慨了几天,但很快就有了自知之明:自己既非红五类出身,又非“革命小将”,而且还在“修正主义学术路线”与“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大染缸里泡过几年,显然不属于“革命主力军”的行列,不时要被人侧目而视,况且还被革命左派当作“修正主义苗子”扫过几笔。因此,自认没有资格去“力争革命上游”,只求自己“既跟得上革命形势”,又做到“明哲保身”,因此,在浑浑噩噩之中,也带几分战战兢兢。每天的“必修功课”是研读中央大报的社论,关注各种小报上有关“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消息与报道,调整自己的表态与言行,以求自己不脱离“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轨道”,还有,与革命主力军、革命左派处好关系,等等。生活内容不外是在机关大院里“观摩大字报”与同派人士交头接耳、议论评析,或打听种种小道消息作为自己行为的准绳,捉摸自己该站“什么队”,该参加哪一派……回到家里,则清壁坚野,根据革命形势的逐步深入,一茬茬把过去的文稿与记事烧得一干二净,谁知道自己哪天会享受被抄家的待遇?如果说,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自己心目中还有文化目标、学术目标,还有业务上的打算与意向,那么,到了这个时期,那种狂热而劲猛的政治风暴就把所有那一切都一扫而光了。完全看不见将来还有什么学术文化道路,更无从设想自己在这条道路上会找到什么位置。生存的状态变了,存在的精神支点坍陷了,于是,原来关心的事物,感兴趣的东西,敬畏尊崇的对象,全都变了,原来闪光的东西与带光圈的人物也都在脑海中、心目中黯然消退。这个时期,我很少想起钱、杨以及他们同辈的学术文化精英,只觉得他们所呆的“牛棚”,是一个与自己完全不同的世界,也是自己绝对不愿意靠近的世界,不愿意与之发生任何关系的世界。
在人人自危,但求自保的利己主义的麻木的自我状态中,我有两次惊异于所听到的两则关于钱、杨的传闻消息。消息都是从大院里、“办公室”里、三五“扎堆”的时候听说的。一次在暴风骤雨来到之初,听说钱、杨在自己的居住区被“革命造反派”揪了出来(作者注:以下所叙系根据当时我个人的观感见闻、即时感受,难免与实际情况不尽贴切,有所出入,好在杨绛先生已撰有《丙午丁未纪事》,其中她在“风狂雨骤”时期的不幸经历,当以她本人的记叙为准),至于是哪个单位的造反派干的,当时我没有搞清楚。反正那时的“翰林院”是全国著名的重点“黑线单位”,“牛鬼蛇神”多,任何单位、任何地方的造反派为了显示自己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造反精神,往往都要到院里来借用几个“祭品”,何况还有院内的各单位“革委会”的左派也十分重视这一份“祭品资源”。不管是谁的“革命行为”,反正钱、杨被揪了出来,被挂了牌子,被押上了批斗会,事情便发生在批斗会上,听说杨季康对造反派的推推搡搡公然进行了反抗,而且怒目而视。这还了得,敢与革命造反派对着干!那么多党内老资格的革命干部在批斗会上,哪个不是服服帖帖?你杨季康真是吃了豹子胆,竟敢老虎头上动土,于是盛怒之下的造反派对她狠加惩罚,给她剃了个阴阳头。我当时听说这件事,第一次惊奇地感到杨季康性格中的刚烈与凛然勇气,我所认识的一个娇小文弱的小老太杨季康在那种被任意宰割情况下的刚烈与勇气,要知道,“牛棚”里有不少从火线上转业过来的老战士,没有一个有此种惊人之举。与此同时,我第一次感到了这场风暴的残酷无情,对杨季康这样一个文弱的高级女学者,竟然采取如此镇压如此凌辱的手段,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倒的确可谓“史无前例”,只可惜在当时浑噩麻木的精神状态中,我没有拍案而起的义愤,至今想来甚感惭愧。
第二件事也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阶段。一天,大院里传来一个消息,说有某人贴了一张大字报揭发钱钟书有“攻击伟大领袖”的言论,这个消息真如“石破天惊”,非同小可。要知道,在那个时期,任何“路线错误”、“封资修罪行”与“现行反革命罪行”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而在“现行反革命罪行”中,最为严重、最为“万恶不赦”者,就要算对“红太阳”不敬了。我当时既没有去观摩这张“革命大字报”,也没有找钱氏所在单位的熟人去核实消息是否属实,说实话,我很不愿钱、杨跟这么一桩事有牵连。为此,自己在对确认事实真相这一点上,就有意识地保持一种“距离”,以求达到“间隔”的效应,甚至干脆来一个不承认主义,认定贴大字报的人是在哗众取宠,谋取政治本钱,要不然就是落井下石,居心不良。果然一两天后,大院里又传来一个消息,说钱钟书出面写了一张小字报贴在那张制造了轰动效果的大字报的旁边,对揭发内容正式予以了否认,加以澄清。还有消息说,有人亲眼看见钱、杨是在晚上大院里没有人的时候,出来把小字报贴上去的,杨季康打着手电筒,钱钟书往墙上贴,情景甚为动人。由于我对钱、杨一贯的敬仰与好感,他们挺身而出,据实力争的勇敢行为,很引起了我的钦佩,也很引起我绝大的同情甚至怜悯。在和平时代的“铁马金戈”时期,在这你撕我咬的“丛林”境地里,一对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年夫妇竟要亲自出来抵挡扔来的巨石、射来的暗箭,我想,怎么会有这么心狠手辣的人要将一对老年夫妇往死里整?!当时,我的不承认主义使我根本没有去打听那张“革命大字报”揭发的具体内容,因此,我一直也没有搞清钱氏对“红太阳如何不敬”。
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后期,我与“季康先生”又打了一点交道。那时,大院里的三个派别经长时期的拉锯战,总算达到了某种平衡,虽互相对峙,但派战相对平静多了。在我们研究所这个小单位里,有那么一二十个人,从运动之初以来,基本上走的是中间路线,既不过激,也不“保皇”,每做一件事、每表一次态都小心翼翼要在“最高指示”、“两报一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召”中找依据,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期,总算混出了一点名堂,成了一个有二十多个成员的“兵团”。“兵团”选出了一个由五六个人组成的“核心领导小组”,我是其中的第五把手,负责宣传与学术批判。在任期之内,我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别人、对不起自己的事,但也乏善可陈。惟有一件事倒值得一提,那就是宣布本所“牛棚”中的人一律“解放”。一个群众组织,既不掌权,又无实力,作此宣布,只不过是句空话,仅有的一点实际措施,便是废除了以往两届已垮台的革委会的规矩,不让“牛棚族”去打扫大院、打扫厕所,而让他们回办公室去自行学习(那个时代普天下的规矩是,学习的内容只包括《毛选》四卷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文件以及《人民日报》社论,甚至马克斯、恩格斯选集也没有被列入的荣幸)。我们这一派当时之所以采取这个措施,一方面是为了标榜自己是讲政策、讲人道的;另一方面则是有意引对立派出来表示反对,做出失人心的事来。可是对立派也不傻,竟然不闻不问,予以默认。于是,我们这个研究所的“牛棚族”从此在事实上就免去了劳役,其中就有杨季康,当然还有卞之琳、罗大冈,后来还有李健吾、冯至。这件事是由我推动的,也是我出面办的,自然免不了要跟“季康先生”打个照面,但打了一个照面后,我就避免再打照面了。因为我很害怕别人见了我把我当作“长官”,碰到这种情况,我非常别扭,心里也很难受,特别是面对过去的师长,那时我真想大喊一声:“我不是那样的人。”
在“翰林院”,“文化大革命”最后阶段的压轴大戏是军宣队进驻后发动与主持的“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在这出大戏中,我和我那些一贯恪守折衷主义立场与中间路线的同伙同伴们倒了大霉。我既然在一个二十多个人的群众组织中排位第五,当然就成为了“重点对象”,我的儿子刚出生三个月,我就被圈进了“特别学习班”。那是一个只有十来平方米的小房间,我不得踏出房间一步,每时每刻都有两个专人看管,即使是上厕所的时候。房间里墙上挂着伟大领袖的画像,每天在这画像前,好几个专案组小成员长时间地“革命大批判”与“苦口婆心”并用,勒令我交待一个超出了自己的理解力与想象力的“反革命政变大案”。当然这几位高超的政治工作者是以墙上那个画像名义进行施压与劝诫的……我当时最害怕的就是精神失常、脑子出问题。
我在“特别学习班”一圈就是三个多月,被释放出来后回到家里,见小小的儿子已能满床爬来爬去,不禁哑声而泣。面对着他,想到这个家庭的将来,只觉得一片黑暗,不堪设想,一场“文化大革命”下来,我们这批人的“罪行”大大地后来居上了,我们身上的“政治包袱”已经远远比一切革命对象,当然也比钱、杨老一辈“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要沉重了许多。我又开始羡慕起他们了,而千万没有想到,钱、杨的家里,也遭到了同样的伤痛与不幸。大概在我被圈在“学习班”的那个时期,他们在北师大工作的女婿王德一就是死于当时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好像也是在一个“学习班”里。不过,我当时没有任何察觉,季康先生在生活中是那样遇事不惊、不动声色,我是好几年后才知道他们家这一不幸事件的。那时,“翰林院”里好几百“五一六”总算被平了反,那个骇人听闻的“五一六反革命政变阴谋”实在因为太荒诞太离谱,总算被当作“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想像故事被一笔勾销了,我也庆幸自己活到了清白的一天,而没有像王德一那样想不开而过早离开了人世。(下期续完)
(选自《翰林院内外》/柳鸣九 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