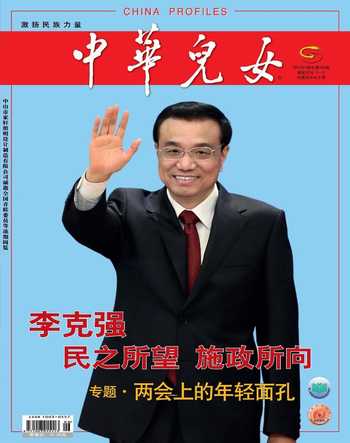张北川 一个怀有理想主义的坚守者
张小华


“这些年来,我从未沮丧过,我之所以做了许多人没做到的事,不过是有一点坚持科学的勇气而已”
“我的心理素质很好。”张北川说。
的确,自从1989年研究“同性恋现象和人群”的那一刻起,他经历了太多的坎坷与波折,作为国内首位在男同性恋人群中进行大规模艾滋病干预的专家、马丁奖得主,他的心理素质不得不好。
“在科学的入口处如同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这里必须丢掉一切疑惧,这里必须清除一切畏怯!”这是马克思说过的一段话,后两句是马克思引用但丁《神曲》中的诗句,张北川甚是喜欢。他说:“这些年来,我从未沮丧过,我之所以做了许多人没做到的事,不过是有一点坚持科学的勇气而已。”
然而2013年,他有些不“淡定”,原因只有一个,全球基金在去年年底已经暂停对中国艾滋病项目的援助。张北川说:“在反对性向歧视和争取同性爱者平等权益的长路上,社区组织是一支主力军。但是‘断粮了,许多社区组织在筹款能力等方面明显准备不足,在新形势、新环境下,缺少应对之策和艰苦奋斗精神。他们未来的路任重而道远。”
“艾滋病,让我们感觉到真正的伤筋动骨”
“艾滋病使我们发现了文化的缺陷,因为艾滋病,我们才感觉到什么是真正的伤筋动骨。我们离现代国家还很遥远。人们把同性恋者看成忌讳,但又有多少人知道自己生活在艾滋病高危环境中?又有多少人科学地正视这个问题?又有多少媒体传播这个声音?”很多次,张北川发问,他用出离愤怒的声音提醒我们,在同性恋问题上,我们没有实事求是!
“作为皮肤病学专家的你为什么要涉足被很多人视作‘禁区的同性恋研究?”记者问道。
“我研究艾滋病易感人群,是在我看到一个人的遭遇后开始的。我的医学启蒙老师秦士德教授,他是我所在医学院里公认的最博学的医生之一,曾两次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他是中国知识界敢于公开自己同性恋倾向的第一人,是我所见过的最富有献身精神、最富有同情心的医生。因为公开了身份,老师的压力很大,面对蒙受羞辱的老师,我站出来想为老师辩护,可我发现自己对同性恋讲不出很实在的道理。我知道,要化解老师遭遇的难处,只有依靠科学。”
就这样,因为老师一个人的遭遇,张北川开始关注起这一群人,而这一关注,就关注到了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同性恋,包容他们,正视他们,张北川开始潜心编写相关书籍。1990年,他开始着手写作我国第一部有关同性恋现象研究的理论学术著作《同性爱》。在这期间,他办公室的墙壁上始终贴着这样一张字条:一般谈话不得超过15分钟。
他关起门来,阅读了200多部性学及相关学科的著作,1000多篇英文文献。
1994年,张北川所著的47万字的《同性爱》终于问世。这部日后被认为是“奠定中国研究同性恋现象的学术理论基础”的专著,通过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分析,阐释了人类史的发展是朝着同性爱者与异性爱者拥有平等权利的方向进步。
“不过,当年出版社采取了低调的冷发行方式,没有做任何宣传,只印了5000册,卖了7年,还余下1000多本。”然而,到了2001年4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出版后(不再把同性恋认定为性变态或心理变态),同性恋现象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短短几个月内,《同性爱》剩余的那1000多本被一扫而空。
在这个“敏感”而又“谨慎”的人群中,《同性爱》被小心翼翼地流传着,原以为自己是“异类”的他们知道,有一个叫张北川的医生理解他们,懂他们。
“像我们这样的人,生在这个世界上,就打上了不幸的烙印,注定了我们的一生是灰暗的。我努力过,追求过,但最后找到的竟是离开这个世界的绝路……”这是同性恋者写给张北川的绝笔信。
“《同性爱》出版后,我接到无数个充满了彷徨、无奈、绝望的求助信和求助电话。这些遭遇让我感到自己肩负的是一个沉甸甸的社会课题。”张北川说。
那些日子里,回信、接听热线咨询电话成了张北川生活的重要内容。他不厌其烦地向这些同性恋者介绍科学的性知识,倾听他们不为人知的心理痛苦,劝慰他们好好工作和生活。
2003年的一天,张北川的电话响了,那头传来的是一个年轻人的声音,“张老师,虽然我只是一名高三学生,学习成绩很好,但人生已经没有希望了,我是同性恋,不久前在一次献血中,我被查出艾滋检测呈阳性!艾滋项目不能通过,就意味着我不能参加军校的招生考试了。我突然觉得整个世界都不再属于我了。”小陆的声音很绝望。
这对于一个从小就梦想成为军人的孩子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一个负责抽血的工作人员的做法更是让小陆心寒,他要求小陆用800元钱来换取检验报告。这对于一个月收入只有七八百元的家庭来说绝对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出于歉疚,为了不连累家人,小陆一度生出自杀的念头。
在与小陆进行了多次沟通后,张北川才逐渐了解到,小陆是同时与几位男同性恋者发生不洁性行为之后,被感染上的艾滋病毒。为了帮助小陆走出心理低谷,张北川查阅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当时他的家人担心那位工作人员因为被处理而报复小陆,公开小陆感染的真相,而不敢索取检测报告。”张北川坚定地告诉小陆的家人:“我国已经有关于艾滋防治的条例,有相关的法规,任意泄露感染者的隐私是要受到制裁的。”
那段日子,张北川和小陆通过40多封信和无数次电话。在张北川一次次信心疏导和支持下,小陆和家人树立了正确对待同性恋和艾滋病的观念。第二年,小陆以560分的优异成绩考上了国家一所重点院校的本科。
直到今天,在张北川看来,有几类人的电话,他是不能回避的:一个是阳性者,一个是未成年人,一个是他们的家人,一个是心理很特殊有自杀倾向的人,还有“同妻群体”。用他的话说,“如果我都回避,还有谁接招呢?”
“艾滋病是一种被污名化的疾病”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有男同性恋者2000万人、女同性恋者1000万人。而男同则是艾滋病的高发人群。张北川说,同性恋问题的影响远超其本身,更关乎同性恋者的家庭以及整个社会,他呼吁政府及社会应给予更多关注。
同性恋者难以拥有稳定的伴侣,一些人因而与多人进行性接触;同时,没有安全保护的男同性恋者的插入性性行为本身容易造成直肠粘膜充血、损伤,精液中的艾滋病毒会通过破损的粘膜进入血液循环或淋巴系统,造成感染。
张北川称,我国在对61个城市的男同性恋群调查发现,男同性恋的艾滋感染率达5%,其中尤以贵阳、成都、昆明和重庆四地最高,感染率均超10%,个别地区甚至高达20%。而全国人口的感染率只有万分之五。由于我国对于捐血者检验技术的制约,处于艾滋窗口期的捐血者所捐的血液无法检测出艾滋病毒抗体,内地已发现有男同性恋者的血液造成输血者感染艾滋的个案。
这些年来,为了同性恋这个特殊的群体,张北川受过很多委屈。
曾经有媒体报道,1999年5月,作为山东省最好的皮肤性病专家之一,张北川却被剥夺行医资格。他所在的医院甚至拒绝让张北川与他的性健康中心进入门诊大楼,理由非常荒唐:“同性恋、妓女进入医院影响不好。”也就在那一年,医院撤掉了性健康中心门诊。在院领导看来,艾滋病研究“纯属不务正业”。
之后,张北川曾多次要求回皮肤科上班,院方要求其保证停止同性恋研究与抗艾方面的工作。但被张北川拒绝。由于无法看病,他与两位同事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没有从医院拿到过奖金,张北川说:“这些人自以为权力与权力网形成,可以完全置国家甚至上级机构和百姓的呼声于不顾,这让人惊讶,也说明我们的工作任重道远,太复杂。”
于是,张北川不顾周围人惊讶的目光,放下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山东省皮肤科学会副主任委员、青岛市卫生局性病防治专家组组长的光环,转向了同性人群的健康干预事业。他常说:“来了,碰到了,了解了,就有责任了。”在一间不足20平米的办公室里,张北川十年如一日,开始了针对同性恋心理和生理健康上的辅导干预工作。告诉他们不必逃避和惧怕,并向他们普及艾滋病防治的知识。
这些年来,为了争得更多人对同性恋健康干预事业的理解、支持,张北川全力以赴,呕心沥血。提起这些,张北川淡淡一笑,说:“其实,我们只是做了很有限的一点工作,但我们得到了心灵的奖赏。”
英国慈善基金会Barry and Martins Trust(马丁基金会)将该基金会首届年度奖颁发给中国青岛医学院的张北川教授,以表彰他在中国预防艾滋病方面所作的杰出贡献。
对于基金会的赞助,张北川一直“攒”着,就是希望能把钱用在刀刃上。十年前,当他得知很多医生和同性恋志愿者想为控制中国的艾滋病流行做些事情,却苦于没有资源时,他在几个大城市资助发起了同性恋社区艾滋干预项目,如今项目组已扩展到几十个城市,而且都各自有了影响。他们曾经所作的一项调查数据表明,积极开展艾滋病干预后,同性恋群体中24.6%的人减少了同性性伴的数量,曾与陌生男性发生性行为者中67.9%的人减少了这种行为,使用安全套的人明显增多。
2012年12月1日,第25个“世界艾滋病日”,卫生部疾控局副巡视员孙新华说:“当前性途径已成为我国艾滋病疫情传播的主要途径,男男同性性传播比例上升明显;不过,我国扩大抗病毒治疗覆盖面,降低了艾滋病病死率。符合治疗标准的感染者和病人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比例目前已达84.0%,病死率显著下降。”中国疾控中心专家吴尊友说:“终生服药可控制病情。感染者,你只要坚持治疗的话,再活30年、50年没有问题,艾滋病不再像刚发现的只有那么可怕,它就像糖尿病、高血压一样,通过吃药能完全控制住。”
“艾滋病可防,可治,不可怕。这是一种被污名化的疾病,人们对于一个艾滋病患者从心理上‘认为是一个坏人,这也是少有人对其进行捐助的主要原因。大家对艾滋病人的道德审判太多了,缺少公正的态度,更谈不上对这部分人人权的尊重。其实这是非常不好的,我们要对付的是艾滋病,而不是人。”张北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