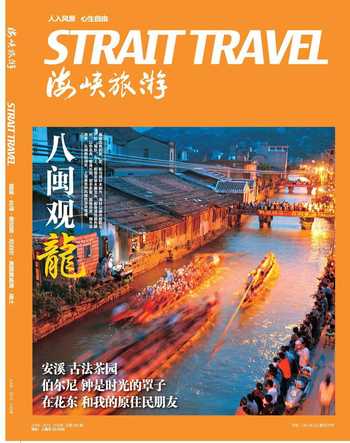热带病与寒带药
每次我对热带开始厌倦时——就像这一次的旅行,九个小时的夜车,穿插着热带人必有的凌晨夜宵时段,再加上整整十四个小时的白日班车,一层层望天木似乎从来没离开左右,雨水和阳光的交替仿佛都是瞬间发生,你会陷入一种永恒不变的恐惧,必须看到什么东西的衰老阵亡才行。很多年以前,我选择的是大兴安岭,那里春秋色变之大,不是我们这样长绿的空间所能想象的。云南南部那些饱经刀耕火种摧残的山峦,季雨林的伤口大大咧咧,正如这些蛮族的猎人一样,阻隔了大象的迁徙之路,也使得真正的森林越来越少。即使是有所谓广泛自然保护区的西双版纳,和大兴安岭地区比起来,面积只是后者的五分之一。虽然若要论树木的数量,几乎可以肯定是相当的,毕竟一个缠绕得铺天盖地貌似难以看透,一个疏朗得云阔天清无边无际。
很少有人真正的穿越大兴安岭,这实在太困难了,夏天的蚊子和心情不确定的狗熊都能让你狼狈不堪。我研究了很多年,最终还是不得不放弃。在鄂温克人和鄂伦春人大部分被劝下山后,在撤退了一部分林场工作场站后,今天的大兴安岭比起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无人无路的区域又增加了不少,地图上那些没有铁路的地方,动辄就是百公里的无人区,而一些六十年代起修了二十年的货运铁路亦再也没有蒸气突突的场景,大兴安岭正在回到它千百年来的寂静,尽管那些幼小的再生林,想要再现白桦外松果香的林海雪原,得祈祷五十年不被骚扰。
对在亚热带生长的我,大兴安岭的色彩,无疑比雨林深不见底的浓绿要吸引得多。我和大部分旅行者一样,都以白日极便宜的火车来进行这无边无际的穿越,从加格达奇到伊图里河,从莫尔道嘎到敖鲁古雅,从白银那到塔尔根,这些闪着光的通古斯语或蒙古语名字,仿佛呼唤着从来中的英雄,纵然它们的面目,不过是庸常的东北镇落。可是它的不凡也在这孤独的处境,三两户砖门外,白的树皮,黄和红的叶,如洗天空下的河流和沼泽,就算没有梅花鹿经过,亦能让你相信,这就是白银之地,鲜卑人、契丹人、蒙古人和满洲人的祖父就在这茹毛饮血,驰马流浪,依着萨满仪轨生老病死,而漠河、瑷珲城和黑龙江,从来对他们不是界限。
英雄的都归英雄,我们不过是个旅人,用的还是那血汗建筑的、正在荒废的内燃机森林铁路。大兴安岭的铁路从百年前的俄国人开始,历经日本人在伪满时期的秘密动作,再有人民共和国在1964年后二十年的发展,不知献上了多少万人的斑斑白骨,如今有的支线废弃拆除,只待松柏百年后有成再留与后人进入,亦就成了永恒的秘密。可是这也比云南好——滇越铁路已经废弃在丛林中,战时的滇缅铁路从来没有建成。
加格达奇到漠河,漠河到海拉尔,海拉尔到加格达奇,这是大兴安岭最常见的黄金三角路线。但漠河往南并没有铁路。你必须得翻过一段没有柏油的森林公路到达满归,才能继续搭火车进入草原地带。我依然记得满归给我的文化冲击:一个有50厘米长的盘子盛着满满的茄子,好吃的漠河猪大骨我不太记得了,这个茄子的份量却让人记忆犹新,它几乎是一个南蛮人家一家人的量。这是大兴安岭的力量所在,也是寒冷的证据。每一列开在白桦林里的蒸汽列车,喷出的白色雾气都像是为了寒冷写诗。
这样寒冷的地带,要有怎样的动物凶猛。或许就应该去到满归附近的敖鲁古雅一看,这里有一个鄂温克人的驯鹿基地,那些鹿不是圈养的,而是奔驰于林海与草原间,当它们归来的时候,帐篷外的星空银河满天,大兴安岭的麋鹿、狍子、水獭、兔子和熊瞎子们亦不知其踪,静静匿在暗河流过的漆黑中。
没有人去大兴安岭只看山不看草原。大兴安岭的壮阔无垠,一定得陪上呼伦贝尔无边无际的地平线才算天作之合。每一个跨山踏草的人看起来都各怀心事,村上春树咧咧呛呛走到草原河边诺门罕是为了武士道吗?一群东北欧野蛮人和一群东亚海岛岛民在东北亚的蒙古荒原上发生战争,是多么荒谬的事情。陈升写《加格达奇的夜车》看来更像是一个酒徒诗人对北方“无节制”习惯的钦慕,而我依然怀念的室韦,那个蒙古人部落源起的草原,有我喝过的白酒,吃过的狍子肉包子和大白菜。界河的铁丝网外,那个冷清淡然的俄罗斯少年,在十度的气温下冲到河里洗摩托车,这无边无际的西伯利亚,摩托车要几日几夜才能越过。
抛弃那些围起来的景点,寻找鄂温克人和鄂伦春人显然显得更加浪漫和人文,但是,他们明明还在生活,寻找之名,不多少有点矫揉造作吗?鄂温克猎人并没有完全消失,就像我的父老仍然会在秘密的丛林屋子留有猎枪,于假日转回从前的森林生活一样。在大兴安岭地区,森林铁路边巨大尺度、空地很多的储木厂不是猎人能栖息的环境,你得离开铁路再进一点。看到白桦和湿地边上,便有通古斯人后代们新的聚居栖息地,从这出去无路的地方,百年的老杨树和白桦上仍然有他们刻下的痕迹。虽然对过往生活方式的推翻已经无法抵抗,但托河和呼玛那些不舍的鄂伦春猎户,仍是只有一次一次的离家进山去。他们身上流着江湖英雄儿女的血,那种无与伦比的张力,让你无力尾随,只能跟上那些厂区的大车,跳进火车无法抵达的莽莽林原。
然而这样的冰冷,真是冻一冻也就清醒了。寒带凄厉的、如刀子一样的严厉,以及可怕的冻疮,让我又回到热带和季雨林的怀抱。云南,或者延伸到西边的缅北野人山,延伸到南边的老挝澜沧王国,它那有界限的群山缭绕固然没有漠北和西伯利亚的壮阔,却是极微观的。永恒不变曾经是我对热带的恐惧,然而换一个名词,它就变成了生生不息。
大兴安岭是一眼望不到边,季雨林每一个山坡却是一个极绿的黑洞,望天树向上冲到几乎八十米高藏住了视野,巨大的榕树张开无数的须根伸进腐叶埋藏的土地,已然是一个独立的小世界,各种绿树和芭蕉在绿荫下成长,那些怕热带灼热阳光的灌木和苗兰,悄悄又肆无忌惮地妖娆成长,还得小心翼翼地躲避那些藤,以防被缠绕至死。没有地方比雨林更生机勃勃地万物生长了,绿草蛮虫的腐败如此迅速,新生却也如此容易。事实上,这里的蚊子并没有夏天的大兴安岭蚊子凶猛,可是这里却有无尽种类的蚁虫蝎蛇,你倒不必太过惧怕它们,山里的爱尼女子和河谷的傣族汉子,闲时会带着他们的捕虫工具搜刮山林,然后就成了热带夏天惊哄游人的香喷食物。
穿越雨林同样也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那些穿越布朗山和基诺山的旅人,看到森林微妙的部分,远远不及稻田、橡胶林、茶山和咖啡园的面积之广,这是无可奈何的人文,因为人已不再因为森林而活,就算他们路过斑斓的野菌和蛇蝎一样的花叶,常常还是会为无尽的热带黑洞迷惑。在潮湿的雨林庇护下,7米长的蟒蛇悄悄于腐泥中翻滚,巨蜥和穿山甲都在躲着它,就连跳在望天树上的蜂猴也不敢随意靠近,大约只有孟加拉虎和亚洲象依然能昂然踱步。这样的丛林,比大兴安岭的坦坦荡与敏捷,算是又多了一出热带的狡黠和玩耍味吧。
和秘密满身的大兴安岭比,这里没有自杀的铁路设计师纪念碑,也没有狂暴的战争遗址。比起已经改宗东正教的鄂温克人来说,无处不在的佛塔和缅寺,以及一代又一代的小和尚,从未失去的布施之风,似乎在说傣族人和布朗族人近千年的信仰简直趋向永恒。只不过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尖顶不再是惟一。不少寺庙亦出现了汉地庙堂式的屋顶了。
这种永恒不变在逐渐远离森林的现实中,渐渐地成了优点。让这片并无酷暑的热带雨林正成为房地产蓬勃向上的新热点。在那些更有闲情和闲钱的人看来,澜沧江边的炎热未免过于下里巴人,高地的古茶才有真谛。于是那些高高在上足有五六米的大树茶和竹楼老房旁,出现了一晚房费是布朗阿妈半年收入的茶屋酒店,营造出一种古早充盈的魔幻感。毕竟是,森林早就不再纯洁,我们能享有的她的绮丽,正是基于她的累累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