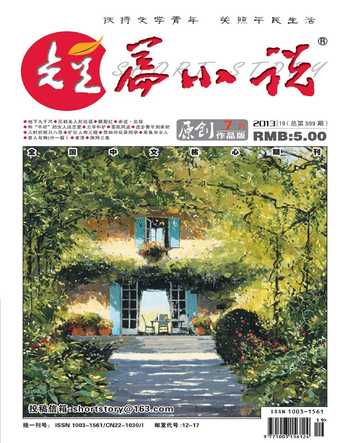《黑客》:从虚构的真迹到真实的情感
书信体小说最早诞生于欧洲文坛,盛行于18~19世纪。在20世纪20年代传入中国后,旋即得到了中国文学的响应。在鲁迅、冯沅君、郭沫若、冰心等一批知名作家的带领下,书信体小说呈现出极为繁盛的景象。进入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书信体小说一度陷入创作的低迷期。近年来,在一部分作家的努力之下,书信体小说又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其中,莫言的小说《蛙》所采用的书信体叙事模式在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同时,也有效地提升了书信体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坛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一、 敏感的现实与叙事的策略
作为一种久已被遗忘的叙事模式,书信体小说曾经创作了许多文坛佳作。从第一部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到冰心的《寄小读者》《再寄小读者》,一大批作家先后从事了书信体文学的创作。或许有人认为书信体仅仅是作者用以表达情感的一种策略、手段,但经过仔细分析之后,我们就会意识到表现范式的选择也暗含着小说文本的某种本质性特征。对于作家而言,选用何种形式的文体并非一个随意性的问题。文体的选择往往与特定的时代紧密相关,也有可能是作者本人为了完成文学创作、表现自我意图采取的一种策略。由此可见,在当代文坛选择书信体作为自己小说创作的题材,小说《黑客》的作者不能被认定为是外在因素作用的结果,而应认定为是作者本人的一种叙事策略。
当读者试图了解小说《黑客》采用书信体叙事模式时,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小说中反映的敏感现实问题如何处理,只有采用恰当的叙事策略,才能让小说在文学性与社会性之间寻觅到恰当的平衡点。正如莫言在面对记者针对小说《蛙》的敏感性提出的疑问时回答的那样:“事件尽管敏感,但是我没有把再现事件作为我的目的,因为这个事件矛盾越尖锐,对抗越激烈,越是复杂、越是敏感,人性表现得越是充分。在这样的事件、环境里,就是对这个人物一种灵魂的考验,或者我设置了一个人类灵魂的实验室,用这种特殊的事件、特殊的环境设置了这么一个实验室,把我的人物放进去考验他,然后看看他的内心,看看他的灵魂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1]
同时针对当今社会的敏感问题进行批判,小说《黑客》的作者将当今文艺界存在的腐败、堕落现象进行了适度的曝光。对于读者而言,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前所未见的社会阴暗面。作者创作小说《黑客》的目的并不在于揭示这一敏感的现实问题,或是像某些带有理想主义情绪的人士那样,简单地认为一篇小说的发表就可以有效改善某类社会问题。作者是要将小说中暴露的发生在蓝蓝与马姓作家之间特殊的关系作为背景,使其升华为读者理解小说文本的精神背景,最终营造出以此作为契机来表现国人在当下乱象丛生的社会中他们的生存、发展现状,乃至于如何去保护他们脆弱的心灵世界、如何去疗治他们空虚的肉体躯壳。
以作者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满足自我的肉体欲望以及谋求荣誉、财富的事件作为小说的背景,是作者在小说《黑客》中想要实现的直接目的。同时,摆在作者面前的首要问题之一是如何在展现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和现实欲望的同时,不将小说的主题定位于制度的臧否之中。对于作家而言,游走在小说主旨表现与现实社会敏感问题之间需要高度的技巧。在当今的文艺界,经济利益的渗透和个人私欲的满足成为很多所谓“文艺界人士”投身其中的主要诱因。作为一篇小说,过多地表现底层民众的情绪最终将导致否定现行的文艺制度。但如果作者过度地追求批判性,则会让小说失去了温情脉脉的艺术感染力。正是基于以上诸多因素的考量,作者在面对敏感的现实问题时采用了书信体小说的写作模式。在这一过程中暗含了一个基本的逻辑前提,信件可以是私密的、个人的,作者仅仅是将隐藏在某处的私人信件公之于众。因此,小说的作者并不需要背上沉重的社会责任。至于如何去评判小说的主题以及作者的情感定位,则成为了读者的事情。书信体小说的体裁选择成功地帮助作者找寻到了敏感的社会问题与叙事策略之间的平衡点。
二、 虚构的私密与情感的真迹
谈及书信,映入读者头脑中的概念首先是私密。从传统意义上来说,书信是私人之间开展信息沟通和情感交流的手段,其内容往往涉及很多不便于公开的个性化、私密化的情感内容。在早期的书信体小说作品中,小说的作者们往往利用这一点将私密的个人情感生活作为小说的主要内容。以最为著名的三部书信体小说为例,“性爱这一最为敏感的隐私问题作为探索的主题,建立符合新兴资产阶级要求的性道德和婚姻原则。”[2]由此可见,书信体小说作者利用小说中单一人物或多个人物之间的信件作为表现情感的重要载体,将人物内心世界中轻易不示人的私人情感暴露在读者面前。书信本身是虚构的,这也就导致了信件的私密是建立在虚构的基础之上。但这并不意味着作者寄予小说中的情感是虚假的,我们甚至可以认定作者正是利用书信体小说情感表达方式的特殊性,将某些个性化、私密化的情感展现了出来。
在书信体小说《黑客》中,蓝蓝发给马姓作家的信件充斥着对作家的爱慕之情,她甚至将男女之间极为私密、不能示人的性爱生活以直接、暴露的方式展现了出来。在常规的小说叙事模式中,对于性爱的描写往往只占据较小的篇幅,其目的也主要是为了营造出某种特殊的审美效果。这一点在中国作家的作品中尤其如此,受到传统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束缚,中国的作家们较少在自己的作品中对男欢女爱的性爱场景展开过度暴露的描写。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部分女性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为了彰显女性的话语权利尝试突破这一禁忌时,却陷入到“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的误区中。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小说《黑客》的作者将两人性爱场景的描写转换为小说主人公之间的信件内容。在私人信件提供的私密空间中,对当今社会中男女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适度的暴露。
虚构作为书信体小说最为重要的特征,它能够为读者提供一种相对隐蔽、非公众化的讨论空间。这正是促使作者选择书信体作为小说《黑客》创作模式的真正原因。男女之间的情感纠葛以及读者和作家之间的情感关系都可以成为当今社会舆论中被广泛讨论的问题。但公共化的讨论模仿往往会使参与到讨论中的各方被舆论所裹挟,无法采用冷静、客观的方式呈现真实的个人意愿。
你还记得吗?我们聊得那么好,当时你正和你的老婆闹离婚。你对我无话不说的。你老婆和你在同一家杀鸡厂上班。你说你老婆一点都不理解你,又胖又蠢,跟鸡笼里的鸡一样,只知道扒食,过鸡零狗碎的日子。你还说她及不上我的万分之一好。你想靠写字发迹,脱离杀鸡的命运,但苦于作品无人问津。这些你都没对蓝蓝这个爱情马甲说起过,可能你觉得这一段是你耻辱的历史吧?我爱屋及乌,从你的字里感觉到你那颗滴血的心,生活的肮脏和低下,才能磨炼你的才华吧?
对于自己的被抛弃,《黑客》中的女主人公终于向所谓的“作家”展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曾经的甜言蜜语,曾经的疯癫迷狂,都成为了被遗忘的过去。只有当男女之间的关系彻底破裂,才会将隐藏的过去、淡忘的伤痛都宣泄出来,继而成为攻击对方的武器。虚构的信件以私密的方式将作者内心最为真实的情感表达了出来。
三、 自由的叙事与袒露的真情
小说《黑客》无论是从故事情节而言,还是从作者寄予其中的情感而言,都要求采用高度自由的叙事模式来呈现。所谓的“自由的叙事”主要是从两个层面而言的:首先,从小说文本的创作者角度而言,“自由的叙事”意味着作者可以采用自己认可的最佳手段来呈现小说的主要内容;其次,这篇小说采用的书信体模式为小说人物表达内心情感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给予了绝对的“话语权”。因此,作者可以通过信件的主人公随时对小说文本展开适度的干预措施。
在小说《黑客》中,我们可以通过前四封信直接感受到蓝蓝的情感起伏。她不仅获得了自由表达内心意愿的权利,也构建起了属于“自己”的小说世界。对比之下,读者会发现传统小说题材中作者的身份总是明确的,能够明确感受到作者在利用自己控制权操控小说中的所有角色,这一点在书信体小说中几乎无法察觉到。
由于小说是以书信作为主要的载体来表现作者的创作意图,书信体的主人——文本中的叙述者——往往直接在信件中袒露心声,或是用以加快小说情节的发展,或是用以帮助读者理解小说文本。
终于收到您的来信了。如果不是为了找我借这两万块钱,我敢打赌您不会给我半个字的回信。这个世界真奇妙。我把我的身体快递给了你,而且是自己付的快递费,你用完之后没有一声谢谢,反过来一开口就是找我借钱。我给你写的又臭又长的邮件,竟然没有丝毫熏到你!我不敢奢望你一字一句看过,但你对我是小索这点提都不提,好像在你的意料之中,又好像这是很无聊的身份辨识问题。
当读者还沉浸在蓝蓝与马姓作家缠绵的爱情故事时,她写给作家的第四封信迅速地推进了小说情节的发展,将两人之间原本含情脉脉的情感迅速打入谷底,将二人早已相识却始终没有揭穿的真实关系暴露无遗。于是,蓝蓝作为读者的身份在一瞬间升级为默默的支持者,曾经的放荡女子摇身一变成为了最大的受害者。与此同时,在小说的结尾我们看到了一直沉默的作家对于蓝蓝的多封信件有了回复。正是借助书信的这一基本特点,小说的作者为我们构建起复杂的人物性格和多面的人物形象。
作为一篇书信体小说,《黑客》成為当今文坛极为少见的“另类”作品。作者借助书信体小说自身的优势,为读者开启了全新的阅读视野。用虚构的真迹表现真实的情感,表达了作者最为真实的内心世界。
[参考文献]
[1] 刘郁琪.莫言小说《蛙》的书信体叙事[J].学理论,2010(20).
[2] 张德明.近代西方书信体小说与主体性话语的建构[J].浙江大学学报,2002(03).
[作者简介]
刘子裕(1967— ),男,湖南益阳人,本科,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与油画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