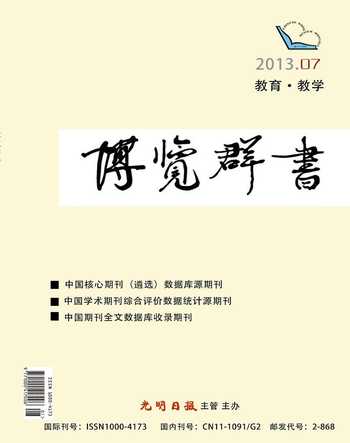中国的民族——政治力量干预的结果
刘玉秋 张保贤
杜磊于1998年出版了他的力作:《中国的族群认同》的英文版,本书的副标题为:一个中国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制造,很不回避地道出了自己关于中国族群认同方面的思考和认识。
在本书的第一章,作者首先从政治需要的角度谈了一下自己对中国民族形成的认识。杜磊认为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也由多种具有文化和族群差异的人口构成,包括8个彼此很难听懂的语言群体(北方、吴、粤、湘、客家、赣、闽南、和闽北方言),在每一个汉语支系中也存在明显的语言和文化差异。但即使是具有这样大差异的人口群体在中国也仍然被识别为了一个统一的民族:汉。于是杜磊先生从汉民族的产生过程角度出发,阐述自己关于汉民族出现的政治考虑。作者认为:把中国的一些群体识别为“少数民族”以及把汉族识别为一个统一的“主体民族”,这对于铸造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具有的基础性作用。首先“汉民族”这种观念的出现完全是现代现象,是随着中国从封建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而出现。孙中山先生在反清的实践中需要一种方式去动员所有的中国人来反对清王朝,他通过论证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口是汉族找到了一种国家的象征作为有效的武器,以此使不同种类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团结起来,反对满族或其他外族。杜磊认为,“汉”看起来是站在中国的“内部异族”——满族、藏族、蒙古族和回族等的对立面;也是站在“外部异族”——被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对立面。而通过区分这些他们之中的“内部异族”,民族主义者培植起了一种新的、一般说来较为明确的汉族认同。作者认为,无论对民族主义者还是共产主义者来说,确认汉族和承认少数民族都不仅仅是为了获取边疆族群支持的政治需要,而且也是希望减弱内部差异,以统一国家去抵御外族。从而阐发了作者关于中国的民族是出于政治需要考虑而强行建构出来的观点。
杜磊的这种关于政治制造民族的观点,从他的论述上来看确有其合理的理由。但出于我对中国民族形成的浅显的思考,在此也想发表一下自己不够成熟的看法。杜磊关于汉民族的出现是当时的政治领袖人物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而建构的观点,固有其合理之处,但若仅仅从这一个方面来考察汉族的形成也难免有失偏颇。汉族的形成是在与异族和外国列强的对抗过程中出现并开始形成的观点,我认为还是很有道理的,但这个时候汉族的出现也有其历史文化的传承之因。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化核心概念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对这个文化核心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贡献以及深受其影响的人群,这样的人群因为对这个文化核心有一定程度的认同而彼此之间亦形成了互为同类的认同。把这样的人群定义为汉族或许可以对杜磊的概念做个补充,无论这些人的表面差异有多大,但他们分享着一个共同的心理素质——即这个文化核心概念。这个文化核心从简单的说,我认为可以指称为儒教思想。
在本书的第二章,杜磊对中国回族的出现从理论上进行了疏理。作者认为,在中国穆斯林认同的中心是对伊斯兰的汉语翻译和阐释,即汉语对“清真”的表述。他认为“清真”揭示了中国伊斯兰教对回族的社会利益和自我理解最重要的两个方面:清,表明宗教的纯洁性和道德的高尚性;真,意味着真实性和合法性。对回族来说,“清真”的两个方面,“清净”和“真实”,明确地解释了他们的认同的重要张力:伊斯兰教的道德纯洁性和族群世系、生活方式和传统的真实性。汉语中对在中国的回回人或伊斯兰教的特定称谓“回”或“回教”,在元朝之前并没有得到广泛流传。作者认为,中国的语言学家根据他们假定的民族自己的语言识别出的那些中国穆斯林民族,其族称则来源与他们所属的语族。根据这种方法,维吾尔、哈萨克、塔塔尔、乌孜别克、柯尔克孜和塔吉克族得到了识别。而新中国政府却用“回族”指称那些没有自己独特语言但又分享不同地区方言的穆斯林人群,以便同其他九个突厥-阿尔泰及印欧语系的穆斯林民族相对应。回族因此而经常被称为“中国穆斯林”,因为他们的语言和其他文化特质比突厥语族穆斯林更接近于汉族。回族就是这样被识别出来了,但紧接着作者就开始发问:谁是回族?因为回族社区的广泛差异及回族为解决在中国社会保持“清真”生活方式的张力而采取的不同适应方式,经常使他们的认同变得模糊。他们分布广泛,人口分散,职业构成特殊,语言多样,教派多样,就这样一个人群居然被识别为了一个民族,这是出于什么考虑呢?到此作者阐明了自己关注的焦点问题,也就是本书主要想说明的问题:不同地区的回族认同是怎样来的。回族社区存在着极大的文化和宗教差异,在以往的讨论中一些理论试图对他们如何认同为一个族群及国家为何将其承认为一个民族做出解释,作者列举了三种主要的理论模式:“中国-斯大林模式”,“文化-原生论”模式和“场景-工具论”模式。
作者认为西北的回族认同超越了族群认同,他们更重要的是一种民族宗教认同,因为伊斯兰教同他们的自我理解密切相关。纳家户回族在开明政策下的宗教实踐复兴和传统主义的上升刻画出伊斯兰教在快速变化的社会经济场景下的重要性。纳家户回族认同与开明政策的互动导致了回族认同表述的迁变和地方民族政策的重构。杜磊认为地方政府政策与伊斯兰宗教是纳家户回族认同的关键因素。常营的回族由于其处于汉族占主导的地区,在保持其族群认同的努力中他们实行严格的族群内婚制。对这些回族来说,祖先遗产和族群认同通过内婚制表述出来,即在一个特定群体内按照风俗或规矩通婚。内婚制是这个社区的回族保持其衍自外国祖先的血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他们通过民族内婚制保持其社区的纯洁性和凝聚力,这就是他们表达自己清真的方式。
在常营这部分内容杜磊一直在谈的就是这里的婚姻情况导致的其民族认同问题,对其研究的主题——政府政策对回民族的制造方面的内容几乎没有什么涉及。我认为这应该也是作者的失误之处了吧。对于那些都市回族——以北京牛街为例,他们散居在城市里面,猪肉禁忌的重要性成为了其族群认同的重要表达方式,因此,在都市促使了清真饭馆成为了一种文化中心。由于政府政策对少数民族尤其是回族在食物供应、子女教育和计划生育等方面的照顾,造成了当地回族地位的上升,以及提高收入和生活方式改变的可能性,因此在与异族通婚所生育的子女中,人们更倾向于登记为回族。由此可见,政府在都市回族的认同方面的作用也是举足轻重的。
对于东南沿海地区的陈埭来说,这里的回族能被认定为回族与政府政策的影响是根本不能分开的。这里的人们认定自己是回族主要是基于自己祖先是外来穆斯林,虽然他们很久已经不遵从穆斯林的生活方式生活了。与之情况相同的人群在台湾却并没有被称为回民。作者对这两者情况的对比分析清楚的说明了大陆政策在东南沿海回民认同中的重要作用。如果严格按照民族识别时所依据的斯大林四条标准,这里的回民是无论怎么样也不会被识别为回族的。但现实情况是这样的:政府政策对少数民族具有偏向照顾的倾向,东南回民虽然已不再是大家通常认识意义上的回族,但他们为了争取政策的照顾发展自己的经济,就搬出了自己祖系真实的证据;政府为了鼓励少数人先富起来,为了争取外来资金支持国家的建设,也愿意把这部分人识别为回族。于是,东南沿海的回族就这样出现了。在这里回族的出现及其民族认同的保持中,政府的作用可以被清清楚楚的看到。
作者在结语中写到:关系过程缔造了中国的一个穆斯林民族——回族,它作为一个民族宗教共同体诞生在四十年前,拥有强烈的族群认同甚至夸族认同。正如随着回族和其他民族与地方场景的互动,他们的族群认同和国家影响他们的政策亦同时发生变化。国家的民族识别制造了中国的56个民族,现在由于政策的影响和长期的认同建构,这些民族正在努力使自己成为这样的民族。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族识别政策将会越来越显示它制造民族的成功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