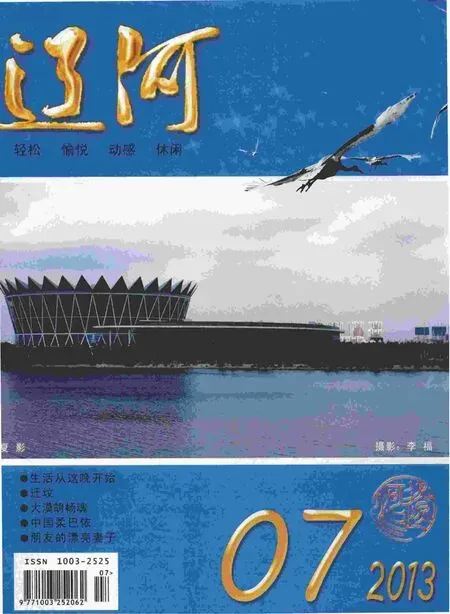发自灵魂的声音
洪治纲
随着年岁的增长,诗歌却渐渐地疏离了我的精神生活。尽管我也在心里时常忏悔,一个远离诗歌的人,实在是有愧于搞文学的,因为母语的高贵与纯洁,在很多时候都是体现在诗歌之中。但是,我转眼又想,诗歌原本就是与青春和激情相伴的产物,既然韶华已逝,留不住诗歌的倩影也属自然,何况自己的青春里的的确确翻涌过一些诗的微波。
更多的理由或许还在于:如今的诗人越来越多,诗歌却越来越“地下”。翻看一些刊物,我也会留意那些有限版面中的诗歌,但我看到的大多是些情绪流或意象流,是些诡秘的语句或玄奥的思辨,却很少感受到诗句中诗人灵魂跳动的姿态。更有甚者,为了让自己的作品获得冲出“地面”的权利和机会,有些诗人以多元文化为借口,让诗歌向“下半身”敬礼,让诗歌向形而下献媚。这让我很是尴尬,甚至为之羞愧。诗人,为什么如此轻易而又沾沾自喜地低下高贵的头颅?如果说“诗歌是用来交流的真理,”(阿莱桑德雷语),那么,这个真理就是要告诉我们,人之为人,乃是要恢复他的动物欲望。
这些不尽人意的现实,使我对现在的诗坛有着难以言说的隔膜,甚至让我说出“如今见到诗人,我便绕道而行”之类颇为决绝的话。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情感定势,当我拿起郑炜的诗作时,说实在的,我并没有什么烈焰般的期待。在一个非常容易成为诗人的年代里,带着更多的热望去阅读诗歌,常常会收获更多的失意。这是经验对我的忠告。
但是,在有意无意的阅读过程中,我慢慢地觉得,郑炜的这本四行诗集,却有着自身独特的韵致。它们萌生于各种世俗的生活里,经过诗人情感和心智的浸润,每每在不经意之中,便绽放出各种意想不到的花朵。我以为,它们是属于内心的产物,灵魂的声音。对于一切发自灵魂中的声音,我必须保持敬意。因为每一个灵魂的存在,都决定了一个生命的全部价值,也决定了他的歌吟与浅唱的份量。感谢郑炜,他为恢复诗歌作为纯粹的内心产物,在进行着孤独的抗争与顽强的尝试。
我不敢说这样的尝试究竟能走多远,因为四行诗在中国的历史上已经走过了自己的辉煌——它不仅以绝句实现了与音乐的美妙融会,而且使文学充分地渗透到其它诸种艺术领域之中。但是,我仍然觉得,这份远离尘嚣的灵魂独语,就像暗夜中轻轻游动的萤火,会随时提醒我们,沉默的大地从来都不曾放弃诗意的怀想,更何况大地哺育的精灵——我们人类,这些被称为“有思想的芦苇”。
惟因如此,里尔克便在那本《给青年诗人的信》中反复强调寂寞对于诗歌写作的重要意义,“艺术品都是源于无穷的寂寞”,“在寂寞中你不要彷徨迷惑,由于你自身内有一些愿望要从这寂寞里脱身”,“在根本处,也正是在那最深奥、最重要的事物上我们是无名的孤单”。英国诗人奥登说得更为明确:“诗人却在绝然的孤寂之中构造他的诗。”是的,寂寞的存在,往往意味着灵魂的苏醒,思想的出场,感觉的跃动,言语的盘旋。而郑炜的诗,很多就是由这种寂寞浇铸而成,仿佛灵魂面向寂寞的祷告。
这是一种“诗心且为寂寞舞”的意境。
背负着寂寞,在热闹的红尘里为内心而活,这当然绝非易事。所以在《放下吧》里,郑炜曾如此写到:“就像放下一桶水/放下吧 当梦/成为一种/负担”。诗人试图让理智来告诫自己,放弃精神里某种沉重的东西,卸下内心中那远离现实的梦想,使自己摆脱孤寂而融入世俗中。但是,对于一个崇尚灵魂质地的人来说,这种愿望,与其说是一种告诫,还不如说是一种自我的安慰。事实上,读郑炜的这本四行诗集,它们或怀旧,或感伤,或积郁,或反思,无一不是盘旋于自己的灵魂,无一不是面对现实的不满而发出的叫喊。它们简明,迅捷,质朴,甚至显得有些浅显,但是始终带着灵魂跃动的韵律。
记得勒韦尔迪曾说:“诗人是潜泳者,他潜入自己思想的最隐秘的深处,去寻找那些高尚的因素,当诗人的手把它们捧到阳光下的时候,它们就结晶了。”在我将自己标榜为诗人的时候,我曾经将这句话写在每一本诗稿的首页。现在,我将它再次抄录下来,送给诗人郑炜,为他的诗,也为他丰饶而敏感的心灵。